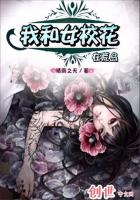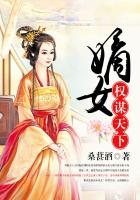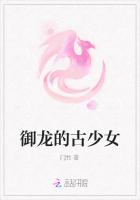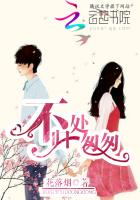这一次,第二件事情发生了——冯谖发现了人世间最闪光的真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冯谖认为孟尝君是金子,所以他认为此人还会发光。为了让孟尝君再度闪闪发光,冯谖出现在了秦王面前。
秦王很不耐烦地看着他。
秦王对没有利用价值的人总是很不耐烦,他没空陪这些人聊天。
只是这一回,他很快就耐烦了。
因为冯谖说的话很有价值。冯谖说,孟尝君这个人你是知道的,人才啊,以前大王你不敢用他,原因只有一个,怕他为齐王效力。可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孟尝君被齐王废了,正恨他恨得要死,可惜又没有一个可以出气的平台,大王如果此时重用他,孟尝君肯定会玩命报答大王的,如此一来,秦国灭齐可期!
秦王恍然大悟。
再一次习惯性地恍然大悟。
当然,冯谖这一次游说的时机也好——秦国的智囊樗里疾死了,秦国急需一个新智囊。秦王突然由衷地佩服自己,离间孟尝君和齐泯王这一着棋走得实在是高啊,既打击了敌人,又壮大了自己。他毅然决定,以丞相的规格,迎接孟尝君入秦。
十辆豪华接待车浩浩荡荡地从咸阳出发了。它们带着迎接孟尝君入秦的坚强决心和意志向齐国孟尝君老家薛地开去。
只是,它们没有接到孟尝君。
因为在最后一刻,齐泯王幡然醒悟,重新启用了孟尝君。
一切都是冯谖的功劳。
当冯谖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从秦国赶回来向齐泯王报告秦王要重用孟尝君的消息时,齐泯王突然觉得自己上了一大当,做了一大错事。
废黜孟尝君,这是要亲者痛仇者快的啊。
决不能让秦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得逞!齐泯王马上让冯谖拿着委任状火速赶到薛地,务必让孟尝君同志重回朝廷,报效国家。
冯谖笑了。
笑得很金光闪闪。这一刻,冯谖发现自己离那个人世间最闪光的真理如此之近,自己不金光闪闪都不行啊……
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
秦王这两天心情比较爽。
虽然孟尝君最终没到手,但是伟大的秦国军队打败了韩魏两国联军新近的一次伐秦企图,其中伟大而著名的白起大将不仅下令砍掉了24万联军的人头,还拿下了韩武遂地二百里、魏河东地四百里。
秦国以其赫赫战果雄辩地证明:合纵之策不可靠,伟大的秦国军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
秦王把头抬到了天上去,整整三天。
但是,第四天早晨他把头低了下来,一方面是因为脖子痛得厉害,另一方面则是,他想到了一个成语。
孤芳自赏。
在这个世界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同样,孤芳自赏的人也是可耻的。
秦王觉得,自己孤芳自赏是因为太谦虚,到今天还和普通的小国国君一起称王。虽说都是王,但燕王、秦王能相提并论吗?!
他决定自我升格——称帝。
一个王的快乐是小快乐,一个帝的快乐才是大快乐。秦王豪迈地做此联想。
不过,在称帝这个问题上,秦王不想唱独角戏。他向齐王建议:两人同时称帝,一为西帝,一为东帝,前者主西方,后者主东方,以平分天下。
与此同时,秦王还建议:两国联手,把赵国他奶奶的给灭了。
齐泯王觉得很头疼。
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重为国相的孟尝君告诉他,秦王现在已是个自大狂了,他这么做,会让所有国家同仇敌忾,我们齐国千万别去做这个垫背……
这个道理,齐泯王当然懂,可他依旧觉得很头疼。
因为孟尝君没有回答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得罪秦王后,齐国该怎么办?
好在这个问题,苏代替他回答了。当时苏代大使正从燕国访问齐国,两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苏大使告诉齐泯王,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问题,可以走第三条道路。大王在称帝问题上,只要跟在秦王后面看各国反应再谨慎从事即可。如果秦王称帝后,各国不感冒,那大王趁势而上,称帝;如果各国强烈反对,那大王就按兵不动,这样的话齐国两头都不得罪。还有伐赵问题,这个万万不可,一来师出无名,二来即便伐赵成功,得地则为秦利,齐国没半点好处。所以伐赵不如伐宋——地球人都知道,宋国国君的良心是大大地坏了,不伐是不行了。
并且,伐宋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得其地可守,得其民可臣,而又有诛暴之名。这是汤武之举啊!
齐泯王屏住呼吸,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快感。
难与人言的快感。
苏代大使把话说得如此玲珑剔透,齐泯王的感觉是——醍醐灌顶。
什么都明白了。如今之策,伐宋是上上之选。
秦王称帝两个月后,突然感觉一阵无边的落寞。
齐泯王没跟上,依旧有滋有味地当着他的王,而不称帝。
当然齐泯王不称帝在秦王心目当中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摆设而已——问题出在其他五国的反应上。
竟然置若罔闻。
竟然不拿他秦西帝当回事。
这让秦王感到好生没趣。
他悻悻地宣布:不再称帝,和同志们一样,称王。
但与此同时,一件令他更不快的事情发生了。
齐国悍然攻打宋国。
这太不给他面子了。因为宋国国君宋康王上个月刚和他拜把子,交杯酒刚喝完还没走肾呢,齐泯王就上赶着开打了——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绝对不能饶恕!
更不能饶恕的一点是:齐泯王在背着他拉帮结派。因为攻打宋国的不止齐国一家,还有楚魏两国!
战国江湖上,什么时候轮到你齐王发号施令了?!秦王很生气。
秦王生气之后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他要出兵,誓死保卫宋国!
齐泯王慌了,他没想到,事情会走到如此地步。因为傻瓜都知道,和强大的秦国对抗,绝没有好下场。
苏代大使只得再次出场,事情由他而起,他当然要负责到底。
苏代兴冲冲地跑到咸阳去,向秦王贺喜。
秦王以为,一个人突然莫名其妙地向另一个本无喜事的人贺喜,葫芦里一定藏着什么药。
他就想看看苏代葫芦里藏着什么药。
苏代说,我贺喜大王、恭喜大王,那可是发自肺腑的,因为楚魏两国要臣服大王了。楚魏两国之所以要臣服大王是因为他们受不了齐王的鸟气。为什么呢?事情很清楚,在即将进行的齐楚魏三国伐宋行动中,强势的齐国肯定不愿意利益均分,它要时时处处压制楚魏两国。这样一来,楚魏两国势必要寻求公道。当今世界,谁能给他们公道呢?大王您哪!为寻公道,楚魏两国只能臣服大王,所以我苏代在此要贺喜大王、恭喜大王了……
秦王笑了。
却是苦笑。
他觉得,苏代所说的事情,相当的不靠谱。他借此机会请教苏代:宋国要不要救?
苏代告诉他,在这个世界上,救一样东西一定有救一样东西的道理,如果它命不该绝的话。可宋国显然该死翘翘了,坊间都在传说,宋康王一个晚上要搞几十个女人,这是天理人道吗?这样的国家不亡,什么样的国家才可以消亡?大王你请告诉我……
秦王无言以对。
他之所以无言以对是因为苏代的话深深地刺激了他:一个晚上要搞几十个女人,娘希匹,什么东西?!还跟我喝拜把子酒。我吐!我狂吐!!
秦王最后作出的决策是,和这个性功能亢进者一刀两断,坐视他的国家走向死亡。
这基本上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三个大人打一个小孩的游戏。
齐魏楚三国以秋风扫落叶般的速度和气势,把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国——宋国给灭了。
这看上去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事实上却是相当的不正义。因为三国灭宋的目的不是为了匡扶正义,仅仅是为了——三分其地。
更大的不正义还在于,齐魏楚三国内讧了。
内讧起自于人心。
一个人的欲望。
齐泯王。
对齐泯王来说,将弱小的宋国“三分其地”只是一个阴谋的开始,他还要对同盟军魏楚“三分其地”。
光天化日之下,各自凯旋的魏楚两军怎么也没想到,刀子已从后面插过来了。
虽说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但魏、楚两军还是没有料到,刀子会来自身后,来得如此稳、准、狠。
在重丘,回师的楚军被齐军重兵追杀,随后齐军占领了淮北之地;在三晋之地,魏军也没有躲过齐军的魔爪,几乎全军覆没。
这场内讧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秦国坐收渔翁之利——很傻、很受伤的魏楚两国倒向秦国怀抱,发誓要复仇雪耻。
齐泯王却一点不怕。
因为胜利接踵而至。
卫鲁邹三国害怕齐泯王杀得性起,祸及其身,连忙屁颠屁颠地赶到临淄来称臣请罪。
齐泯王头抬得很高,眼睛看向无限遥远的一个地方。
洛阳。
人生如此无趣,胜利如此无味,只有这个地名才让齐泯王有那么一点点兴趣。
当然齐泯王不是对洛阳所有的一切都感兴趣,他只对那九只鼎感兴趣。
这个意义上说,齐泯王的志向比秦武王要远大。
秦武王只对九鼎当中的一只鼎感兴趣,而且很没出息地死在那只鼎面前。齐泯王却不一样。
他不屑于大老远地跑过去摸一摸,使蛮力去搬动它们。
他要它们乖乖地跑到临淄来。
他要临淄成为世界中心的新坐标,而他齐泯王的两只脚,将死死地踩在新坐标的中心点上,一百年不动摇。
一句话:他要成为当今世界的新主人。
孟尝君很不知趣地打断了齐泯王的意淫。
因为他觉得这样下去很危险。
齐泯王的危险就在于,他奶奶的当真了。他竟然跟孟尝君说:“旦晚提一旅兼并二周,迁九鼎于临淄,正号天子,以令天下。”
孟尝君告诉他,最后一句话说错了一个字。
不是“以令天下”。
而是“以亡天下”。
宋国是怎么灭亡的?就是因为他人小卵大,向全世界挑战,结果被这个世界给消灭了。大王啊,在这个世界上混,名望比实力更重要。周王朝为什么奄奄一息却老是死不了?名望在啊,他是天下共主,所以我们七国打仗从来不敢去伤害他。可大王你没有这个名望啊,你硬去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不成了第二个宋国君吗?
孟尝君这话说得慷慨激昂,齐泯王却不置一词。
他的脸上看不出有什么表情。
几天之后,孟尝君的相印又被他收回去了。孟尝君这才明白,大王生气了,后果又很严重。
当然最严重的后果还没到来,这是关乎一个国家的后果——齐国,将会为齐泯王不合时宜的欲望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他孟尝君随时可能人头落地:国破家亡之际,恼羞成怒的齐泯王是绝对不愿意孟尝君活着看他笑话的……
孟尝君只得跑了。国家他是顾不上了,自己的小命,他还是要顾及的。他跑到了魏国去做国相,静看一场战国江湖因果轮回的大戏即将拉开帏幕,同时为自己的无力感深深叹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而聪明如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