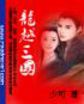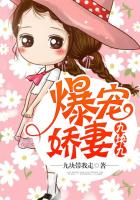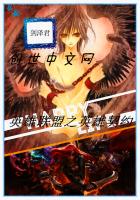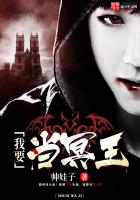吕不韦不再偷情了。
这并不意味着他良心发现或是性功能方面出了什么问题,而仅仅是因为——
一双眼睛。
秦王政的眼睛。
在吕不韦漫长的偷情岁月里,秦王政的眼睛从单纯清澈走向狐疑忧伤。
因为他感觉到了母亲和吕不韦两人共同制造的绯闻。
不,应该是丑闻。
吕不韦不得不有所忌惮。
不错,秦王政现在是没有出手,但这不代表他将来不会出手。
聪明如吕不韦者春江水暖鸭先知地作出一个决定:及时抽身,中止他的偷情活动,以免惹火烧身。
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因为太后饥渴难耐。
当然准确地说法是性饥渴难耐。
她继续缠着吕不韦,一副飞蛾扑火的架势。
吕不韦可不想和她一起焚身以火,他很快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替代品——
嫪毐。
嫪毐是个天生异秉的男人,正是由于他的天生异禀,吕不韦得以全身而退——太后不再缠他,而是缠他的替代品了。在太后看来,替代品比正品更具实用性。
也更具成果。
因为他们竟在两年之中,搞了两个孩子出来。这让吕不韦自愧不如的同时,心里也是怕得要命。
见过明目张胆的,没见过如此明目张胆的。万一太后事败,自己也脱不了干系:不说有前科吧,起码也是一拉皮条的。
好在两个孩子是在离咸阳两百里地的雍州大郑宫生的,这大郑宫是秦王政赐给太后养老的所在,没想到太后她老人家将它变成产房了。
吕不韦只得祈求上苍,希望老天能瞎了眼,别让秦王政知道大郑宫里发生的一切。
秦王政还是往大郑宫来了。
不过,他不是来捉奸的,而是来行冠礼。尽管这一年他已二十六岁,但太后仍迟迟未给他行冠礼。
也就是说,在太后眼里,秦王政还是个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不懂成年人的事,太后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但是秦王政却是不管不顾了,他直闯大郑宫,并且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接下来就是举行酒宴,隆重庆贺秦王政成为成年人。
即便到这时,太后的丑闻也未曾暴露——因为她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那从理论上来说就没有什么丑闻了。
除非他自己嚷嚷出来。
太后当然不会这么傻。
但是有一个人却有这么傻。
嫪毐。
客观地说,嫪毐在不喝醉酒的情况下也没这么傻,要命的是这一天,他偏偏喝醉了。
而且是和中大夫颜泄一起喝醉的。
嫪毐不仅喝醉了酒,还骂颜泄不是东西,同时称自己是当今秦王的“假父”。
“假父”这个词很暧昧,但颜泄很快就明白了。
秦王政也很快就明白了。
明白之后是愤怒。
愤怒之后是搜索。
便在大郑宫搜出了“假父”嫪毐的证据——
他和太后两人生的两个儿子。
当时他们两人被藏在暗无天日的密室内,不知道自己的明天会是怎样。
秦王政没有给这两个孽种明天,也没有给嫪毐明天。
他们都被处死了。
甚至嫪毐的三族都被处死了。
对于太后,秦王政实施了软禁政策:伤风败俗以至于此,不可再为国母。着即搬出大郑宫迁居别处,以兵三百人守之。
当然还有那个吕不韦。秦王政本来也想把他“咔嚓”掉的,但最终他只收了他的相印了事。
原因有两点:一是吕不韦的丑闻都是传说,没有留下实据。正所谓春梦了无痕,梦醒时分,谁也不知道吕不韦同志到底做的是春梦还是噩梦;
二是吕不韦有功于先王。要不是当年他倾家荡产扶持先王,秦王政现在还在赵国做人质呢……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根本没有秦王政这个人的存在,因为一切都在吕不韦的掌控之中,包括秦王政可疑的身世。
这场很黄很暴力的宫闱秘案就此不明不白地结案,不过秦王政对案中人的种种处分却在不久之后引来了一些非议。
非议主要围绕他对太后的处分方式。
大夫陈忠哭喊着对秦王政说,天下无无母之子,大王要早日把太后迎归咸阳,以尽孝道啊……
但是陈忠很快就不喊了。
因为他死了。
秦王政以一种恶狠狠的方式让他毫无尊严地死去,并且横尸阕下。
横尸阕下是有目的的。那就是秦王政想以陈忠作为反面典型,告诉那些试图再对他说三道四的人——这就是下场。
但是不识时务者接踵而至,有些人看上去什么都不怕。
包括死。
在陈忠之后,继续横尸阕下的有二十六人。他们和陈忠一样,都死于——
死谏。
命运的逆转
接下来沉寂了一段时间。
不错,有些人是不怕死,只怕死得毫无价值。秦王政杀人杀红了眼,再前去送死,毫无意义。
茅焦就持这个看法。
茅焦是沧州人,却喜欢行走天下,四海为家。
“行走天下,四海为家”不是他人生的目的,而是他寻找人生意义的手段。
一直以来,茅焦就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这实际上是对其人生意义的拷问。这样的拷问很多年来都没有答案,直到他漂流到秦国,遇上秦王政杀人事件。
茅焦觉得——答案有了。
如果能劝阻秦王政停止杀人,以天下苍生为念,茅焦认为,这就是他的人生意义。
他一直以来行走不已的全部价值之所在。
所以他要往秦宫去,往秦王跟前去。他要焚身以火,即便成为第二十八个谏死者,茅焦认为,那也是舍生取义的壮举。
从秦王政的视野里望出去,这个叫茅焦的沧州人和前二十七个找死者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说真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比前二十七人更笨。
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茅焦将有二合一死法——找死兼笨死。
事实上茅焦也做好了死的准备,因为他紧靠着一口大火锅,而这大火锅里的水即将沸腾。
很快地,茅焦将主动或被动地投入到那口大火锅中去,煮熟后被捞出,很荣幸地成为横尸阕下的第二十八个谏死者。
但是茅焦没有很快地将自己投入到那口大火锅中去,因为他有话要说。
秦王政长长地打了一个了无新意的呵欠,然后做洗耳恭听状。
不错,是洗耳恭听,却是有些心不在焉的洗耳恭听。
因为秦王政料定此人也会和前二十七个找死者一样,了无新意地痛骂他不孝之后就再也不会给他什么惊喜了。
但是,秦王政错了。
茅焦不屑于骂他,而是号啕大哭。
为秦国而哭,为天下苍生而哭。
茅焦说,秦国是多么有底子的一个国家啊,秦王又是多么有雄心壮志的一个君王啊,本来一统天下指日可待,却在小节上纠缠不清,留下了不仁、不友、不义、不孝的名声,以致天下英雄不敢来投,天下苍生不敢归顺。苍天啊,大地啊,同样都是君王,为什么要给秦王这一层魔障,使得秦国王业半途而废?!假使我的死能帮助秦王去除魔障,茅焦又何惜此肉身哉?
茅焦说到这里就开始脱衣了。他要投之于汤水,他是真正地打心眼里要拯救秦王政,而不是来一个现场火锅秀。
秦王政拉住了他。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还有一个词能打动秦王政的话,那就是——
天下。
的确,没有人可以藐视天下,而茅焦恰恰把这个词说了出来,哭着说了出来。所以他的命运在一瞬间逆转了。
他不仅走出了阕下,还成为太傅,政治待遇相当于上卿。
太后的命运也逆转了。她被秦王政接回咸阳,母子重归于好。
吕不韦的命运也附带着被逆转了。
他死了。
不是秦王政杀的,而是自杀身亡。
当然他的死说到底和秦王政有关,因为秦王政在将他罢官之后,吕不韦回到了河南老家。作为秦国前政治明星,退隐的吕不韦依旧是各诸侯国争夺的对象。它们纷纷派人与其联络,希望吕老能屈尊到他们国家去指导国事,而吕不韦同志呢也是人老心不老,很有再战江湖的想法,这让秦王政相当的不开心。
于是便手书一封,告诉吕不韦要老老实实,不要乱说乱动;要闭门思过,不要四处招摇。同时暗指吕不韦为老不尊,于国于己危害大矣。在这封信的背后,秦王政还为吕不韦指定了一个养老场所——郫城,希望他就待在那里终老,别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了。
吕不韦于是自杀。
的确,一个终生行走在风尖浪口上的人,他的命只和风浪在一起。风平浪静了,他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吕不韦就是这样的人。
当然,还有很多人的命运也逆转了。
吕不韦的门客们,以及那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秦漂。
吕不韦死后,秦王政就下了逐客令。
他不想再看到他们,特别是他们的——
舌头。
在秦王政看来,这些靠一根舌头走天下的人比吕不韦还不如,吕不韦当年好歹是金钱开道,玩的可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可那些秦漂呢?没有一点风险投资就来搏天下了……
但是,一封信让秦王政的看法大变。
信是李斯写的。
李斯也是秦漂,著名秦漂。很多年前,他因为看到厕所里的老鼠和粮仓里的老鼠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顿时悟出行走改变人生的道理。随后他来到吕不韦门下,慢慢地让自己变成了一只粮仓里的老鼠——他被秦王政拜为客卿。
只是秦王政逐客令一下,李斯再也做不成粮仓里的老鼠了,尽管他著名,著名得全体秦漂都知道他,可毕竟,他也是秦漂,也是一根舌头走天下的人,所以李斯也被驱逐了。
他成了秦王政不欢迎的那一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