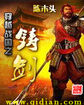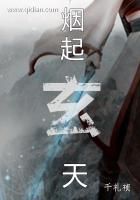周俊利
提到90年前的那场声势浩大的反袁护国运动,人们很自然地想起驰骋沙场的赫赫战将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却往往忽视了护国运动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梁启超;长期以来,在史学研究领域,也未能充分肯定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笔者以为:在护国运动中,梁启超在制造舆论、策划和组织护国战争以及联络各党派、各阶层建立反袁联合阵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些活动推动了护国运动的爆发和发展。
一、护国运动中舆论制造的主将
梁启超的反袁有一个过程。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结束亡命生涯,由日本回国。面对当时的中国政局,梁启超寄希望于袁世凯,幻想通过袁世凯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由开明专制,逐步推行民主政治,所以,梁启超一回国,便站在袁世凯的阵营,入主“第一流人才内阁”,为袁氏政权指点江山。但当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刚露端倪时,便写信给袁世凯:“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立国于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愿大总统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5-716页。)劝袁世凯悬崖勒马、急流勇退。并于六月份,与冯国璋一起晋见袁世凯,再次力陈帝制运动的危险,劝袁再三思考,不要走自取灭亡的危险道路。当帝制浪潮翻滚而来的时候,梁启超再也忍耐不住,写下了那篇传诵一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批驳了古德诺和筹安会关于非改共和为君主不能立宪的谬论,抨击了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在当时一片帝制的鼓噪声中,梁启超这个曾经是袁世凯身边的名人、舆论界的“骄子”发出如此强烈的论调,像惊雷一样,在当时的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正如蔡锷所说:“帝制议兴,九宇晦盲。吾师新会先生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故不足以动天下也。”(云南社会科学院、贵州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护国文献》(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13页。)
然而,有人认为梁文是“对袁世凯的刻骨镂心的忠谏之书”,“字里行间,跳动的仍然是梁启超那颗忠于袁世凯的赤心”。且不说,此文原稿比见诸报端更为激烈,其中有一段专斥帝制之非,并说:“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21页。)后来因有人说袁世凯当时并未承认有称帝之意,初次商量政见,不必如此激烈,所以将这段删去,其余各段也经过修改,语气比原来平和多了。从另一方面说,辛亥革命后,善于伪装的袁世凯在梁启超归国后,大加赏识,对梁来说有“知遇之恩”,作为人臣,梁文语气中肯,应该算是合情合理的。但通过这篇文章,梁启超也表明了自己反袁称帝的立场,否则,袁在得知梁的文章后,何以先是以二十万元巨款作筹码,要梁放弃发表这篇文章,遭到拒绝后又派人威胁、恐吓呢?但这些都没有动摇梁的立场,他在给女儿的信中愤怒地说:“吾不能忍,已作一文交荷丈带入京登报,其文论国体问题也。若同人不沮,则即告希哲,并译成英文登之。吾实不能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0-721页。)从中可以看出梁反袁称帝的坚定立场。
除此之外,梁启超在护国运动爆发后,还写了《军中警告国人》、《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袁世凯之解剖》等战斗檄文。因为梁启超同袁有着数年打交道的经验,对袁相当熟悉,所以,对他的抨击往往能击中要害、矢矢中的。如在袁世凯取消帝制后写的《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中,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勾画出洪宪皇帝出生图,又说:“以总统为未足,则觊觎皇帝。若皇帝做不成,则又谋保总统。险诈反复,卑劣无耻,一至此极。”这些言论,对激励人们投入护国战争的行列,将反袁斗争进行到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护国战争策划和组织的参与者
对于袁氏称帝,梁启超一开始苦口婆心地劝告,之后制造舆论反对,当这一切都阻挡不了袁氏称帝的逆流时,梁便决心以武力反袁,其在天津的寓所成为反袁志士策划反袁的秘密机关。对此梁启超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说:“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余曰: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密图匡复。蔡君韪其言,故在京两月,虚与委蛇,使袁氏无复疑忌。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又招戴君戡来京面商。……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乃与蔡君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庐。此后种种军事计划,皆彼时数次会谈之结果也。”其中,在1915年11月11日,梁启超、蔡锷、戴戡在天津共同商定了反袁大计,决定在袁氏下令称帝后云南即独立,黔、贵随后相应,然后合力下川、粤,会师湖北,抵定中原。以后护国战争大致便是按照这一方案进行。天津计议后,蔡锷在梁启超的精心安排下,潜回云南,兴师讨袁;梁自己也于1915年12月16日躲过密探监视,冒着生命危险,从天津乘船去上海,秘密指挥反袁武装起义。1915年12月23日,蔡锷、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联名发布的《云南致北京警告电》,25日的《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电》以及以后的《云贵致各省通电》、《云贵檄告全国文》均由梁启超代拟。在护国战争中,梁启超、蔡锷虽远隔千山万水,但密电不断,“每书动二三千言,指陈方略极详”。(云南社会科学院、贵州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护国文献》(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203页。)另外,梁启超与唐继尧等也是书信不断。
关于梁启超参与和组织护国战争,有人认为他是“夺功”,并对其所说的代拟电文产生怀疑。功劳不是靠夺的,而是靠行动。且不说蔡锷也承认说:“当去岁秋冬之交,帝焰炙手可热。锷在京师,间数日辄一诣天津,造先生之庐,谘受大计。及部署略定,先后南下。”(云南社会科学院、贵州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护国文献》(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272页。)护国起义的提前爆发,便是因为梁启超到达上海后,得到消息说袁世凯准备以重要权力让与日本,并派周自齐为特使克日赴日本。梁感到,如果让袁世凯与日本的卖国交易做成,必然给护国运动带来更大的阻力,所以急电蔡锷,要求提前起义。在关键时刻,梁当机立断,表现了一个政治家敏锐的判断力。关于有人怀疑梁代拟的文电,亲自参加护国起义的白小松说:“护国初期诸文皆由梁新会在外撰就,文由蔡公带滇发表,梁于计算蔡到滇后,即先以所撰原文,在外先行揭登报章。殊蔡将稿带到之后,迭经会盟诸人研审,或加以局部修改,或悉将全篇废弃。一则照登梁氏初稿,一则根据实际之定稿,遂致有此差异,局外之人无从知此底蕴。”白小松:《护国运动初期文电各种记载每多歧异之原因及其订正》,云南《正义报》1943年12月15日。由此可见,梁确实起草了护国战争的部分文电,但由于其不在现场,云南护国运动领导人根据实际情况对电文作了修改,也很正常,但我们不能由此否认梁启超在其间的贡献。
除此之外,梁启超尤其重视云南起义的经费,因为在他看来“滇以贫瘠之区发出巨难,糈饷之出至为艰巨”,(《护国大事记》,第126页。)所以主张先将盐税全部充作起义之用,并将稽核分所的外国办事人员护送出境;其次,建议护国军充实银行。另外,派其女婿到南洋募捐。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坚持每日写文章,制造舆论,联络各省以揭露帝制真相,争取国内外对护国战争的更多支持。
三、反袁联合战线的促成者
护国战争爆发后,梁启超除了频繁地函电各省,促其响应云南起义,同时为促成反袁各派政治力量的联合而积极奔走。
策动广西独立,是关系护国运动成败非常关键的一环,而广西独立又和梁启超的积极奔走、运筹帷幄分不开。当时蔡锷率领不足万人的疲惫之卒,与数万北洋军在四川泸、叙之间进行着十分艰苦的战斗,整个护国战争一时呈现出胶着相持的沉闷局面。梁启超为促成广西独立,一面写信给陆荣廷交涉,一面又冒着生命危险,亲赴广西,商讨反袁事宜。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此行乃关系到滇黔生死,且全国国命所托,虽冒万难不容辞也。”(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5页。)梁启超的冒险之行,促成了广西独立。这给蔡锷以及全国的反袁斗争以极大的支持,护国军乘胜反击,使云、贵、川、桂联成一体。蔡锷说:“当锷极困危之际,突起而拯拔之,大局赖是以定。”《护国文献》。广西独立对袁世凯是重大一击,在袁氏党徒中反复折冲了多时而没有发出的取消帝制的通电终于在3月22日以袁世凯的名义发表了。护国运动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对袁世凯手下的北洋军阀将领,梁启超采取了分化政策。他深知北洋派系内部以冯国璋、段祺瑞为代表的消极反袁力量,在袁氏帝制活动中持旁观立场。所以他“居沪七十余日,除筹划滇、黔、桂三省举义各事外,以运动冯华甫起义事为重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7页。)梁启超争取南京冯国璋的工作,做得很有成效,减轻了北方军队对护国军的压力。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尽力联合国民党的温和派,一方面与黄兴书信来往联络合作之事,又于1916年3月11日,在赴广西途经香港时与李根源、杨永泰会面,商讨了两党合作反袁的计划。
真正体现各党各派实现大联合的是1916年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的护国军军务院,它既包括了革命党人,也包括了进步党人,还包括了以唐继尧、陆荣廷、蔡锷等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其中,梁启超可谓是军务院的灵魂。另外,章士钊、李根源等许多国民党人都担任了极其重要的职务。这说明了梁启超减少了党派偏见,以反袁大局为重。尽管军务院名为南方统一政权,实际上从未形成强有力的统一领导;但军务院在帝制撤销一个多月后成立,这本身就表明护国军和西南独立各省对袁世凯北京政权的否认,表明了同袁世凯继续斗争的立场和决心。它进一步壮大了护国军威,鼓舞了全国人民,推动了护国运动的发展,加速了袁世凯的灭亡。“军务院的成立,滇、黔、桂、粤联军西南,声震全国”,《护国大事记》。其“声威振动,使袁世凯知西南不可屈焉”。邓之诚:《护国军纪实》,邓氏玉石斋1937年刻本。
关于梁启超参加护国运动的动机,有人认为他是“抢旗”、“投机”,以此来否定他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论从史出,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此作一历史的分析。随着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步伐加快和表面化,全国各阶层、各党派都投入了反袁的行列。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无疑是最坚决的反袁力量,但由于他们力量分散,又缺乏群众基础,因而始终未能抓住护国运动的领导权。西南地方实力派尽管有军事力量,但他们各自为政,谁也不肯拿自己的政治宝座做赌注,也缺乏一个纽带将他们联合起来。此时的工人阶级还未登上政治舞台。而以梁为首的进步党在舆论上比较主动,受到了大多数反袁人士的支持和拥护;他一方面利用与蔡锷的师生关系联合西南地方实力派,另一方面又通过与北洋实力派人物的历史渊源,对其进止产生影响,所以这一时期的梁启超及进步党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了最精彩的一面。还有人说梁启超决心发动反袁的护国起义是因为他看到在袁氏加紧进行帝制的时候,各种反袁力量也在酝酿和积聚,袁世凯的垮台是没有疑问的。这是典型的“先验论”。试想,当蔡锷以不足万人的疲惫之卒与数万北洋军交战的时候,当梁启超冒着生命危险去广西的时候,有谁能肯定反对袁氏的护国运动会取得胜利?如果仅是“投机”革命,当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又企图通过拉拢梁启超等进步党人进内阁,换取进步党人的让步,以求继续霸占总统职位时,梁何不与之媾和,获取一要职?而是明确表示:“袁逆取消帝制,希图调和,万无许理。”“现舍袁退位外,对北京断无调停之余地。”(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33页。)从梁个人利益讲,他也没必要“投机”,凭着其社会威望和学识,并非除了反袁就别无出路。梁启超若从个人安危、名利考虑,可以退出政界、专门搞学问从事教育,或干脆与袁氏合作;然而,他却不这样做,在袁世凯的金钱诱惑与威胁面前,正义凛然,为广西独立,“蛰伏运煤船舱底,不见日者八昼夜”。若仅出于私心能做到这些吗?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不能说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但纵观其在护国运动中的表现及其产生的客观效果,我们应充分肯定他的积极作用。不能因为他曾经保皇、拥袁而形而上学地否定他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进步性,否则就难以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还历史以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