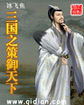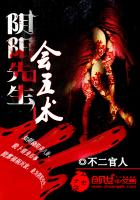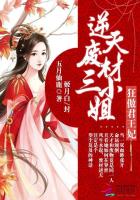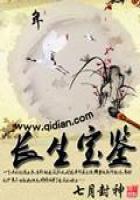方印华
“赤脚医生”这个名词对我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不仅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那个农村缺医少药的年代,还是救死扶伤的象征。
1968年一个寒冷的傍晚,大队干部到我家中,说是要推荐我去参加大队卫生员的培训。这一推荐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在当地农村算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几天之后,我就接到了一张油印的通知,上面还盖有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印章。通知明确规定,每个参加培训的人员必须带铺盖、米和饭盒,地点在观城东门的干校内,时间为两个月。
这次参加培训的人很多,观城区范围,共有一百多人,分为几个班。当时我们这些初学医者,经历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领域;也有几个例外,他们在部队当过卫生员,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在学习中就会轻松得多。我虽然在此前没有从医的经历,但家中有两本书我曾经看过,一本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的《家医》,其内容有维他命对于人体的重要性、淘米会使营养流失、疟疾是由蚊子传播的以及蛔虫、钩虫等寄生虫病的防治等。另一本是手抄本,据我父亲说是我的曾祖父摘录的,内容有雄黄散的制作方法、伤风感冒的治疗偏方等。原来在看这两本书时,似懂非懂,但一到学习班上,我也算是有一点儿医学知识的人了。
学习班学习的主要课程分为三大部分。标点与字的间隔加大一是急救处理,如清创包扎、人工呼吸、担架固定等;二是中草药和针灸;三是常见病的防治。任课老师有观城区卫生院的张迪蛟、卫前卫生院的吴达封、附海卫生所的岑岳灿等。在学习针灸时,每位学员还要实践,那就是每人拿银针在自己的身上反复试验练习。我自己练习的穴位有合谷、足三里、曲池、内关、外关等。
在学习结束前,还有一次专门的采集中草药实习。我们卫前公社二十余名学员来到了龙山,住在虞氏旧宅,前后大约一个星期。回家时已近年关,二十几个人用几辆手拉车装着铺盖和采集的草药标本,步行回家。一路上,天还下起了鹅毛大雪。
春节以后,我们再次集中到卫前卫生院实习。当时卫前卫生院有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中医科等科室,我们轮流到每个科室实习一星期,又到药房、注射室学习配药注射等基础知识,因为这一期是实践操作,在学习班里是无法学到的。待到实习一结束,大家就回到各自的大队,开始承担防病治病的重任。
农村的防病工作,当时是十分重视的。每年都要接种麻疹、“百白破”三联、卡介苗、牛痘、流脑、乙脑、小儿脊髓灰质炎、霍乱等各类疫苗。另外,还在流感季节用板蓝根大青叶煎汤,乙脑流行季节用千筋草煎汤,让每个社员喝,而且全部免费。还要一年两次检查钉螺,防止血吸虫病蔓延。到了夏季,要用漂白粉对水井消毒,防止肠道传染病蔓延。这些工作都是由各村的赤脚医生来完成的。从1969年到1983年的15年间,至少在我们村没有发生过一例急性或烈性传染病。
我不敢说自身医术有多高明,但在当时的赤脚医生队伍中,应该算是还可以的。当时农村的外科,主要有清创处理、缝合包扎以及疮疖痈肿的手术治疗。疮疖的治疗除了口服或注射抗菌素外,很关键的是外科开刀。开刀以后,排出脓血,同时还要使用引流物。我们在学中医时使用“油润”,一种用牛皮纸搓成的小纸条,熏上一些药粉后插入脓肿部位。
另一种是西医的方法,叫做凡士林纱布引流。对于刀口较大的一般用凡士林纱布,较小的用“油润”,效果很好。内科的疾病在于诊断。我们的诊断器械是一只听诊器,一支体温表,一块压舌板,一只血压器。除此之外,就是触摸、叩打。中医的望问闻切虽然也了解一点,但在实际应用中显得力不从心。这样,对疾病的诊断主要是采用西医的方法。
为了准确诊断和对症治疗,我当时买了很多书,一有空就看这些医疗知识的书籍。经过几年的实践,发现那些为赤脚医生特别编写的书籍内容过于浅显,于是就去购置《内科学》、《外科学》等书籍,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套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出版的《实用内科学》。其他诸如《皮肤病手册》、《眼科疾病手册》、《肿瘤病防治手册》等书籍,对于我们这些赤脚医生来说,其中内容都是应当了解和掌握的。
另外一个学习的途径,就是不断地向专业医生请教。一些专用的医学术语和医学名词,如惊厥、昏迷和休克的特征及病因,对光反射、膝反射等的临床意义等,在原先学习时根本就不可能涉及,但在自学时又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术语,要想切实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老老实实向专业医生请教。所以那个时期只要一有空,我就去两个地方,一是新华书店,一是医院。在医院有时一待就是半天,看着医生诊断的步骤、方法、检查的要领以及处方的开具等,我逐渐对于一些疑难病症也有了肤浅的了解。我常常听医生们说:病人不会照书生病。这句话的意思是,同一种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有可能完全不同。有一次,一位村民的头颈后长了一个小小的疖子,因为表面有一个白色的小脓包,他就用手去挤压,把小脓包挤破了。不料第二天却发起了高烧,叫我去诊断。我用体温表一量,体温竟高达40℃,浑身伴有寒战。经过询问病历,又看了后面的一个小疖子,明显红肿扩大,我怀疑他得了败血症,建议马上送县人民医院治疗。当天晚上,病人就送到了区卫生院。后来他的家人回来告诉我,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否则有生命危险。
做赤脚医生可以说是有苦也有乐。苦的是经常半夜三更有人来叫,我必须起床,背起药箱出诊。农村最常见的是小儿高热惊厥和腹痛腹泻发病。小儿高热惊厥一般都由上呼吸道感染所致,晚上发病居多,而腹痛腹泻等胃肠道感染也在晚间居多。有时候一个晚上要起来两三次。腹痛腹泻病人都需要输液,所以待处理完一个病人需要一到两个小时。看到病人腹痛缓解,安然入睡,心里就感到很高兴。尽管第二天还要出工干活,因当时年纪轻,精力充沛,睡几个小时也就足够了。这种晚间出诊,都是不计报酬的,而且又是上门服务,极大地方便了就医的群众,故过半数赤脚医生在农村是很受欢迎的。
对于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治疗,我也曾下过一番功夫。我们村有一户人家,兄弟姐妹5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这户人家的长子经常一人坐在门口,两脚不能走路,双手颤抖不止。在我担任赤脚医生之后,此人已经死亡。不料,他的弟弟在二十几岁时也出现了与他哥哥同样的症状。我曾经把他的病状特征写成一份材料,去相关医院求教。当时医生也说不出具体的病因病名。有一次,我的一位堂哥来我家做客,他是浙江医科大学毕业生,后来分配在台州的一家医院。我向他请教,他说,这很有可能是帕金森病,主要病源在大脑。我去查阅了很多书籍,后来在一本药物学中查到一种叫做“安坦片”(又名苯海索)的药剂可以治疗这种病。不过,当时反对崇洋媚外,帕金森病叫做震颤麻痹。后来这位病人到杭州去检查治疗,医生给他配的也是这种药。另外有一次,一位五十余岁的男性病人突然不能排尿,憋得他面红耳赤,痛苦呻吟。我过去一看,知道这可能是急性尿潴留,需要导尿或膀胱穿刺抽尿。一来从未做过这类手术,二来也没有设备,就只能将病人抬到医院。因为这人是个单身汉,我又叫来另外一个人,一起把病人送到观城区卫生院,在医生治疗过程中,我留意观察,后来也做过一次膀胱穿刺。为了学到更多的医学知识,我经常主动陪护病人去医院,这对提高我的治疗水平和诊断水平很有帮助。
针刺疗法是赤脚医生必须掌握的一门医术。如用三棱针点刺小儿手指第二关节横纹中治疗积食,针刺后溪穴和压痛点治疗急性腰扭伤,对偏头痛、三叉神经痛、牙痛使用针灸也很有疗效。同时对胆道蛔虫症、胆囊炎等引起的疼痛,针刺也有一定的辅助功效。对于那些肌肉劳损、关节劳损、坐骨神经痛等慢性疾病,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但在整个赤脚医生队伍中,使用针刺治疗的并不普及,这主要取决于赤脚医生本人的技术与胆识以及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度。如果提出的治疗办法病人加以拒绝,就会使针刺治疗无法实行。而这种拒绝一旦过多,也会使赤脚医生的信心失去支撑。所以,在农村要推行一种新的治疗方法,除了医术外,还得进行必要的宣传。我就曾经反复向病人或村民讲解针刺的原理,对人体的无害、对治病的作用等,当然这些讲法现在看来找不到严格的科学依据,但确实起到了效果,在一般情况下,我提出的针刺方案,病人是不会拒绝的。病人的信任也给我增添了勇气,也使医术在实践中得以提高。
我们曾经去采过几次草药。记得有一次是到奉化,住了近10天时间。采药是到奉化的一座大山深处,山上有很多山蚂蟥。尽管我们穿着厚厚的布袜子,但这些山蚂蟥还是钻进了袜子,拼命地吸血。回到住处,奉化大桥镇的一个招待所,脱下袜子,满脚流血,又痒又痛。当时有两个草药郎中是我们的“师父”。一个是五里的韩尔康,另一个是前方村的方绍伦。他们对草药比较熟悉,不但能叫出名字,而且还知道这些草药的功用。特别是韩尔康,原在观城大街上设摊卖药,是个经验很丰富的草药郎中。在奉化山上我们采集到最多的是淡竹黄和仙鹤草。据说用淡竹黄浸泡的酒,可以治疗风湿疼痛,而仙鹤草则是止血良药。回来以后,我们集中把仙鹤草晒干后,送到中药制片厂加工成片剂。但这两种药的实际效果如何,我们没有做过跟踪调查。利用中草药治病,在当时不但提倡,而且流行,但有的病人对这些药却抱有怀疑态度。他们宁愿出钱买西药,也不愿要免费的中草药,所以中草药治病在我们这个地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文革”结束以后,由县卫生局统一组织赤脚医生进行了考试,合格的发给一本红红的“赤脚医生证”,不合格的不发。从严格意义上说,没有取得证书的赤脚医生将失去行医的资格。后来又组织了一次考试,名称也由“赤脚医生”改为“乡村医生”。当时我已经到乡文化站工作,从此脱离了赤脚医生队伍。
在初涉赤脚医生时,有一个很轰动的例子,大概叫做“打开禁区”。说的是洛阳某部的一位军医,叫赵普生,用针刺治疗聋哑人,因为治疗这种先天性的疾病需要针刺一个叫做“哑门”的穴位,而这个穴位在颈椎第三与第四节之间,还说这里有“生命中枢”之称,向来被视作针刺的禁区。而赵普生却在自己的身上大胆实验,并获得了成功,就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后来又推广针刺麻醉,我们曾参加过短期的学习,但并没有在实际治疗中应用。
在赤脚医生培训期间,学习最多的是毛泽东的“6·26”指示。在一些医院内,都挂着大型横幅,上面写着“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旁边还贴着“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等标语作为陪衬。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确实存在。农民一旦有病,就必须到几里地外的医院就诊,又加之当时的交通不方便,一个病人又需要两三个人陪护,确实给病人及其家庭带来极大不便。从这一点上说,赤脚医生在农村,为缓解缺医少药起到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