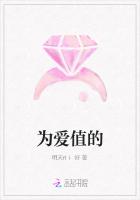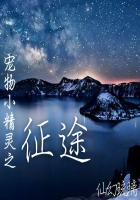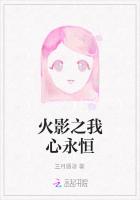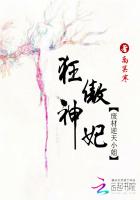史传与辞赋,一个求真实,一个务华丽;一个刻画人物,一个铺排事物,是有本质上的不同。但在唐前史传文学中,可以把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唐前史传文学中,收录、保存了大量的辞赋,也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赋论资料。
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对《史记》、《汉书》等史传著作收录辞赋颇有微词,他说:“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刘知几从劝善惩恶的实用功能出发,对《史记》、《汉书》收录辞赋予以否定,而没有看到史传收录辞赋的积极意义,因此,这一问题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一、史传中的辞赋
(一)史传收录辞赋概况
史传著作中收录辞赋作品,这是表现人物才能、个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史传在描绘历史人物的时候,除了选择传主的典型事例外,还适当选择他们的辞赋作品,以表现其才能、个性。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文学家、辞赋家的传记,通过他们创作的作品,表现出他们在文学史、辞赋史上的地位。以汉赋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来说,他们在汉赋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司马相如,是汉大赋的首要人物,《史记》、《汉书》都收录了他的代表作《天子游猎赋》(即《子虚》、《上林》二赋)、《哀二世赋》、《大人赋》等,充分显示出司马相如的文学才能。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又一辞赋大家,《汉书》对他特别关照,除收录《解嘲》、《解难》、《反离骚》外,还全文收录了他的大赋《长杨赋》、《羽猎赋》、《甘泉赋》。班固的作品,除《汉书》收录《幽通赋》、《答客戏》外,《后汉书》将他的大赋代表作《两都赋》全文收录。张衡作为汉大赋向抒情小赋过渡的重要人物,《后汉书》收录了他的《思玄赋》、《应间赋》。如果说,大赋作品主要表现人物铺排事物的才能的话,那么,抒情性的小赋则更能表现人物的个性以及当时的心态。如汉初贾谊,《史记》、《汉书》收录他的《吊屈原赋》、《服鸟赋》。《吊屈原赋》一方面凭吊战国时代的屈原,另一方面也寄寓着作者本人的不遇之感。《服鸟赋》则是他处在逆境时老庄消极避世思想的反映,给我们提供了贾谊在当时情况下的真实思想。东汉时期的赵壹,是一个刚直不阿的人物,因而《后汉书》收录了他的《刺世疾邪赋》,表明作者“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的倔强个性。《宋书·隐逸传》中收录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表现陶渊明喜欢大自然、不愿同流合污的人格精神。另外如《后汉书》收崔篆《慰志赋》、《宋书》收谢晦《悲人道》,《魏书》收李骞《释情赋》、李谐《述身赋》、袁翻《思归赋》等,都是具有自传性的作品,它们是作家个人性格的真实表现。“言为心声”,从传记写作来说,作家的作品就是第一手材料,是人物心态的真实写照,将它们直接用于传记之中,使作品更具有真实感,也最能体现人物的个性。章学诚指出:“马、班二史,于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著于列传,自刘知几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
盖为后世文苑之权舆,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实绩,以视范史而下,标文苑而止叙文人行略者,为远胜也。然而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于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于以文传人也。”后来刘熙载说得更明确:“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于赋寓之。《史记》、《汉书》之例,赋可载入列传,所以使读其赋者既知其人也。”章 刘二家的看法,无疑是公允的。因此,史传中收载辞赋,是“以文传人”的重要手段之一。
有时,史传著作的“书”、“志”为了说明问题,常常引用辞赋的某些句子。以《宋书》为例,《律历志》论及道神时,引嵇含《祖道赋序》以说明;《乐志》论及聘享之礼,引王沈《正会赋》、何桢《许都赋》、傅玄《元会赋》以说明;论及禊祠之礼时,引张衡《南都赋》、刘桢《鲁都赋》,论乘舆之礼时引潘岳《籍田赋》等;《乐志》介绍乐器时,也征引辞赋的句子,如引用傅玄《节赋》、马融《笛赋》、傅玄《筝赋》、《琵琶赋》、杜挚《笳赋》等。这些著作,把辞赋当作《周礼》、《礼记》一类的经典著作来引用,亦可见辞赋的特殊作用。
史传由于受体例限制,不可能把辞赋全部征引,但为了让世人知道辞赋作家及其作品,就往往在传记中指出作品的题目,并说“文多不载”。或在传记结尾,总说其创作辞赋的成就,如《后汉书》的许多传记,在最后指出:“所著赋颂铭诔箴论××篇”。
(二)史传收录辞赋的意义
史传中保存辞赋,其积极意义在于:
第一,使史传作品形成散韵结合的特点,增添了诗的韵味。先秦时期的史传作品,往往引用人物的大段说辞,如《史记》以来的正史著作,通过人物自己的辞赋作品以表情达意,可以说是先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辞赋,一般都是介于诗与文之间的文体。在散文叙述中,适当加入一些韵文,使读者在阅读历史时,也阅读到精美的文学作品,引起美感。
第二,在历史著作中收录辞赋,这本身也是历史著作的责任。历史著作,要全面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文学的发展,也是意识形态领域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因而,辞赋作为文学的一种,收入史传中,这体现了历史著作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程度。
第三,史传中收录辞赋,也反映了史传作家对文人的态度。辞赋家,往往被视为“倡优”一类的人物,地位卑下。史传中给辞赋家立传,并收录他们的作品,这体现出史传作家超世俗的精神和胆量。
第四,史传中收录辞赋,是文学向着自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一般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是从魏晋开始。但这个局面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史记》、《汉书》收录辞赋作品,已露出端倪,即在司马迁时代,已昭示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详见附《司马迁与司马相如论略》一文)。
如果从收录的作品本身来看,它的意义也值得重视。
首先,这些辞赋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它们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如汉大赋,它是汉帝国兴盛强大的形象性反映。如果没有政治的大一统、经济的繁荣、军事力量的强大等社会条件的成熟,就不会有歌功颂德的汉大赋。还有些辞赋作品,或揭露社会的黑暗,或抒发作者的个人情感,或描写祖国的大好河山,使我们透过字词的表层,看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其次,展现了赋的发展历史,为研究辞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成熟于战国时代。我们从《史记·屈原列传》可以看出,当时的赋,尤其是屈原的赋,以抒情为主,篇幅短小。汉初的贾谊,继承了这种传统,我们从《贾谊列传》所收的《吊屈原赋》、《服鸟赋》可以明显看出其特色,以骚体的形式,抒发个人内心的情感。但我们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传记中所收的作品,又可以看出,辞赋到他们手里,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仅篇幅巨大,而且主要用于铺排事物,这种散体大赋,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许多辞赋。东汉后期,这种辞赋的数量相对减少,而抒情性的短赋又兴盛起来,如赵壹、张衡等人的作品。这种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仍占主流。仅从《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所收录的作品看,它们或咏物以抒情,或借物以刺世,或感物而兴叹,或借古以喻今,各式各样。尤其到南北朝时期,辞赋语言也愈工整、华丽,骈体化倾向较为明显,如《海赋》等作品。
如果我们将史传中辞赋所表现的这一发展概貌,与辞赋史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两者是十分吻合的。
二、史传中的赋论
唐前史传不仅收录保存了许多辞赋作品,而且还保存着有关赋论的珍贵资料。将这些零散的资料加以整理,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论赋的发展
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在战国时代产生,到汉代达到兴盛。《汉书·艺文志》对先秦两汉时期的辞赋进行了整理,分为四大类: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并且对赋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概述: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班固将赋的源头追溯到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然后对汉代的辞赋大家予以评论。从这段话可以明显看出,班固将赋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赋如孙卿、屈原,属讽谏性的赋,即属“诗人之赋”;第二阶段从宋玉、唐勒,到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失去了讽劝之义,属“辞人之赋”,注重的是辞藻。班固的这种看法,与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所说的“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具有一致性。
可见在汉人的眼里,赋的开始阶段每以讽喻为其主要特征,之后,逐渐走向了追求华丽辞藻的道路。《宋书·谢灵运传论》对此期的辞赋发展作了更为详细的总结:
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扬(雄)、班(固)、崔、蔡(邕)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张衡)艳发,文以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曹操、曹丕)陈王(曹植),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曹植)、仲宣(王粲)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
沈约将屈原以后的辞赋归纳为“文体三变”,即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基本符合事实,尤其是以建安作为一个转折点,颇有眼光。以上史传中的材料,大体勾勒了赋的历史概貌,与辞赋作品所表现的发展过程相得益彰,对于今天的辞赋研究还是很有价值的。
(二)论赋的作用
对于赋的作用,历史家、辞赋家异口同声,都认为赋的作用在于讽谏。从司马迁到班固,乃至于魏晋南北朝,都有共同的看法。如司马迁评价司马相如的赋:“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太史公自序》也说:“《子虚》之事,《上林》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讽谏,归于无为”,肯定相如赋有讽谏作用。班固基本继承了这一观点。另在《两都赋序》说赋“或以抒下情而通风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也是强调赋的美刺作用。扬雄对赋采取始肯定又否定的态度。《汉书·扬雄传》说:“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于是辍不复为。”扬雄对赋杀了个“回马枪”,由肯定到否定,其出发点都是一样的。肯定它,意欲起讽谏作用,否定它,是由于起不到讽谏作用。另外如《三国志·刘劭传》说刘劭尝作《赵都赋》、《许都赋》,“皆讽谏焉”;《魏书·阳固传》说:“初,世宗委任群下,不甚亲览,好桑门之法。尚书令高肇以外戚权宠,专决朝事,又咸阳王禧等并有衅故,宗室大臣相见疏薄,而王畿民庶,劳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赋》,称恒代田渔声乐侈糜之事,节以中京礼仪之式,因以讽谏。”诸如此类的评说是很多的,足见赋的功能在于讽谏。尽管赋往往被人斥为“劝百讽一”,但其讽劝的功能还是存在的。正如《后汉书·边让传》所说,《章华赋》“虽多淫丽之辞,而终之正,亦如相如之讽也。”关于赋的另一作用,即娱乐功能,史传中亦有记载。汉代皇帝,据《史记》、《汉书》记载,“景帝不好辞赋”。但汉武帝对辞赋颇有兴致,他不仅大力提倡,而且自己创作。《汉书·艺文志》说他有辞赋两篇。《汉书·外戚传》全文收录了他的《李夫人赋》。汉武帝周围,还有一大批辞赋家,朝夕献赋。汉宣帝对辞赋的认识值得注意。《汉书·王褒传》记载宣帝一段话:“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比如女工有绮,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娱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宣帝既注意到辞赋单纯的娱乐作用,又注意到它的教化作用,当然,两者相比,前者价值是“小”的,后者作用是“大”的,因为,“大者与古诗同义”,具有重要的道德作用。
(三)创作论
唐前史传在收录辞赋作品时,对于它们的创作背景都有一定的介绍,属于“赋本事”,这对于我们了解作品的内容很有帮助。如《史记·屈原列传》明确指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深刻揭示了《离骚》创作的社会背景。《贾谊传》说:“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号鸟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号鸟曰服。贾生既已适(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后汉书·张衡传》:“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者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后汉书·赵壹传》:“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乃作《解摈》。后屡抵罪,几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贻书谢恩曰:余畏禁,不敢班班显言,窃为《穷鸟赋》。”《三国志·曹植传》:“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裴松之注引此赋)《魏书·自序》:“出帝尝大发士卒,狩于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时既寒苦,朝野嗟怨。帝与从官皆胡服而骑,宫人及诸妃主杂其间,奇伎异饰,多非礼度。收欲言则畏惧,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赋》以讽焉。”
以上所举几例,旨在说明:史传中对辞赋创作背景的介绍,是我们认识和研究作家、作品的一个重要线索,通过这个线索,我们可以认识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创作主旨及创作风格。
实际上这已经涉及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任何一个作品的产生,都不是作家凭空虚构的,而是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连,即使那些带有夸张、浪漫色彩的辞赋,也没有完全脱离现实。
关于辞赋的创作,我们从史传中还可以看到一些规律性的问题。如《南齐书·文学传》收有《陆厥与沈约书》,论及赋的声律问题:“《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孟坚精正,《咏史》无亏于东主;平子恢富,《羽猎》不累于冯虚。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杨修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赊于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坏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齐朝永明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文人在诗歌、辞赋创作方面都注意到声律问题,沈约就是“永明体”诗歌的代表人物。这封书信,就是探讨辞赋中的声律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当时辞赋创作的特征,也是很有帮助的。
(四)作家论
唐前史传对重要的辞赋作家都立了传,并对他们的创作特点及个性有一定的介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史传文学本身就是刻画人物个性,描绘人物的一生,这对于我们认识作家是极好的资料。虽不是直接进行作家评论,但实际上给读者提供了了解作家的第一手材料。何况,有些传记本身就是作家论。如《史记》的《屈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汉书》的《贾谊传》、《司马相如传》、《扬雄传》,《后汉书》的《班固传》,《宋书》的《谢灵运传》等,都是典型的作家论式的传记。尤为可贵的是,有些作家论还将人格与创作风格联系在一起,使读者能更进一步了解作家的创作情况。如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将屈原高洁的人格与他的创作联系在一起。指出:“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的人格与作品,都可以与日月争光。甚至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可见司马迁对屈原人格与作品的推崇。
(五)作品论
史传著作除了对作家的创作有些涉及外,常常还论及到某个具体作品。如:《史记·屈原列传》论《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后汉书·崔传》评《四巡颂》:“辞甚典美”;评《达旨》:“拟扬雄《解嘲》”;《后汉书·王延寿传》:延寿“作《灵光殿赋》、《梦赋》。蔡邕亦造殿赋,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后汉书·张衡传》:“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三国志·正传》评《释讥》:“其文继于崔《达旨》,假文见意。”《宋书·谢惠连传》评《雪赋》:“以高丽见奇。”《南齐书·张融传》评《海赋》:“文辞诡激,独与众异。”《魏书·高允传》评《代都赋》:“亦《二京》之流也。”《魏书·封肃传》评《还园赋》“其辞甚美”。《魏书·自序》评《南狩赋》:“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
如果我们将散见于史传中的作品评论汇集在一起,数量也是比较可观的。清代李调元的《赋话》,其中的许多资料就是来自于这些史传作品。
另外,史传中对于辞赋作家在当时的地位亦有所反映。如《汉书·枚皋传》:“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曼戏,以故得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严助传》:(武帝)“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汉书·王褒传》:“其后,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辞赋家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他们被视为“倡优”一类的人物,只是皇帝身边的侍臣,奉命作赋或诵赋,供皇帝解闷、消遣。
三、史传对辞赋的影响
史传文学,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辞赋的宝贵资料,而且,从艺术渊源上说,史传对辞赋的产生与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
(一)影响辞赋的产生
关于赋的产生原因,人们有许多说法。笔者以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值得重视。“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然后说到春秋时代各国外交活动“赋诗言志”的情况,而春秋以后,聘问歌咏不行于国,于是贤人失志之赋出现。班固虽未直言“赋诗言志”与赋的关系,但我以为这段话很给人们以启发。“赋诗”为了“言志”,而这种活动本身就是假借别人之言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增添婉转的风格,其中有许多也是借诗来讽刺时事。《左传》所记,晋公子重耳至秦,秦穆公享之,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鲁文公如晋,晋襄公享之,赋《菁菁者莪》。郑穆公与鲁文公宴于,子家赋《鸿雁》。齐国庆封两次到鲁国,因为举止失礼,叔孙豹先后用《相鼠》和《茅鸱》(逸诗)来讽刺他。又如昭公二年:“公享之。季武子赋《绵》之卒章,韩子赋《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赋《节》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遂赋《甘棠》。
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按班固的意思,到了春秋以后,这种活动消失了,失志之士的赋又产生了,而这种赋,也是以假借的形式,托别人之口(或问答形式)来抒发感情的。由于当时赋诗言志的具体情况,就保存在史传著作《左传》一书中。因此,有理由说,史传对辞赋的产生也有促进作用。赋的特点在于铺陈,乃至于用夸张手法来描绘事物,这种特点也与先秦史传著作《战国策》所记述的纵横家言论有关。
战国时代,处士横议,纵横家苏秦、张仪之流,在游说人主时,往往极力铺陈该国地理的优势、国势的强大、国君的圣明、百姓的富饶、战士的勇敢等,以鼓励采纳自己的主张。有时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上至天文,下到地理,从古到今,正反对比,滔滔不绝。如《秦策一》苏秦游说秦惠王时说:
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
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
这种铺张扬厉的形式,无疑影响了汉大赋的铺陈特点。因此,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曾指出:“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式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分别见《战国策》的“楚策”和“魏策”)。《客难》、《解嘲》,屈原之《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将《战国策》的说辞作为赋的源头所在,这是颇有道理的。因此,从赋的产生来说,它与史传有密切关系。
(一)影响辞赋的发展
史传对于赋的发展也有影响,主要有:
第一,为辞赋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唐前史传记载了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内容极为丰富。这给辞赋作家的创作、尤其是一些“咏史赋”的构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扬雄《反离骚》、杜笃《首阳山赋》、李德裕《项王亭赋》、杜牧《阿房宫赋》、苏轼《赤壁赋》、方孝孺《吊茂陵赋》、高启《吊伍子胥文》、管同《哀邹阳赋》等,或是评价历史人物,或是借史传中的人、事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或是借历史人物来抒发自己抑郁悲愤之情。总之,史传中的人或事,是启动辞赋家情怀的重要的原动力。
第二,为辞赋家提供了丰富的语言和艺术的借鉴。史传作品,尤其是先秦两汉时期的作品,语言精炼、优美,富于形象性,为辞赋家提供了大量的语言资料。以用典来说,仅以庾信《哀江南赋》为例,其中大量的典故,来自《尚书》、《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如其中的一段: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辟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日暮”句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之语;“将军”句用《后汉书·冯异传》“大树将军”之典;“壮士”句用《战国策·燕策》中荆轲刺秦王之典;“荆璧”句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完璧归赵”之典;“载书”句反用《史记·平原君传》“毛遂自荐”之典;“钟仪”事出自《左传·成公七年、九年》,“季孙”事出自《左传·昭公十三年》,“申包胥”事出自《左传·定公四年》。窥一斑而知全豹。史传提供给辞赋的是丰富的营养。
第三,为辞赋作者树立了求实批判的精神。刘知几《史通·载文篇》曾批评史传载文的过失,出发点也是从求实原则出发,这种思想意识的积淀,使辞赋作者往往也注意求实,一些自传性的辞赋更是如此。“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谈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因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辞赋作者常常承担起讽刺、批判现实的重任,是史学家的求实精神和文学家的浪漫气质的双重组合。
史传作家人格对辞赋家的影响,像司马迁在逆境中顽强奋斗的精神,以及史传中描绘的屈原等人物的崇高精神,都对后代辞赋家产生影响。
第四,为辞赋的保存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史传,尤其是被确定为“正史”的著作,具有极强的“权威”性。辞赋作品能进入这些著作,等于进了“保险箱”,随着史传的载体,永远流传下去。即使只被列入像《汉书·艺文志》的目录中,也给后人的研究留下了可靠的线索。
当然,辞赋对史传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屈原及其辞赋,对司马迁有极强的感染力,并对司马迁创作《史记》产生积极影响。另外,唐前史传作家中有许多就是辞赋家,他们在创作史传作品时,也创作了一些辞赋作品,如司马迁(有《悲士不遇赋》等)、班固(有《两都赋》等)、魏收(有《南狩赋》等)、萧子显(有《鸿亭赋》等),他们的双重身份,也使得他们对辞赋作品加以重视。总之,唐前史传中保存辞赋,使历史著作有了文学色彩,也使文学作品以史的形式流传,两者相得益彰,使文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无论对于史传还是辞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前人说:“文章西汉两司马”,是说司马相如、司马迁分别代表了汉代辞赋和散文的最高成就,事实确实如此。如果进一步来看,司马相如的赋和司马迁的《史记》,虽属不同的门类,但它们在许多方面却有相同之处。
司马相如是辞赋大家,但辞赋家的地位在当时是非常低下的,被视为倡优一类人物。如枚皋说:“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扬雄写过不少赋,但后来不写了,认为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雄以为赋者……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于是辍不复为。”后来的班固在《两都赋序》里说:“至于武宣之世……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把辞赋家视为“言语侍从之臣”,亦可见地位之低下。对此,鲁迅先生曾精辟地指出:
中国的开国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地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划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它已经“寿终正寝”了。司马相如的可悲结局,代表了汉代辞赋家的共同命运。所以,从结局来看,司马相如的一生也是不得志的。
司马迁对辞赋家却另眼看待,尤其是对汉大赋代表人物司马相如给予“特殊照顾”。他在《司马相如列传》里收入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上书谏猎》、《谕巴蜀檄》、《难蜀父老》、《封禅文》,是《史记》中收文章最多的篇章。这样做,既表现了司马迁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大胆创新精神,也预示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同时也寄寓着作者的自身感慨。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评《司马相如列传》说:《史记》列传,独于司马相如之文采之最多,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可谓倾服之至。而所载之文,又复各呈其妙,不拘一体……驱相如之文以为己文,而不露其痕迹;借相如之事为己照,并为天下后世怀才不遇者写照,而不胜其悲叹。洋洋万余言,一气团结,在《史记》中为一篇最长文字,亦为一篇最奇文字。“借相如之事为己照,并为天下后世怀才不遇者写照”,此话点到要害之处。司马迁作为太史令,“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地位与司马相如一样低下。而司马迁,也是一位怀才不遇的士子,其不幸与司马相如相似,所以,《司马相如列传》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司马迁的影子。比较一下《史记》与司马相如的赋,笔者以为,以下几点应特别注意:
第一,两者都是大一统的产物。西汉王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武帝时达到了鼎盛时期。经济实力雄厚:“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政治地位稳固:镇压了阴谋叛乱的宗室藩王,平定了割据东南沿海的东瓯闽越等地,开发并控制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军事、外交取胜:大力抗击匈奴,开通西域,拓展帝国的疆域。思想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制礼作乐,兴太学,礼五经博士。总之,汉帝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气象。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大赋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既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也表现了时代的精神。正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所描绘的那样: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游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
对于这样的盛世,文人们都充满了自豪感,不由得要进行歌颂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先以子虚夸楚开始,说:“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并极力夸耀楚王游猎云梦泽的规模。
接着,乌有先生以齐国的渤氵解、孟诸可以“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压倒了楚国。最后亡是公以天子上林的巨丽、游猎的壮观,又压倒了齐楚。作者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以天子之事压倒诸侯之事,贬斥诸侯,抬高天子,巩固中央集权。这样的作品,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而“天子之事”中,那种磅礴的气势,宏大的景象,强壮的声威,无不体现着大汉帝国的时代精神。《史记》也是在这样的时代地平线上产生的。随着帝国的日益强大,总结古代以来的历史文化并从而给大一统时代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就成为一个时代的课题。司马迁担当起了这一历史重任,他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诸未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为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圣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之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司马迁的一片肺腑之言,与上引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的一段,是多么的相似。他们有共同的感受,共同的责任感,就是歌颂国家的统一强盛。只不过,司马相如以赋的形式来表现。《史记》“描述了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对世界直接征服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现了‘海内一统’时代人们心胸的开阔,气魄的雄沉,以及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这也是时代的需要,时代的产物。
第二,风格上都有“全”、“大”的特点。司马相如曾说自己创作赋时,“苞括宇宙,总揽人物”,从他作品的实际来看,确实如此。描绘事物时,大肆铺陈,前后左右,东西南北,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凡说到“木”,必将所有地方的树木都移到皇家的苑林来;说道“鸟”,必将天上地下所有的飞禽走兽搬到皇帝的打猎场上,如此等等,无不体现出“全”的特点。
由于求全,所以,作品体制宏大,体现出汉帝国的壮阔气象,摒弃了“小”家子气。而这全与大,正是汉帝国一统天下的真实反映。《史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包揽三千年历史。古往今来,天文地理,无不展现在司马迁的笔下,体现出“全”的特点。而且,《史记》一书创立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规模宏大,思想丰富,体现出“大”的特点。当然,两人“全”、“大”特点也有不同之处。如果说,司马相如的“全”、“大”主要包揽了“空间”的话,那么,司马迁的“全”、“大”则主要包揽了“时间”;如果说司马相如的“全”、“大”主要局限在皇家的林苑范围之内的话,那么,司马迁的“全”、“大”则已超越了小小的林苑,驰骋在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勾画出一幅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如果说司马相如的“全”、“大”主要着眼于世界中的“物”的话,那么,司马迁的“全”、“大”则着眼于创造世界的“人”;如果说,司马相如的“全”、“大”着意于“静态”的话,那么司马迁的“全”、“大”主要意于“动态”(指古今之变及人的活动),同时兼有“静态”(指“八书”的内容)。
第三,现实与浪漫的结合。司马相如的赋,如《子虚》、《上林》,虽说是描绘客观事物,写齐、楚、天子苑囿的广大,游猎阵容的壮观,宫殿楼阁的雄伟,但也极尽夸张之能事:“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俱获。”如: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这样的夸张是极有声势的。但古来的赋论家往往以“虚辞滥说”予以斥责,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相如赋中的夸张,是一种艺术手段,是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表现。再以他的《大人赋》为例,它描写了“大人”(喻天子)嫌“中州”太狭窄、局促,就驾着应龙,乘虚无,漫游天外,他能驱使五帝、含雷、陆离、征伯侨、羡门、岐伯、祝融等神仙为自己效劳,还能“召屏翳,诛风伯,刑雨师”。这篇作品与屈原的《离骚》、《远游》一样,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对此,我们只能用文学的浪漫主义手法予以解释,而不能以“虚辞滥说”来否定。赋的创作有它自己的规律。据《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这说明,司马相如创作赋时,不再是纯粹的“实录”,而是“已有意识地运用形象思维进行艺术创作”,“已大胆地跳出了写真人真事的圈子,对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世界,有目的的进行筛选,进行分析综合,进行再创作。在这里,浪漫主义手法已被广泛地采用了。”所以司马相如赋中的夸张浪漫色彩,并不是什么消极的手法,而是“文学自觉”的一种标志。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实录”作品,但也有浪漫主义特征,对此,拙著《史记与中国文学》中已有详论,不再赘述。但司马相如赋的夸张、浪漫色彩,是一种艺术的虚构,而《史记》的夸张、浪漫主义手法,则要受到历史真实的限制,不是纯虚构的东西,这是两人的区别所在。另外,司马相如的赋和司马迁的《史记》都有讽刺意味。尽管人们常用“劝百讽一”、“曲终而奏雅”来贬斥司马相如的赋,但相如赋毕竟还有讽刺意味,只不过手法委婉曲折罢了。司马迁的《史记》,讽刺意味极强,在某些方面也受到了司马相如讽谏艺术的影响,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详述了。
总之,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司马相如和司马迁虽然各有千秋,但他们共同昭示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龚克昌先生认为: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魏文帝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先生的根据是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也就是近代所说为艺术而艺术。根据鲁迅先生这个标准,或用我们今天所说的所谓自觉地进行艺术创作的标准,我都认为,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至少可以再提前三百五十年,即提到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身上。这个见解是非常精辟的。笔者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司马迁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他的许多思想影响到了六朝文艺理论,是六朝新文学理论的先声。因此,我们认为,“文章西汉两司马”,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并称问题,而是他们二人为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