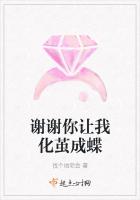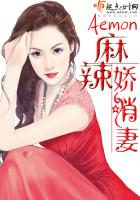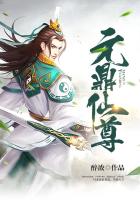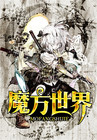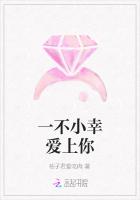陈衍的宋诗观是在宋代以来诗论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唐宋诗之争的背景下形成的。他能接受前人合理的论见,克服种种偏颇,宗宋而不弃唐,推尊苏、黄兼及杜、韩,同时重视宋以来强调的诗歌之法式、声调,对宋诗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陈衍的宋诗观主要体现在他的诗话《石遗室诗话》、宋诗选本《宋诗精华录》以及论诗诗、探讨诗文的序言题跋等,他的诗论涉及先秦至近代诗歌的源流升降、功能作用、内容形式、创作技法等多方面的内容。
陈衍的宋诗观具有较宏大的视野,他不是简单地站在诗学的立场来认识宋诗,而是从文化史的角度俯视历史上的各种诗学,在“诗亡雅废之时”,通过比对分析,对宋诗进行综合的定位和评价。因此他的宋诗学实质上已经成为特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对宋诗进行的文化审美观照。胡晓明先生指出,陈衍诗论的文化意义在于:“唐宋一并泯除,上达风雅,即由学古转向开新,由诗艺取法转向人文工夫。这使其超越了传统唐宋诗之争,不期然而然地关涉到诗学及其相关联的文化存亡问题。应该说是比唐宋诗之争更为富于忧患意味的文化诗学问题”。的确是这样,尽管陈衍于宋诗有个人的偏好,但在个人倾向与述评之间,他基本上能够不以个人好恶来论宋诗及宋诗人。钱仲联先生赞陈衍《石遗室诗话》的诗学之功说:“衡量古今,不失锱铢,风行海内,后生奉为圭臬,自有诗话以来所未有也。”
一、“三元说”的言外之意
陈衍论诗号称“诗不分唐宋”,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三元说”:
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放翁、诚斋,岑、高、李、杜、韩、孟、刘、白之变化也。简斋、止斋、沧浪、四灵,王、孟、韦、柳、贾岛、姚合之变化也。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枢斡也。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书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
仅就这段话来说,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三元”并立,是历史上诗歌达到的三个高峰,各有所长,不应厚此薄彼;第二,宋人乃继承唐人而来,在唐人基础上变化生新。所谓“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即宋人本之于唐人所立之法而推演,在其未尽之处下工夫,也就是“开天启疆域,元和判州部”之意;第三,宋调非宋人所创,实唐人开启此风,“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枢干也。”前人有“诗到元和体变新”之说,而陈衍却将开元一并纳入了这个分唐别宋的枢干,将宋诗与中国诗歌的典范——盛唐诗歌放在了同一条生态链上。
陈衍提出“三元说”之时,正是近代诗坛流派众多,异彩纷呈之际。各家宗奉不一,有“远规两汉,旁绍六朝,振采蜚英,骚心选理”的湖湘诗派,有“无分唐宋,并咀英华,要以敷鬯为宗,不以苦僻为尚”的河朔派,有“驱役新意,供我篇章,越世高谈,自开户牗”的诗界革命派等,其时唐宋诗之争已经不是核心的诗学问题,已经很少有诗家画地为牢,自囿于一朝之诗学。他们往往会“时出入于他派”。不同派别之诗人亦能酬唱往来,很少因诗学宗旨不同而攻讦不休。但是,在一片诗学复古的上溯途径中,同光体派如果仅上溯到宋,与其他派别比较起来显然不够“古”,而且唐音的正声地位使宋诗成为别调已有悠久的历史。因此,宗宋必然要在理论上有突破之处。“三元说”则赋予了宋诗以丰富、深厚的文化背景,为宋诗“根正苗红”寻找了一个不可撼动的源头——盛唐诗歌。
陈衍论诗极讲策略,“三元说”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显然在宗唐宗宋的问题上,他不想陷入无谓的诗学纷争。《瓶粟斋诗话》中记有陈衍的一段话:“审言言鄙人专主唐音,殊不然。或以为专主宋诗,更误”,“不但不专主宋主唐,凡汉魏六朝皆不可主矣”。陈衍始终认为“论诗固不必别白黑而定一尊”。
“三元”上奉开元,中奉元和,下举元祐,使宋诗与盛唐、中唐诗成为其诗学体系的组成部分,构成一个诗歌发展演变的链节。唐玄宗开元时期的二十九年间,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诗人活跃于诗坛,创造了具有典范意义的盛唐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同时,从文学发展史来看,儒学思想在这三段诗歌高峰形成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促进了诗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意识,重视诗歌的社会政治作用,并使诗歌在语言上去浮靡绮丽,变为或清新自然,或生峭雄奇;在思想上脱淫靡浮艳的情思,转向昂扬向上的情感,以风雅精神相号召,并使诗歌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诗坛。
同光体派诗学宗宋及陈衍论诗都没有脱离这个宗旨,折中的论诗方式下面是其真正推尊宋诗的意图。盛唐的典范意义是万流所宗,而承上启下的“元和”突出了新变的意义,成为“元祐”合理化的前提。而陈衍正是在赞同“变”的逻辑下,得出了“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的结论。
陈衍提出“三元说”后,不断地为这个理论进行补充,以泯除唐宋诗界限,他引袁枚的话说明不当以时代作为划分诗歌的界限:
清袁简斋,文人之善谑而甚辩者也。有数人论诗,分茅设蕝,争唐宋之正闺,质于简斋。简斋笑曰:吾惜李唐之功德,不逮姬周,国祚仅三百年耳。不然,赵宋时代,犹是唐也。
陈衍在认同袁枚所论的同时肯定了唐宋诗并不是朝代差别,同一朝中允许存在唐宋诗,那只能是风格的不同了,而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但陈衍还是努力突出了宋诗“后出转精”的高明,力图出宋诗于唐诗之上,虽然他反复多次地表示过“诗不分唐宋”,以避免露出过分扬宋的意图:
唐宋诗佳者,无大分别,真能诗者,使人不能分其为唐为宋。使人能分出者,非诗之至者也;自家之诗而已,其次,乃似某大家。
自咸同以来,言诗者喜分唐宋,每谓某也学唐诗,某也学宋诗,余谓唐诗至杜韩而下,现诸变相,苏、王、黄、陈、杨、陆诸家,……然诗之于唐、宋,果异与否,殆未易以断言也。
同光体派论诗主张“复古以求新”,从根本上说陈衍也不是一个守古不化之人。正相反,他于诗学更看重在前人成就上推陈出新的变化之功。所以,古与新之间的创变在他心目中有更高的价值。另外,陈衍引入“至”作为评判诗歌的标准,将诗歌放在同一标准下进行对比,不再以时代和作者来区别划分,他认为:
夫学问之事,惟在至与不至耳,至则有变化之能事焉,不至则声音笑貌之为尔耳。……子孙虽肖祖父,未尝骨肉间一一相匹敌似。壹壹化生,人类之进退由之。况非子孙,奚能刻意蕲肖之耶?
余于诗文,无所偏好,以为惟其能与称耳,浅尝薄植,勉为清隽一二语,自附于宋人之为江湖末派之诗耳。
在这样的诗学语境下,学唐诗仅惟妙惟肖在他看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像他批判明七子一样“专事摹拟,诗无真性情,不能变化。读唐诗不必再读明矣”。所以,每当论及唐宋诗时,他都会强调宋诗对唐诗的变化:
诗极盛于唐,而力破余地于两宋。眉山、剑南之诗,皆开天、元和之诗之变化也。
诗人之盛,唐代后以宋代为观止。盖宋人诗学,各本唐法,而扩充变化之。卓然成大家者,不甚亚于唐也。
所谓“物极必反”,盛极难再,愈强调唐诗之强,也就愈显出宋诗变唐的艰难和意义的重大。“不亚于唐”当然是含蓄的讲法,但后来陈衍还是将宋诗推到了唐诗之上:
故诗至唐而后极盛,至宋而益盛。
由此可见,“三元说”是陈衍推重宋诗的一种方法。由云龙就认为陈衍“虽不自承为江西派,顾提倡宋诗甚力”,并指出:“盖欲避俗、避熟、避肤浅,而力求沉厚清新,固非倡导宋诗不可。”而陈衍的“三元说”事实上也起到了推动宋诗的作用。
陈衍对宋诗的推尊是强调其变唐,他对宋诗的接受也是立足于宋诗的这种“变”。王安石变法取消了宋代科举中的诗赋,诗歌没有了唐诗的功利性。
经世思想下形成的诗歌观念,并不代表诗歌本身具有经世致用的效果。陈三立、陈宝琛都具强烈政治愿望,但在为政期间几乎都很少作诗,而在退居林下对政治失意之际才借诗以遣愤。陈衍显然是看到了这一点,他说:
诗至唐而极盛。盖以诗取士,如汉代以经学为利禄之途。
余以为诗者荒寒之路,羌无当乎利禄,仁先精进之猛,乃不在彼而在此,可不谓嗜好之异于众与?……然之数人者,诗与其人各不同,而负异于众,不屑流俗之嗜好则同也。
在《何心与诗序》中他更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寂者之事,一人而可为,为之而可常,喧者反是。故吾尝谓:诗者,荒寒之路,无当乎利禄,肯与周旋,必其人之贤者也。既而知其不尽然。犹是诗也,一人而不为,虽为而不常,其为之也惟恐不悦于人,其悦之也惟恐不竟于人,其需人也众矣;内摇心气,外集诟病,此何为者。一景一情也,人不及觉者,己独觉之;人如是观,彼不如是观也;人犹是言,彼不犹是言也;则喧寂之故也。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己所自得,求助于人者得之乎?柳州、东野、长江、武功、宛陵以至于四灵,其诗世所谓寂,其境世所谓困也。然吾以为,有诗焉,固已不寂,有为诗之我焉,固已不困。
清代以来的宋诗运动与经世致用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陈衍本身并不否认经世致用的思想,但是他却并不提倡诗歌的社会政治功能,甚至多次对文人的大言欺世表示不满。他说:“书生好作大言,自以为器识远大,此结习牢不可破”。梁节庵在给王可庄的诗中有“丈夫会须饱天下,岂以琐屑矜其私。江南百姓待泽久,请从隗始铺仁慈”,表达了个人济世扶危的远大志向,而陈衍对此的评价却是“书生喜作大言,亦作诗成例应而也”。钟嵘《诗品》评曹植曰:“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陈衍不赞同诗文有如此之功效,他认为:“譬以周孔、龙凤,未免太过。”对钟嵘的反驳表现了陈衍对诗歌功能的一贯态度。
同时陈衍也对那些热衷于在诗歌中表现政治热情的诗歌表示不赞成。例如文天祥的作品,他就不是很喜欢,不仅挑出其中不合逻辑的典故“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还含沙射影地指责说:“论诗文者每有大家名家之分,此文人结习也。或以位尊徒众而觊为大家,或以寿长诗多而觊为大家,或以能为大言托于忠君爱国、稷契许身而亦觊为大家,其实传不传不关于此。”表现了陈衍强调诗人的孤寒气骨,不浸凡俗的精神和追求。
汪辟疆论陈衍的诗歌道:“石遗初则服膺宛陵、山谷,戛戛独造,迥不犹人。晚年返闽,乃亟推香山、诚斋,渐趋平淡。”似乎陈衍从一开始学诗即从宋人入手,晚年才趋向唐宋融合,将白居易与杨万里奉为圭臬。其实未必如此。陈衍尽管承认以黄庭坚和陈师道为首的江西诗派有可取之处,但他还是坚决否认自己喜爱二者,有人赞他师法黄陈,他说:“余不甚喜山谷、后山,而其工处不可没,实获我心。而篇中又言造江西堂奥,未免信日本博士铃木虎雄之说,余于他处曾辩之。”他又说:“余于诗不主张专学某家,于宋人,固绝爱坡公七言各体,兴趣音节,无首不佳。五言则具体而已,向所不喜。双井、后山,尤所不喜。日本博士铃木虎雄,特撰《诗说》一卷专论余诗,以为主张江西派。实大不然。余七古向鲜转韵,七律向不作拗体,皆大异山谷者。故时论不尽可凭,若自己则如鱼饮水,较知冷暖矣”。
显见陈衍对宋诗的代表诗人黄庭坚和陈师道并非完全赞同,甚至在倡宋诗的同时,明确表明自己尤其不喜欢黄庭坚和陈师道的五言诗,在这一点上他与郑孝胥的观点是一致的,对典型风格的宋诗并非完全接受,而是对带有浓厚唐诗色彩的宋诗更感兴趣。
二、宋诗特征的认同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称:“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对严羽的此论,清代以来宗宋诗者显然不赞同,且多有驳斥之言。陈衍论诗往往有与之对应之处,并且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渗透到自己诗论的不同方面。
(一)“以文为诗”的延展
陈师道最早提出“以文为诗”的概念,他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但陈师道并没有对“以文为诗”给出明确的定义,后来论者遂以严羽所说“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综合起来作为“以文为诗”的表现。
陈衍对以文为诗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桐城派,即用文章的方式、方法、技巧来作诗。方东树称:“汉、魏、曹、阮、杜、韩,非但陈义高深,意脉明白,而又无不文法高古硬札。”又“观韩、欧、苏三家,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欧公作诗,全在用古文章法”。在方东树看来,诗歌与古文有着内在的相通之理,好诗同样来自于章法剪裁得当,将“陈义高深,意脉明白,文法高古”这些文章做法的术语用在评论诗歌上,反映了其诗文一贯的观念。陈衍尽管没有具体论述“以文为诗”,但他认为作诗与作文一样,都可以用来记事、言情、写景,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所以,文章写得好,诗就能作好;诗写得好,文章也自然会好。
诗者以言情说理写景纪事与文同,而所以言之写之纪之者,与文稍有不同。及其工也,可诵可读又无不同。所以古者均谓之文。……实则工文不工诗,工诗不工文者,非其未为,即其为之未力者也。
昔人谓曾子固不能诗,是一恨事,殊不然……余尝论古人诗文合一,其理相通,断无真能诗而不能文,真能文而不能诗,自周公、孔子以至李、杜、韩、柳、欧、苏,孰是工于此而不工于彼者。其他之偏胜而不能兼工,必其未用力于此者。
陈衍主张“诗文合一,其理相通”,认为诗与文只是稍有不同罢了,但只要达到一定的造诣,“可诵可读又无不同”,所以他以为“断无真能诗而不能文,真能文而不能诗”者。同时他也以文章的做法来探讨诗歌的脉络,进行诗歌的鉴赏批评,如:
杜陵古诗,往往将后面意,撮在前面预说,使人不易看出线索。退之作文之善于蔽掩,即此法也。……《芒砀》十字,似登台语而寓意极微,语切友生……此二句置在未入先帝之前,故无所阂口,而使人不觉,下面即紧顶先帝好武,叙拓境后,便接以存殁,中间全无曲折,盖亦倒找势耳。
由此可见,在陈衍眼中,宋诗的“以文为诗”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文即是诗,诗亦是文,因为“诗文合一,其理相通”。
(二)诗“理”的开拓
宋人文学创作中的理性意识较唐人增强,苏轼等人在诗歌创作中又好追求理趣,寻求一种将自然之理和人生哲理融为一体的理趣。如《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以自然景物寓人生哲理。但是这种倾向发展到后来,就成了“以议论为诗”,并最终产生了钱钟书先生所批评的宋诗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
陈衍对宋诗重“理”的接受可以分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诗要能“发明哲理”。陈衍本身就偏好苏轼诗歌,他说:“余于诗不主张专学某家,于宋人,固绝爱坡公七言各体,兴趣音节,无首不佳。”因而对苏轼这种从自然体悟哲理的方式也能够体会出其中的兴趣。唐文治在《石遗室丛书总序》中评价陈衍诗歌道:“先生名满天下,艺林中莫不称其诗,已刻《石遗室诗集》十卷,《补遗》一卷,《朱丝词》二卷,《续集》二卷。撷其菁华,大抵清劲真适,风骨高骞,且时时发明哲理。”而陈衍评论诗友之作也常从“理”的角度予以褒赞。如“见子培数诗,雅健有意理”;沈曾植看了陈衍的诗后也极口称赞:“事理相扶,昭彰朗彻,讽咏再三,不能去手”;陈衍与陈仁先论诗时说:“余谓吾辈生古人后,好诗已被古人说尽,尚有着笔处者,有无穷新哲理出,可以边际之语写之也。”在陈衍看来,哲理已经成为了从古人诗歌中发掘出新意的前提,诗歌的题材有限,只有从不同的角度发现不同的哲理,然后用“边际之语写之”,才能有新意,否则就会在古人将好诗说尽的情况下无法下笔。这种观点与叶燮有些类似,叶燮指出:
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递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其理日出。
另一方面,诗作要合乎“情理”。这里的情理指日常生活的人情世故以及事物的原理、道理。
杜牧之叙李长吉诗云:“少加以理,则可以奴仆命骚。”言昌谷俶诡之词,容有未足于理处也。理之不足,名大家常有之。
李贺诗歌以想象奇特、用语夸张而著称。陈衍认为,杜牧所谓“稍加以理”,就是针对这些想象和夸张而言,因为它们超出了人们正常认识,显得不合情理。以陈衍、黄庭坚的诗为例,说明名家、大家也常会有不合理之处。
山谷题画诗云:“石吾甚爱之,勿使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伤我竹。”此用太白“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调也。然不见月虽以譬在上者被人蒙蔽,而就字面说,月之不见,于事固无大碍,以较行人之没于水,自觉其尚可。若其石既为吾所甚爱,惟恐牛之砺角损坏吾石矣。乃以较牛斗之伤竹,而曰砺角尚可,何其厚于竹而薄于石耶。于理似说不去。
黄庭坚诗首先称自己甚爱石,因为爱石怕其有损,故不让牛在石上磨角。然而,随后笔锋一转,说到牛在石上磨角也没什么关系,更担心的是,要是牛打斗起来伤了自己的竹子可不好。如果将诗中对石与竹的感情看做递进关系,也讲得通。但陈衍指出此诗源于李白,所以其结构也应与之相同,则爱石而担心竹就不合道理了。此类关于诗歌不合“理”的解释在《石遗室诗话》中并不少见,这应当是从宋诗的“理趣”衍生出来的东西了。至于陈衍所体认的“理趣”,钱钟书先生的解释可谓搔着陈衍的痒处:“‘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乃理趣好注脚。有形之外……不落迹象,难著文字,必须冥漠冲虚者结为风云变态,缩虚入实,即小见大。”陈衍现存诗作山水诗占据绝大部分比例,从外物特别是自然山水中体悟哲理是陈衍发明“哲理”的“趣味”所在。
(三)诗与学问的关系
宋人在创造宋型文化的同时,也感受到自身对于文化传承的责任,因而诗歌中出入经史,贯穿百家,集文、史、哲于一体,这种表达方式可以说是宋型文化意识的集中体现。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均以知识丰富、学问渊博著称。对于宋诗的学问化倾向从清初以来的宗宋诗派几乎都持赞成态度,并往往以之与明人的空疏不学或者空谈性理、束书不观对立起来。
同光体派承近代宋诗派理论,继承了宋人的这种文化精神,主张合学人与诗人一体。陈衍是同光体派诗学主张的总结者,他对于宋诗重学问的接受方式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学问与诗有别,但学问有助于诗。陈衍对于宋诗学问化的倾向并不反对,诗中可以有学问,但学问本身并不是诗。诗归根结底是性情的表现。在陈衍看来,学问主要来自于读书,所以他对钟嵘反对以诗表现学问、强调“直寻”表示不满:
余所以雅不喜《诗品》者,以其不学无识,所知者批风抹月,与夫秋士能悲,春女能怨之作耳。力诋博物,导人以束书不观,不免贻误后生。……夫作诗固不贵掉书袋,而博物则恶可已。
诗不一定要富于学问,但是博学多识、知广闻多却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强调了就诗而学诗是最下的方法,而这些基本上是对黄庭坚“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的解说,并无多少新发现。
盖作诗不徒于诗上讨生活,学问足,虽求工亦不至于苦也。
求诗文于诗文中,末矣。必当深于经史百家以厚其基,然尤必其人高妙,而后其诗能高妙。
其二,学问表现为用字有来历,用事典切。用典到了宋代的苏、黄手中,在用典范围和技巧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用典一是讲求“博”,经史子集、稗官野史、道藏释典、医学农书无不可以入之于诗,强调诗中“无一字无来历”,也就是苏轼所言的“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和黄庭坚所讲之“夺胎换骨”之法。陈衍对用典的态度较宽容,不认为诗歌必须用典:“大概作诗不用典其上也,用典而变化用之次也。明用一典,以求切题,风斯下矣。”他肯定了巧妙用典的好处,认为“诗有用事甚切,不能以白描见工者”。并引沈瑜庆诗“肠断父兄携我处,白头来此听溪声”说明“‘肠断’句用荆公诗,甚切”。但是他坚决反对有意堆砌典故,特别是满眼故实而无真意的:“读大复《明月篇》,反复再四,不知其命意所在,但觉满纸填明月故实耳。”
至于“无一字无来历”则是陈衍所说学人诗的标准之一。他说张亨嘉的诗乃“惨淡经营,一丝不苟,所谓学人之诗也”,并举《苇湾泛舟》和《游积水潭》道:“二诗不过数百字,凡用经史十许处,几于字字皆有来历。”所以他提出要“诗人与学人合”,要求有学术根底,而学术根底则包括朴学、小学、史学等诸多学问。只有这样,才能“具学人之根底,诗人之性情”,“诗人学人二者,非肆力兼致不足以薄风骚、副雅材”,要求将诗人与学者合为一体,兼于一身,方能有所成就。在陈衍看来学人与文人有别,文人的见识不能与学人相比:
文人有文人见解,以之论史,要不足以服古人者。《读吴志》句云:“青盖早知归晋室,白衣应悔取荆州。”支对非不工,然英雄攻取,岂能以后来之归晋室而当时遂不取荆州哉。又《吊张世杰》云:“歌声已唱青山转,天意难回白雁谣。遗恨厓山山下水,不能化作浙江潮。”南宋亡时,浙江潮固三日不至,然江潮即至,蒙古兵遂不渡哉。
因此,陈衍大力提倡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强调诗人要“学有根底”,而不屑于以文人自居:
文端学有根底,与程春海侍郎为杜为韩为苏、黄,辅以曾文正、何子贞、郑子尹、莫子偲之伦,而后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
总之,对学问的认同反映了陈衍对于高度发达的宋型文化的认同,他自觉地用诗歌作为承担文化的载体,肯定了学问的意义和价值,是宋代以来“以学问为诗”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