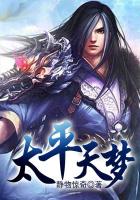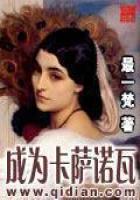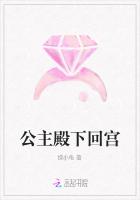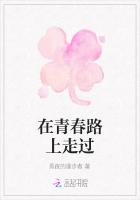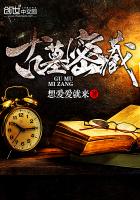元修还盯上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人选——高乾。可高乾明明是高欢的铁杆支持者,当初是他将冀州拱手相让,才让高欢有了容身之所,是他兄弟高昂的临阵一击,才让高欢转危为安,而高欢也尊称高乾为族叔,关系非同寻常。元修此举近似火中取栗。
可元修虽年轻,在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上是绝对地老辣。他敢冒险,是他一眼看出了高乾和高欢之间的貌合神离,看出了河北大族和六镇鲜卑之间的天然隔阂。且高乾一旦入伙,他的能量非同一般,只要他振臂一呼,整个河北豪族定会应者云集。
而此时,高乾刚好处于仕途的低谷期,的确需要人来拉他一把,而元修找准这个机会开始雪中送炭。
那时高乾刚遭受了父丧,他很自觉地请朝廷解除他的侍中一职——乱世中,守孝的礼法虽不像以前严苛,但丁忧的原则还得遵守。可高乾这一客气就麻烦了,军国大事都听闻不到,被直接踢出了北魏的权力核心层,只剩下司空这空头衔。
元修在华林园宴请诸官,宴后便单独留下高乾。高乾还没回过神,元修一下子非常殷勤地拉着他说:“司空世代忠良,今日复建奇功。你我虽是君臣,可义同兄弟,宜共立盟约,以敦情契。”
高乾一下子懵了,皇帝放下至尊之位与自己共立盟誓,岂能拂其好意,只得假意应承:“臣以身许国,何敢有贰!”
这种香火盟誓都是逢场作戏的,倒不会惹出什么大祸,可错在高乾没有把这事立刻禀告自己的领导——高欢,而正是这疏漏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盟誓之后,元修发现自己找错了人。因为高乾虽明白高欢与自己若即若离,但元修和高欢孰强孰弱一目了然:选择元修只能速死,而跟随高欢起码还有活路!高乾不为盟誓所动,铁了心跟着高欢,元修便也不再拉拢。高乾看到元修与斛斯等人日日操练军队,知道他们与高欢之间的火并在所难免。他便将洛阳的一举一动告知高欢。高欢立传他赴晋阳商议。
高乾为讨高欢欢心,竟劝高欢逼魏主退位,自己接受禅让。高欢是何等狡猾之人,怎会为其所动,成为众矢之的,便忙用袖子掩住高乾之口:“不许胡说!你官复原职的事包在我身上了。”
高欢立即向元修屡请让高乾官复侍中一职,元修当然屡屡驳回。
见皇帝不许,高乾知道大难即将到来,洛阳已不可久留,便通过高欢所请,转为徐州刺史,逃离这是非之地。这回,召命倒是批下来了,可紧随召命而来的还有死神。
高乾刚要出发赴任,大祸便来临了。因为元修知道高乾泄密了,这让他恼火万丈——好心拉你入伙,你不来就算了,还当小人去告密,太不像话了。他便修书一封给高欢,很直接,概括为一句话:“高乾与朕私有盟约,今乃反复两端。”这皇帝倒也不害臊,作为君主,与臣子私底下眉来眼去的事都还要说给第三人听。
高欢一听高乾竟怀有异志,顿时杀心四起,便做了一件极不厚道的事——将高乾那些高谈阔论、劝他篡位的文字一块打包送给了元修。元修忙召来高乾责问。高乾无以为对,明白是高欢出卖了自己。他倒没有破口大骂,只淡淡地说:“陛下自立异图,却说为臣反复。人主加罪,其可辞乎!”从容就死。
高乾家族势力庞大,元修立马要斩草除根,密令除掉高敖曹和光州刺史高仲密这两兄弟。高敖曹一闻兄长死讯,便埋伏路旁,绑架了朝廷派来的官员,从他身上搜到了杀自己的诏书,率十余骑投奔高欢。虽然高乾分明为自己所害,而高欢依然作秀,竟然抱住高昂之首,大声痛哭:“天子枉害司空(高乾)!”将自己的罪状推得一干二净。而高仲密也间行逃至晋阳。
高乾之死,北魏皇室和河北大族两败俱伤。高乾死后,河北大族再无一呼百应的领袖,封隆之怯懦,高昂粗猛,皆不是领袖之才,以后便完全受控于高欢。而北魏皇室此举也得罪了河北大族,多了一个势不两立的敌人。高昂对元修更是恨之入骨,急欲复仇。
唯独高欢渔翁得利,这招借刀杀人绝对高明——借元修之手,轻松除掉高乾这个未来劲敌,又使河北大族与元修势不两立,果然一箭双雕!
可高欢为何一定要除掉高乾,此正是用人之际,他不怕人心离散吗?因为高欢和河北大族需要的不仅是合作,还要绝对的忠诚,而高乾这种三心二意的举动在他眼里是容不下的。由于关中劲敌尚在,高欢不愿立即与河北大族分道扬镳,所以又收留了高昂兄弟。此次借刀杀人,算他对河北大族的一次惩戒。而以后,这种惩戒还会接二连三地到来。
不是自己的终究不是自己的——高欢明白自己力量的根源来自六镇,虽然他流着的是汉人的血,可六镇鲜卑才是他的根脉,才真正让他安心。
高乾明明是一心一意侍奉高欢的,在危难之际,也早就未雨绸缪,却最终被高欢无情抛弃,难逃一死,这又为何?乱世之中,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落幕的基本都是悲剧。岂独高乾如此?此鲜卑族人争权夺利之时,整个华族的命运莫不如此——浮若飘萍,随波逐流而已。
而更为惨痛的莫过于高昂,他虽有霸王扛鼎之力,明知其兄之死是拜高欢所赐,却只得死心塌地为高氏卖命,而把满腔仇恨转到元修身上。何也?天地虽大,却是元修和高欢之天下,无其容身之所!不归元修,便归高欢,但元修已挥起屠刀,高欢尚能假意收留,只得对高欢俯首帖耳!
高欢的劲敌——贺拔兄弟
虽然元修一直在洛阳蠢蠢欲动,可高欢还不想撕破脸皮:这天下本就是元家的,作为元氏子孙为自己的江山奔走,也算理所应当;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高欢认为元修掀不起什么大浪来,任由他折腾去吧。可关中的贺拔岳也在一旁敲锣打鼓,势力越来越大,这是高欢所绝对不能忍受的,而他跟贺拔岳之间的恩怨情仇也到了该了结的地步。
高欢和贺拔岳以前都是尔朱荣的得力干将,可他们在投奔尔朱荣后却一直都在明争暗斗,他们结下梁子的事还要追溯到“河阴之难”时。当年的高欢政治上还极不成熟,为取得尔朱荣欢心,一时冲动,竟竭力劝他称帝。结果弄巧成拙,野心勃勃的尔朱荣中途突然改弦易辙,称帝之事不了了之。贺拔岳当时竟然怂恿尔朱荣杀掉高欢,幸亏高欢人缘好,众人帮他请求,才免于一死。那一回合,贺拔岳占了先机,而高欢彻底地败了。
此后,贺拔岳率领六镇中的武川人马西征关中,立下功勋无数,名扬四海。而高欢虽无贺拔岳风光,默默无闻地窝在晋州之地,但也在积蓄力量,以待一飞冲天。那段时光,两人都是蓄势待发的状态,算是并辔而行。
转而高欢诱骗到了尔朱兆的六镇之民,取得韩陵之胜后,其势便如日中天,天下无人可及。论兵力,高欢拥有六镇大部,而贺拔岳仅有武川一支,兵力悬殊自不可相比;论地盘,高欢占据河南、河北、山西等广袤之地,可贺拔岳窝于关中一隅,也相距甚远;论官职,高欢已位极人臣,贵为丞相,一人之下,而贺拔岳仅为关西大行台,一方诸侯而已。这回,高欢完全是一骑绝尘,将贺拔岳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此时的高欢便以丞相之尊,居高临下地召唤他的对手——任命贺拔岳为冀州刺史,让其赶往洛阳。
贺拔岳接到任命后,一时惧于高欢之威,为求自保,竟然欲单马入朝。幸被手下薛孝通劝阻:“高王方内抚群雄,外抗劲敌,安能去其巢穴,与公争关中之地乎!今关中豪俊皆归心于公,愿效其智力。公以华山为城,黄河为堑,进可以兼山东,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于人乎!”
此言如醍醐灌顶,使贺拔岳如梦初醒:高欢现在内外未安,征讨尔朱兆才是其首要之务,且他还需安抚洛阳城中勋贵,何来精力顾及关中?自己一旦单马入朝,便是将关中拱手相让,到时一夫可斩!趁高欢外征内讨之机,先固守关中,到时争雄天下,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这一回合,贺拔岳虽在关键时刻翻然醒悟,但在气势上已经完全输了。
贺拔岳并不放弃,他要观察这位老对手的一举一动。当高欢抵达晋阳的时候,贺拔岳便派了手下冯景前去打探。高欢又故技重演,装作大喜过望的模样迎接来使,还郑重其事地与来使歃血为盟,与贺拔岳遥结为兄弟。
可这种香火之誓只对尔朱兆这样的粗人有效。冯景一回关中,便禀报:“高欢奸诈有余,不可信也!”这时贺拔岳手下又有人主动请缨,要求再前去打探虚实。这人一回来便禀报“高欢未篡,正惮公兄弟耳”,并建议贺拔岳趁高欢大军未至之时,先打扫自家院落——引军征讨陇西一带,以取得敲山震虎之效。陇西一带,各股势力盘根错节,并不归属贺拔岳,此举意在安定关中后方,为关中崛起打好基础。
贺拔岳闻之大喜,又派这位年轻人前往洛阳通禀元修。元修正愁着该如何笼络贺拔兄弟,如今贺拔岳主动派人献策讨官,便大喜过望,以贺拔岳为都督雍、华等二十州军事,雍州刺史,使其成为关陇一带的最高长官。他唯恐诚意不够,又割心前血,以作信物,派专人送与贺拔岳。
得到皇帝授权,贺拔岳立马引兵向西,屯于平凉。果然如那位年轻人所料,附近各州刺史咸来拜会,各族豪强也纷纷示好,唯剩下灵州刺史曹泥依然我行我素,遥与高欢呼应。贺拔岳此敲山震虎之举,收拢了后方那些摇摆不定的各族势力,实力大增。
而贺拔岳的哥哥贺拔胜抵达荆州后,便是大肆骚扰梁境,攻克多城,梁军竟无力抵抗,节节败退。
高欢对此难以忍受,再任由贺拔兄弟迅猛发展,这天下以后还能姓高吗?坐卧不安之际,他底下的翟嵩献策:“嵩能间之,使贺拔岳和侯莫陈悦自相屠灭。”这种离间之计,高欢在尔朱家族倒是屡试不爽,在贺拔岳这里又故技重演了。
暗中一刀
贺拔岳准备再度出兵,征讨未归附的灵州刺史曹泥。此举意在报复高欢,因为不久前,高欢刚刚擒拿了依附贺拔岳的河西流民帅伊利。但曹泥只是高欢埋在贺拔岳身边的一颗钉子而已,最多让他走路磕磕绊绊,并无大碍,可他却急于拔除,而对于高欢高悬他颈上的那把利刃,他却没有丝毫察觉。
那把利刃便是侯莫陈悦。侯莫陈悦和贺拔岳一起入关,官职也大致相当,并不接受贺拔岳调遣,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而现在贺拔岳一跃成为关陇一带的最高长官,侯莫陈悦已是贺拔岳名副其实的部下了。侯莫陈悦的野心不大,只求有块地盘,自己能当家作主就行。而贺拔岳这势头发展得咄咄逼人,对他吆来喝去的,让他很不舒服。而这回贺拔岳名义上是在收拾曹泥,可侯莫陈悦明白,下一个兼并的就是他的地盘了。
正当侯莫陈悦惶恐不安时,翟嵩的游说更是加大了他的疑惧。这地盘可是自己拼死拼活挣来的,这转眼间就没了,侯莫陈悦怎能甘心?他得誓死捍卫。这就是侯莫陈悦简单的想法,为捍卫自己的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