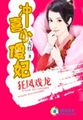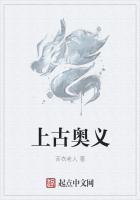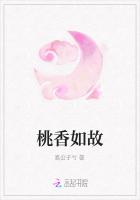安置好这一切后,宇文泰便要大刀阔斧地收拾侯莫陈悦了。他指责侯莫陈悦言而无信,与贺拔岳多次结盟,但结果却是“口血未干,匕首已发”。他又上表元修讨伐侯莫陈悦,表明决心:“宇文泰自视贺拔岳与其情同父子,今仇恨未报,亦何面目以处世间?若得一雪冤酷,万死无恨!”
待各路人马毕集后,宇文泰便从原州进军,路上军令肃然,秋毫无犯,深得百姓之心。四月,陇右一带却是雨雪交加,路上雪深二尺。宇文泰选择了逆水行舟,趁此恶劣天气日夜行军,要杀侯莫陈悦个措手不及。
侯莫陈悦听闻,吓得率军退回秦州老巢(今甘肃天水),只留万人防守水洛城。此城防守形同虚设,宇文泰军至后,随即降附。侯莫陈悦更加焦急,召来南秦州刺史李弼一起拒守。侯莫陈悦把秦州让自己的这位连襟李弼(他们娶了同一家的姑娘)防守,自己跑到山中去了,以险固守。
宇文泰又率军赶至,准备与侯莫陈悦明日决战。李弼对侯莫陈悦无端杀害贺拔岳一事早已不满,认定侯莫陈悦败亡是迟早之事,夜里便与宇文泰通款,请为内应。李弼还派人到侯莫陈悦营中宣扬:“侯莫陈公欲还秦州,汝等何不装办?”众人都以为实,皆有离散之心,至此人情惶惑,不可复止。机灵点的,便见风使舵,主动投奔到宇文泰营中去了;糊涂点的,相信了李弼的鬼话,也争相跑回秦州城去了;留下的那些人也是首鼠两端,不再卖命。而李弼早已在秦州严阵以待,收拢了这些游兵散勇。
侯莫陈悦一看部队人心离散,更加紧张,想趁夜与宇文泰决战。不料双方还未交战,他的部队全无斗志,自行溃乱。宇文泰纵兵奋击,大破敌军,俘虏兵士万余,战马八千。
遭此大败,本来疑忌之心就重的侯莫陈悦更是雪上加霜,连亲兵都不要了。最后他只带了弟、子及随从等十余人弃军逃跑。可这可怜的十几人转来转去,就是找不着北。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法:翻山越岭去投奔灵州的曹泥。可要爬山的话,马就不能骑了。侯莫陈悦自己找了头驴子骑着,左右步行跟随,开始了长征之旅。可宇文泰对他的一举一动早已了如指掌,派人追赶。侯莫陈悦倒是个明白人,一看逃生无望,便非常爽快地自行了断,自缢死于野。
李弼把秦州之地拱手让给宇文泰。宇文泰进城后,见府库堆积如山,他却秋毫不取,全以赏赐将士。李弼不是武川人,但后来能贵列为八柱国之位,虽是战功赫赫所至,但与此次投诚关系莫大。李弼有一曾孙,便是那位牛角挂书,雄踞瓦岗寨的李密,他们李家的发迹便是从这次投诚开始。
闹翻了
当宇文泰在关陇一带热火朝天的时候,高欢和元修之间也闹得不可开交,使得高欢无暇西顾。
高欢明白自己和元修之间不过是元子攸和尔朱荣的翻版而已,而他肯定不会再犯尔朱荣那样的低级错误——送上门被皇帝刺死。高欢更清楚自己的实力没有尔朱荣强大,尔朱荣当时是真正的一手遮天,而现在还有宇文泰、贺拔胜和他为敌。万一元修和自己闹得不欢而散,他还能投奔关中、荆州,有个容身之所。正是有他们的依托,元修在行动上越来越有恃无恐,这更使高欢痛下决心要收拾这位不知深浅的年轻人。
高欢留在洛阳的势力被元修彻底驱逐了。侍中封隆之和仆射孙腾这两位都是高欢的心腹之臣,高欢将他们留在洛阳本为监视元修的一举一动。可这两位却辜负了高欢的厚望,竟然为争一个寡妇——元修的妹妹平原公主闹得满城风雨。结果最后两人互相揭短,都狼狈逃回晋阳。高欢的小舅子领军将军娄昭也只得辞疾而归。这次,高欢忍住了,没跟元修翻脸。
此后,元修又得寸进尺,将建州撤了——建州处于太行要道,是晋阳南下洛阳的重要关口,而它的刺史是高欢的亲信韩贤。而元修利用调整政区规划,暗地削夺高欢势力,防备高欢南下。这一次元修已把手伸到自家门口了,可高欢还是忍住了。但元修忍不住了,不想坐以待毙,准备主动出击,北伐晋阳。他这两年靠斛斯苦心经营,也征集了十来万人。不过这些军队都是新征来的,花拳绣腿不会打仗,他决定先搞个军事演习。他以征讨梁朝为由,下令戒严,在洛阳城外点兵阅军,搞得气势宏大。他又怕高欢起疑,便暗中向其表示是要讨伐宇文泰和贺拔胜。
这对高欢而言可是正中下怀,正愁着没有出兵的借口,便上表元修,表示既然皇上要收拾逆臣,自己肯定全力以赴,在表中把自己的兵力炫耀了一番:东西南北各线竟达二十几万人马之多。
元修一见自己的小把戏被高欢揭穿,只得硬着头皮下令高欢罢兵。可为时已晚,局势已呈骑虎难下之态,高欢这堂堂大宰相竟在回表中发了毒誓:“臣若敢负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孙殄绝。”不过,毒誓后又增加了一句更狠的话:“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动,佞臣一二人愿斟量废出。”
威胁,赤裸裸的威胁!这佞臣指谁不言而喻。要皇上自断臂膀,以示诚意,高欢之心已路人皆知。
臣子竟对皇上如此挑衅,元修更加火冒三丈,派人严守北边防线。他又给高欢答复了一封书信,替他捉刀的是北魏第一才子温子。温子是明白人,此次一旦下笔,定会得罪高欢,所以实在不愿接这苦活,迟迟不肯下笔。结果元修不顾帝王之尊,亲自拿刀相逼。
刀刃之下,温子只得下笔,出手依然不凡,开篇先是盛赞高欢:“朕不劳尺刃,坐为天子,所谓生我者父母,贵我者高王。今若无事背王,规相攻讨,则使身及子孙,还如王誓。”
帝王和宰相两人如街头泼妇般发这些断子绝孙的毒誓,古往今来倒是少见。
盛赞之后,笔锋一转,指责高欢多种不臣之举:“谋害高乾,贪立幼君,包庇罪臣,举兵犯上。”
指责过后,最后又作苦语:“王若晏然居北,在此虽有百万之众,终无图彼之心;王若举旗南指,纵无匹马只轮,犹欲奋空拳而争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无知,或谓实可。若为他人所图,则彰朕之恶;假令还为王杀,幽辱齑粉,了无遗恨!本望君臣一体,若合符契,不图今日分疏至此!”
此信虽为千古名篇,可惜只能成为书信的范文,供后人品读,在高欢这样的枭雄面前依然如同石入大海,毫无作用。高欢收信转而上书指责宇文泰、斛斯之恶,并以高敖曹为前锋,向洛阳进军。
元修收拢了十万人马,结阵于黄河一带,与高欢大军对峙。由于高欢之军远道而来,又是日夜行军,早已疲惫不堪。元修却只把希望寄托在了黄河上,不敢主动出击——斛斯要率军偷袭高欢的绝妙建议被他拒绝了,原因竟然是他担心一旦斛斯得胜,便会成为第二个高欢。
黄河虽是天险,但渡口极多,只要有船便可轻易摆渡。而元修手下看出这皇上迟早要败,部分将领暗中早已投降高欢。高欢率军轻松过河,元修的十万大军一朝瓦解。
元修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与众人商议后,他决定西避关中。本来元修手下还有五千骑兵跟随,可到半夜之中,便亡者过半。元修此行极为悲惨,路上既担惊受怕(高昂为报兄长之仇,在后猛追),又饥肠辘辘(跟随他的从官好几日只能喝水充饥)。路上有个村民送了点普通饭菜,这位天子竟然感动得一塌糊涂,免掉了整个村庄的一切赋税,而且大方地给了十年期限。
元修就这样忍饥挨饿到了宇文泰的地盘,宇文泰亲自于长安城外迎接,免冠流涕,殷勤备至。至此,元修这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才算结束,可往后他就能过上童话里那种幸福安定的日子吗?高欢把他从田间找到立为皇帝,如今却凶相毕露,逼他流亡;而现在这位口口声声地宣称效忠于王室的宇文泰,真的是在做慈善事业,会把关中之地拱手相让吗?
早在元修入关前,就有有识之士看出“图欢有立至之忧,西巡有将来之虑”,元修入关不过是“避汤入火也”。
这话很有见地,不过结果倒反了。假如元修落入高欢之手,或许还能多活几年,可在宇文泰手里他却已时日无多了。
元修有个坏毛病——好色。这本来对帝王而言,算是优点,不好色肯定当不好皇帝,不然怎么给帝国生产继承人?可元修却玩过头了,天下美女如此之多,他竟然只喜欢自己家里头的——与自己的从妹多人有染。宇文泰是那种很正统的人,容忍不住这些丑事,便借元氏宗室之手杀了其中的一位——平原公主元明月。心爱的女人无端被杀,元修当然怒不可遏,在宇文泰的地盘上又是弯弓欲射,又是拿刀椎案。
宇文泰是那种快刀斩乱麻之人,一见如此,便立马毒死元修,而这时离元修入关竟不到半年。因为那时洛阳已经有了新的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计策已无效了。而对于宇文泰而言,北魏的公主已经讨到手,丞相的帽子也戴上了,这个天天舞刀弄枪的皇帝留着迟早是个祸害,便痛下杀手。
新立的皇帝是跟元修一起入关的南阳王元宝炬,这位皇帝在洛阳当王爷时脾气可不是一般地大。即便在高欢如日中天时,他也敢痛殴高欢的从弟高隆之,还直接戳人痛处:“镇兵何敢尔也!”而高欢改迁父墓时,百僚尽拜,独他不屈。
不过,在宇文泰手里,这位刺头老实多了,跟宇文泰竟相安无事了十几年。这便是宇文泰的过人之处。
天下三分
回到高欢。他进军时,怕自己今后承担逼走皇帝的恶名,一路上便给元修连上了四十道奏折,以示拥立之心。便是元修已西入长安,他也一直苦请元修回洛,可元修只字不答。
无奈之下,高欢只得立了清河王世子元善见为帝,这回他挑的是个小孩,只有十一岁。高欢以前惧怕世人责其贪立幼君,把持朝政,如今他吃尽苦头,终不再为贪虚名而受实祸。
自此,统治黄河流域接近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北魏王朝终于一分为二,变成了东魏和西魏两国对峙,加上南朝,天下终于三分。
如以战国旧地相论,西魏只占关陇一隅,秦国一地而已;而东魏几乎尽占东边之地,韩、魏、赵、齐、燕几乎尽归其有,两者相差悬殊。可自从东、西两魏对峙的两年间,双方除了试探性地出过兵外,并没有大规模地交战过。宇文泰不出兵,那明显是实力不够,既然有潼关等天险可守,何苦盲目出击,自寻死路?
可高欢为何忍耐得住呢?
因为高欢已看出了宇文泰绝非等闲之辈,自己已经为轻敌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吃了不少苦头。在争夺贺拔岳余部时,他只派侯景孤身入境,结果让宇文泰抢了先机;在宇文泰剿灭侯莫陈悦时,他不以大军压境,只派万人相救,结果坐视侯莫陈悦被灭。如今这位年轻人在关中立足已稳。在元修与自己对峙的情势下,他也只是佯装支援而已,不派一兵一卒交战。这是个可怕的对手!高欢这才明白,当葛荣、元子攸、尔朱荣、贺拔岳这些配角都纷纷退场时,站立在天地间的只剩下宇文泰和自己了。
加上境内新的都城要建,朝中的元勋要加以安抚,南边的萧衍老儿要搞好关系,而北边的柔然大爷也要伺候好,等这些焦头烂额的事尘埃落定后,才是出兵之日。
高欢明白了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他攻克潼关,返回洛阳立完新帝后,便下令迁都邺城。这不是心血来潮之举,早在高欢拥立元修时便以洛阳久经丧乱,欲迁都邺城,但被元修拒绝。如今洛阳不但与梁朝邻近,又凭空多出关中这一个劲敌,处于四战之地,不得不搬了。
搬迁之令下达三日,洛阳城的四十万户便狼狈上路,这一年与孝文帝迁都刚好隔了四十年。而洛阳的永宁寺也在这一年的二月化为灰烬,大火经三月不灭,观者哭声震天。与永宁寺一同化为灰烬的还有洛阳的无尽繁华和孝文帝元宏的良苦用心。
从当时战局和日后战事来看,高欢此举是高瞻远瞩的,洛阳的确不适合当首都了,不然也只有等着战火来焚毁。但断然放弃洛阳,也预示着高欢走上的是一条与孝文帝截然不同的道路。
而贺拔胜这一介武夫在高欢大兵来临时,却坐山观虎斗,错失良机,最后被侯景打得大败,只剩下数百骑投奔梁朝。
牛刀小试
立足已稳
立完新皇帝的这两年,高欢也只在晋阳遥控朝政而已。新的国都邺城在增修之后已初具规模,可在这新国都里发号施令的却是两个小孩,这是很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