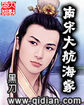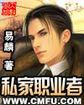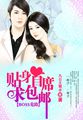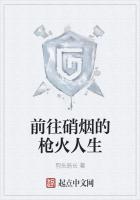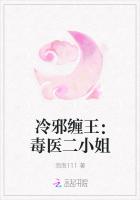然而蔡的怀抱虽然坚强有力,但也只能给宇文泰带来一时的安宁——他的噩梦远没有结束。一听闻宇文泰惨败而归,西魏的反对势力也蠢蠢欲动,趁机开始浑水摸鱼。这次跟随宇文泰参加河桥之战的也有一些东魏的被俘士兵,可他们受宇文泰的感化(或者威逼利诱),倒是与自己的老东家——东魏拼命死战。可是留在关中的那些东魏散卒觉悟要低得多,一听闻西魏兵败,便立即谋乱——想不谋乱都不行,当时西魏驻守首都长安一带的军队只够维持治安的。
这糟糕的局面当然跟宇文泰有关。与高欢一样,宇文泰也不愿跟皇帝朝夕相处,这种主弱臣强的关系总让人极其别扭——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皇帝再怎么无能总还是皇帝,虽然三拜九叩可以免除,但其他的君臣礼仪依然繁琐得要命。待在一块大家都心知肚明,总会束手束脚,索性跑远一点遥控指挥更加舒服。高欢把自己的霸府建在晋阳,而派自己的长子高澄看守邺城,这是上乘之计;而宇文泰也效仿在华州(就是王罴吓走高欢的那地方)建立府邸,在此处发号施令。之所以选择华州,主要是此处位于前沿要害,对东魏的战事可以随时应对。如此一来,华州倒驻扎了重兵,首都长安兵力比较薄弱,却成了陪衬。
所以此次战败,长安一带防守薄弱,被叛军闹得天翻地覆。叛军的主要力量是东魏的降卒,但一些图谋不轨的当地土豪,还有为数不多的朝中官僚也加入了这场叛乱。
如此一来,整个关中乱成一团,一些刁民也浑水摸鱼,互相抢掠。败退回来的李虎将军倒是一马当先,杀回了长安。可是这些一向能征善战的西魏军士如今尽是伤残老弱,加上兵力不济,对这群乌合之众也无可奈何。徒手杀兽的李虎如今唯一所做的竟是保着太子逃向城外,而将长安拱手相让。
叛军更加有恃无恐,长安子城、咸阳都被他们轻松占领,只有长安大城在大都督侯莫陈顺(少年将军侯莫陈崇之兄)的英勇抵抗下,才得以苦苦支撑,没有落入敌手。关中一带阴云密布,民众皆惶恐不安,西魏遭遇了开国以来最大的危机。宇文泰应该庆幸当时沙苑之战后自己的慷慨,将俘虏多数放回——要是全部留下,关中这老窝便彻底没了。“屋漏偏逢连夜雨”是宇文泰此时最贴切的感受。
难道是宇文泰一时疏忽懈怠,没安妥后方就急于出击吗?情况并非如此,宇文泰有他不得以的苦衷——他和高欢的实力过于悬殊了。高欢可以下大赌注,一次出击,带个二十万士兵那是轻而易举,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家里依然人山人海,备用部队多着呢。而宇文泰要想与高欢决战,那非得翻箱倒柜、孤注一掷不行,不然档次相差太大了。如此一来,他家中便一贫如洗,简直穷得揭不开锅了。此次河桥会战,宇文泰便赌过头了——的确他还没实力与高欢硬碰硬地决战。如今一败,终于尝到了恶果。
后有东魏追兵,家园叛乱纷起,手中将士又筋疲力尽,此时的宇文泰终于到了焦头烂额的地步。
宇文泰一生中失魂落魄的时光并不多,这回属于最严重的一次,但他依然马上从心惊胆战中振作起来。面对混乱不堪的局面,竟胸有成竹地说:“我欲率领轻骑赶赴长安,必能手缚反贼。”山穷水尽之际,还能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胆识的确非同一般。
可他的手下早已觉察出事态不可小觑,万一宇文泰有个闪失,群龙无首,西魏便会面临灭国之灾。通直散骑常侍陆通更是洞若观火,看出关中大乱起因虽在于东魏降卒闹事,可根源却在于人心不安——关中百姓为反贼流言所骗,误认为东魏军队要倾国而来,皆惴惴不安。现在首要之务在于安稳人心,而安稳人心最好的方法是西魏大军全部杀回关中。他向宇文泰建议:此贼不可小视,应当全力以赴。虽然此时士卒疲惫,但精锐尚多,只要大军压境,叛贼何犹不克?
宇文泰向来是以少胜多,如今也不得不沦落到以多欺少的地步,为了万全之计,也只得答应。关中父老见到宇文泰,如同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皆惊喜万分,又热泪纵横:“不意今日复得见公!”宇文泰这一露面,这叛乱等于已平息了一半。
其实宇文泰如此踌躇满志,在于他在关中还有驻军。长安防备虽然薄弱,但是他的霸府华州却驻扎重兵,替宇文泰驻扎华州的是他的侄子宇文导。
高欢的儿子高澄早已长大成人,可以人模人样地替高欢在邺城看守场子,处理公事——可这家伙好色,经常勾引人家老婆,也惹了不少麻烦。要是只在家里玩玩倒不大碍事,反正高欢心胸宽广,为长远之计可以忍气吞声,但别人的老公可没有高欢这么好的修养,所以他这宝贝儿子迟早要惹出惊天动地的大祸来。
与高欢相比,宇文泰要累得多。此时他最大的儿子宇文毓刚刚满五岁,吃喝拉撒还不会自理,要替宇文泰排忧解难等于做梦——这得怪宇文泰自己磨蹭,快三十了,才生了第一胎,而北魏的皇帝基本上十三四岁就初为人父了。不过,宇文泰家族人丁兴旺——他是少子,兄长很多。虽然他的几位兄长早已死于非命,但给他也留下了好几个能干的侄子。其中最能干的属于他大哥宇文颢的两个儿子——宇文导和宇文护,他们皆已长大成人。宇文泰一旦出征,在华州看家护院的便是华州刺史宇文导。宇文导精明能干,此危难时刻,忙率兵来救,一路扫荡,杀得反贼人仰马翻,渡过渭河后,又与宇文泰合军,直入长安,轻而易举地将叛乱镇压下去。
惨败之后虽能转危为安,但这教训也足够宇文泰沉静一段时间了。至少他应该承认——高欢远比他强大,自己小打小闹可以,但一旦倾巢出动,两人力拼,自己必败无疑。如今天下三分,他应该把希望寄托在萧衍身上,在高欢这里他很难占到便宜。
西魏虽兵败如山倒,可另一主角高欢此时才从晋阳率领骑兵赶到黄河边。由于侯景的出色表演,高欢这登台唱戏的主角却成了鼓掌叫好的看客。虽然东魏大胜,但也元气大伤,加上又折损高敖曹等数员大将,也不敢深入追击,只是重新占领了部分河南之地。
此后,高欢便将河南之地完全托付于侯景,自己专心经营晋阳一带。其实,高欢并不十分信任这位狡猾的兄弟旧好,可这也是无奈之举。以前窦泰、高敖曹两人打仗勇猛,又对高欢忠心耿耿,是在河南牵制侯景的最佳人选,可这两人都倒在了宇文泰的脚下。如今高欢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捆住侯景的手脚了。在高欢眼里,最大的敌人是宇文泰——关中不灭,侯景这样的用兵天才就得重用。高欢有这样的自信:只要他活着,侯景就掀不起多大的风浪来。
此后,侯景专制于河南之地,雄兵数万,横行无阻,此地完全成为他的天下。东西魏双方拼得你死我活,可这场胜利从目前来看,却只属于侯景!
天崩地裂
让人头痛的玉壁
自公元534年东、西两魏并立开始,至河桥鏖战结束,高欢和宇文泰已经杀来砍去了整整四个年头。高欢在沙苑折戟沉沙,宇文泰于河桥损失惨重,这两头撕咬得死去活来的猛兽,终于都累得筋疲力尽,需要休养生息,以便发动更猛一次的进攻扑倒对方。
抢先爬起来的依然是高欢——谁让他体力好。休整四年后,到了公元542年冬天,高欢已基本休整完毕,占着“多收了三五斗”——东魏连年丰收,谷物堆积如山——抢先发动了攻击。高欢是个实在人,这次进攻的路线依然没有一点新意,还是按部就班地从晋阳出发,准备抢占河东的渡口后再渡河攻击关中。
这条线路对高欢来说,的确是轻车熟路。最早的潼关之战、沙苑之战,他都是从河东准备渡河,然后轻易袭击关中腹地。可时过境迁,自沙苑败后,河东地区早已被宇文泰爱不释手地抓在手中了。河东地区虽然不大,可是历来却为兵家所重:易守难攻。它的西面和南面是滔滔的黄河,东边有群山环绕,而北边则有峨嵋台地和汾水天然屏障拱卫。自从东、西魏分裂伊始,高欢和宇文泰是划河而治,按理说,河东应属于高欢的地盘。可宇文泰硬生生地把这地盘抢过来,变成了高欢眼皮底下的一枚毒刺。尽管高欢也多次想夺回此地,可惜,他每次投入的兵力过于吝啬,加上遭遇了西魏的顽抗,一直未能如愿。
这回高欢又是倾国而来——吹角连营四十里,排场极其浩大。如果说高欢这么精心准备只为重夺河东而来,那是有点小看他了。高欢的目标是关中,是整个西魏,而河东在他眼里只是一颗顺手要拔掉的钉子而已。但他料不到就是这颗小小的钉子却绊住了他前进的步伐,让他伤得头破血流、寸步难行。
高欢从晋阳发兵要进入河东腹地有两条路。第一条是闻喜路线。不过这是一条不寻常的路,只适合驴友探险旅游——路上地形复杂,道路崎岖狭窄,容易遭受伏击,路上的绿林好汉(河东豪族)也不少,不利于大军通行。
第二条是龙门、汾阴路。这线路可是阳关大道,路宽道平,适合领导带领大队人马视察。而且从晋州到龙门一段还可以水陆并进,运输粮草辎重都顺风顺水。 高欢的职业是领导,不是驴友,对游山玩水不感兴趣,所以对这条大路钟爱有加。他每次讨伐关中都是选择这条路线——从晋州从容沿汾水而下,抵达龙门后接着南下至蒲津渡口,然后渡河。但这回老驴友碰到了新山水,这路上竟然又多了一道风景——玉壁城。
玉壁城的确是刚刚长出来的,从前这个地方并不惹人注目。
玉壁和龙门渡口隔水相望,汾水是它天然的堑壕。面对汾水两岸,它的位置更是居高临下——处于峨嵋台地之上,险峻天成,东西北三面都为深沟巨壑。其实只要对“玉壁”两字顾名思义,就能想象出这个地方的险峻。而不幸的是,玉壁却是高欢从龙门进入汾阴,南下蒲津渡口的必由之路。当然高欢也可以冒险从汾水北岸的龙门渡口西渡黄河,不过一旦大军渡河后,玉壁的西魏守军便会出来骚扰,切断粮道,这样深入敌境的大军更会军心不宁。这不符合高欢稳扎稳打的追求。
绕不过去,又难以拔除,玉壁便是这种让人头痛万分的地方。玉壁城的建立得归功于赌徒王思政。河桥战后,他对局势洞若观火,知道不久高欢定会卷土重来,而他对高欢进攻的路线更是了如指掌。河桥战后,王思政便慧眼识珠,看中了玉壁这块风水宝地,在此大兴土木,不久玉壁就在高地上拔地而起,雄视着汾河两岸。玉壁城中的常备守军在八千左右——太多了也不行,粮草供应不上。
如王思政所料,高欢终于又率军来到玉壁城下,为此王思政已经精心准备了四年。这是一个可怕的对手,对高欢了如指掌,高欢却毫无知觉。
此时的高欢还是踌躇满志,以为能轻松拔掉玉壁这颗钉子。这次进攻,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冬天——深秋和冬日一直是高欢偏爱的季节,山寒水瘦,汾水流量骤减,适合大军涉渡。
高欢先是一封招降书传给王思政:“若降,当授以并州。”这橄榄枝的确诱人——王思政并非宇文泰的嫡系,长久遭受冷落,若只为富贵考虑,很有可能心动。
王思政很有趣,只回了这几个字:“可朱浑道元降,何以不得?”可朱浑道元是侯莫陈悦的死党,侯莫陈悦死后,绕道千里迢迢投奔高欢——结果也没捞到什么大官。王思政是在含沙射影指责高欢言而无信。
招降不成,那就只能消灭——高欢带着几十万人马将玉壁城这弹丸小地围得水泄不通。
高欢昼夜攻围,可玉壁城在王思政的防守下岿然不动——人马虽不足万,防守却绰绰有余。玉壁城周围全是百丈悬崖,只有南边有路,不过这条路相当狭窄,不适合伸展手脚,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意思。高欢人多势众,优势兵力难以展开,一直被压着打,占不到一点便宜。
老天也开始捉弄起高欢来了——竟然下起了大雪。一时天寒地冻,粮草供应不足,士卒在城下又死伤无数。九日九夜围攻过后,除了堆积如山的尸体,高欢一无所获。而这时更不利的消息传来——他的老冤家宇文泰已经率大军前来救援了。撤军成了唯一的选择,面对这不足万人的防守,高欢只得伤痕累累地离开了。
玉壁,我总会回来的——我想高欢心里是默念着这句话咬牙离开的。不过,玉壁也在深情地等待着高欢的再次到来。
唯一得到好处的是可朱浑道元,一个月后,他莫名其妙地被加封为并州刺史。
如以大雁不过衡阳相比,玉壁之于高欢(沙苑败后),河桥之于宇文泰,这两地都是他们难以逾越的雷池。
虎牢关的诱惑
高欢退兵后,宇文泰也像模像样地追击了一下,不过到了两人地盘的交界处也就立马打住了——做做样子、长长威风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