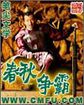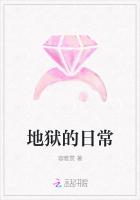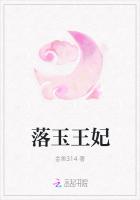随后的战局变化更加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宇文泰侥幸逃得一命后,慌乱地逃入关中,屯兵渭上。这时,宇文泰最担心的是:高欢一旦杀来,自己手中无可挡之兵——鲜卑精锐在邙山一战中伤亡惨重,已无力反抗了。高欢率领大军乘胜即将追至弘农。然而,这路越顺畅,高欢的心也越虚。河北大族封子绘(封隆之之子)目光如炬,看出西魏军队已是苟延残喘,便给迟疑不定的高欢打气:“东西一统,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汉中,不乘胜取巴、蜀,失在迟疑,后悔无及。愿大王不以为疑。”
高欢非常赞同,但心中依然没底。本是他最该独断专行的时刻,他却发扬起民主精神来了,他心里还是缺少那种一意孤行的霸气——他召集了众将一起商议。可是东魏军队早已损伤惨重,谁都不愿再去拼命送死。鲜卑将领们个个鼠目寸光,异口同声地回答:“野无青草,人马疲瘦,不可远追。”
唯有高欢手下的文士陈元康执意追敌:“两雄交争,岁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时不可失,当乘胜追之。”
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动嘴皮子的是你,到时战场上送命的却要换成我们——陈文人的一番话当然不会得到这群粗人的赞同。可高欢却觉得在理,但新的疑问又来了:“若遇伏兵,孤何以济?”
陈元康反应敏捷,立马旁征博引:“大王前沙苑失利,彼尚无伏;今奔败若此,何能远谋!若舍而不追,必成后患。”高欢迟疑半天,依然不敢冒进——他一生难得一次在沙苑冒险,结果兵败如上,此回当然更加慎之又慎了。但高欢又觉得太不甘心,便象征性地派了手下刘丰生率领数千骑追击宇文泰,自己率众东归。一统江山的丰功伟业就此毁于一旦,此后高欢一直后悔莫及,临时死前依然对儿子高澄喋喋不休:“邙山之战,吾不用陈元康之言,留患遗汝,死不瞑目!”
真实的空城计
刘丰生是从西魏逃过来的将领,原是贺拔岳死对头灵州刺史曹泥的女婿,也是一员虎将,但结果他连这点象征性的活都没干好。
弘农是刘丰生此行的第一站,一座很小的城,以前是储存粮食的,并非军事要地,是那种立马可下的弹丸之地。来势凶猛的刘丰生追到弘农后,却看到了一副奇异的场景:城门敞开着,守城的敌军也懒洋洋的,全城几乎是张开双臂迎接远客的架势。然而守城将领的名字却让刘丰生不寒而栗——王思政,那位让高欢也头痛不已的守城名将。
王思政这样的奸诈之徒会大开城门迎敌?一定有埋伏!刘丰生再也不敢停留了,做了一个非常明智和惊人的决定:撤军。明明乘胜来追,可一见敌方城门大开,刘丰生却变得如同惊弓之鸟,慌忙逃回——可见整个东魏的士气早已坠地。
其实,这只是赌徒王思政赌的一个游戏——继在宇文泰面前掷的卢之后,他又赌了一把。可这回,他下的注可大多了,除了他自己外,还搭上了弘农全城军民的性命。王思政从玉壁城赶来本是去接收虎牢城的,结果走到半路,便遭遇了宇文泰的邙山大败。宇文泰非常慷慨,顺便让王思政殿后去防守弘农城。
这实在是个不能完成的危险差使:弘农城以前是粮仓,没有坚城厚壁,可轻易被攻;西魏兵败如山,宇文泰自己几无可用之兵,哪还会留给精兵强将让王思政差遣?无险可守,无兵可用,全城之人皆惴惴不安,而且追兵即刻就到,王思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而王思政却拥有一样连这时的高欢都没有的东西——良好的心态。既然无险可守,那么索性大开城门;既然无兵可用,那么无需枕戈待旦,晚上解衣而卧便是。这一幕我们很熟悉,都知道叫“空城计”。当然白日里王思政也没闲着,经常对将士循循善诱,轻易消除了将士们的恐惧之心。所有的人都等待着奇迹的发生——如果等不到奇迹,那等来的便是灭顶之灾。
数日后,刘丰生马不停蹄地赶来。可他疑惑一阵后,又惊慌失措地逃回去了——刘丰生对自己的这个举动肯定要懊悔得痛彻心肺,因为数年后他便是死在王思政军队的乱箭之下。
王思政的空城计成功了,这个赌徒又赌赢了。前三国诸葛亮的空城计只是后人的添油加醋而已,但设想的情形倒是与后三国王思政的演出大致相当,估计那些擅长移花接木的后人在王思政这里定有不少借鉴。刘丰生退兵后,王思政便开始修城建楼、耕田存粮,弘农这时才具备点防守的能力。
引起高仲密叛逃的崔暹,高欢本想一杀了之,结果高澄将其藏匿,逃了一命。高欢依然不依不饶,认为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要痛杖一顿。高澄非常无赖,便去威胁高欢最信任的陈元康:“卿使崔暹得杖,勿复相见!”陈元康只得苦劝高欢:崔暹是帮你儿子(高澄)咬人的狗,打崔暹其实就是在打你儿子。以后你儿子如何服众,如何能做好你的接班人?高欢觉得言之有理,结果崔暹毫发不伤。
罪魁祸首高澄却成了邙山之战最大的受益者。全军将士血流成河,父亲高欢几乎命丧黄泉,却只满足了高澄一人之淫心。宇文泰败后,虎牢重又回到了高欢手中,而高仲密的妻子李氏自然也落入了高澄手中。他衣履光鲜地去会见李氏,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今日何如?”
亘古不变的是,战争虽只是男人迷恋的游戏,而战后的悲剧却全得由女人承担:李氏默然接受了——因为她唯一的依靠,那个靠不住的丈夫高仲密早已逃入关中了。而高氏家族在数年之后依然要为高澄这次的淫贱之行付出代价。
在胡汉间摇摆
高欢的草莽兄弟
高欢这一生几乎是为了宇文泰而活,可除了宇文泰这个如鬼缠身的魅影之外,他手下那一帮胡作非为的弟兄也让他焦头烂额。在高欢与宇文泰拼命搏斗的十余年间,他为了“漂白”自己这些草莽兄弟也同样殚精竭虑。
高欢接管的是北魏元氏的天下,说得更精确一些,应该是尔朱家族的江山。元氏皇族的奢靡无度和尔朱家族的横征暴敛是高欢亲历的,这两位先行者的败亡给了高欢这个后来者无尽的思考。在高欢眼里,元氏皇族的百年基业到了胡太后这里之所以变得风雨飘摇,直至轰然倒塌,最主要的原因是穷奢极欲的生活像慢性毒药一样侵蚀了鲜卑族人强壮的肌体。这些本该驰骋疆场的鲜卑健儿变得跟他们统治下的汉人一样柔弱,忙于吟诗作画,忙于子曰诗云,野性在酒池肉林中消亡殆尽,结果被尔朱氏轻易夺了江山。奢靡,这可怕的病菌,是来自六镇边陲的高欢需要时刻警惕的。
取而代之的尔朱家族虽然凭借武力迅速地接管了北魏王朝,粗野无知的他们却痴迷于武力,盲目崇拜着血与火的原始力量,犯下滔天罪恶,引起人神共愤,结果立马消亡得无影无踪。从尔朱家族败亡的历程中高欢懂得:痴迷于武力只有一种结果——失去的永远会比得到的更快。
他们的覆辙当然不能重蹈——既要防止走上元氏家族的奢靡柔弱之路,以致江山移位,同样也要避免建成尔朱家族那种纯粹野蛮的尚武王国而失去民心。高欢要走的是一条文武结合的新路。但高欢在接管北魏江山的同时,不可避免的是他对北魏固有的顽疾也要照单全收,局面远比他想象的复杂。而且高欢明白自从起家之时,他自身,他的家族,他的兄弟就已携带着很多顽疾——镇相连,似影追形,分不开如刀划水。消除这些顽疾,光凭借高欢一人意志的确有点蚍蜉撼树的意味。高欢虽然是鲜卑化的汉人,但他统治的基础,他力量的根源上都深深地打着这四个字的鲜明烙印——六镇鲜卑。而要消除这四个字的消极影响,就够高欢忙上一辈子了。
和高欢一同打天下的人很多,而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人投奔,但按时期的先后和关系的亲疏,他的权力圈子基本可以分成这么三批。
第一批,高欢最核心的权力基础,是他在怀朔刚起家时的那批伙伴。这些人与高欢不是知根知底,就是沾亲带故。比如他的姐夫尉景,当初怀朔的小狱吏,如今已贵为太保、太傅;高欢的小舅子娄昭,已做过大司马、领军这样的高官;他的老朋友司马子如已成为左仆射,掌管朝政了。加上侯景、孙腾、段荣等人,他们和高欢意气相投,对他忠心耿耿,一同出生入死——一同在河北之乱中浑水摸鱼,一同在尔朱荣帐下建功立业,一同谋划反对尔朱家族,是高欢取得天下的支柱。这批人现在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勋贵。但这些和高欢一同出生入死的兄弟如今却成了高欢最头痛的一群人。
第二批成为高欢手下的是六镇降户,就是从尔朱兆手中骗来的那二十万人。如果说怀朔旧友是高欢权力集团的塔尖,那么这二十万人便是他坚实的塔座,是他维护统治的中流砥柱。这些人本在尔朱氏手下受苦受难,是高欢带领他们翻身做主,过上了吃香、喝辣的生活,自然对高欢死心塌地。作为东魏王朝的主力部队,他们并非居住在东魏的首都邺城,而是被高欢煞费苦心地安排在晋阳,拱卫着他的丞相府——邺城一旦有点风吹草动,随时可以驰援;关中的宇文泰稍有动静,也可以立马南下渡河与其一争高低。
第三批入伙的成员要复杂一些:河北大族的乡兵和元氏皇族的残余军队。河北大族的乡兵本也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在韩陵大捷中立下汗马功劳,但自从高乾无辜被害、高昂困死城下、高慎叛逃入关之后,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元氏皇族的残余军队,人数还不少,他们有一个称呼——六坊之众。他们也是鲜卑人,本居住在洛阳的六坊一带,在高欢迁都时便搬到了邺城。虽然他们也是鲜卑,但与那些在边陲之地土生土长的六镇兄弟相比,汉化程度较高的他们要文质彬彬很多,战斗能力自然不能与六镇的同日而语。不过他们虽在战场上纵横驰骋的本领差点,但看家护院的能力还是有的——他们大多驻扎在首都邺城,替高欢监视着元氏家族的一举一动,当然也防备着西魏军队的渡河北上。到了高欢儿孙的手里,由于胡化之风愈演愈烈,这群鲜卑人又重新燃烧起了野性。高欢的那个疯癫儿子高洋从他们中挑选出了一批能以一敌百的勇士,称为“百保鲜卑”——在战场上是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力量。六坊之众里当时另有一小部分跟随北魏孝武帝投奔了长安,现为宇文泰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