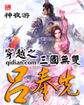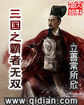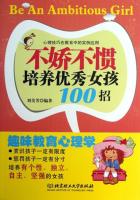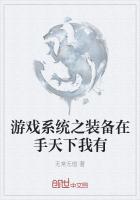当然关中、河东一带的汉人大族也有加入宇文泰的部队中。比如王罴,他便是长安的大族。但这位跟豹子一样凶猛的关中豪族在北魏之时便参与行伍之事,并非宇文泰新近招募。其他的汉人大族们虽有自己的武装——乡兵,不过他们得自己掏腰包供养这些人。而且这种武装力量基本都驻扎在自己的地盘,主要用来地方自卫,并不长年累月地跟着宇文泰四处打仗。比如,商洛的泉氏家族,武装力量也颇为雄厚,不过他们只是在东魏军队来犯时才予以迎头痛击,至于河桥、邙山这种到外面惹是生非的场面是找不到他们的身影的。还有河东的薛姓家族也是如此,他们只在自己的地盘上活动筋骨,纠缠纠缠路过的高欢。
在邙山之败前,宇文泰领导的军队一直是这种严格胡汉分离的方式。他跟汉族地方武装力量之间的关系只能用这句话形容:偶尔抱团打仗,一直分灶吃饭。
然而这几年的形势发生了逆转:宇文泰一败于河桥,二败于邙山,两次大败皆损失惨重;尤其是邙山之败让他差点将原有的鲜卑家底赔光——被歼灭的就达六万之多。高欢虽然也有数次惨败,损耗了不少鲜卑部队,但原先鲜卑族人聚居之地皆是在他统辖之下,他的鲜卑兵源用之不竭,犯不着挖空心思拉扯新的汉人入伍,所以军队上下还是清一色的鲜卑风格。
可宇文泰的情况却与高欢不同,他属于外来政权,本来就这么点鲜卑家底。麦子这一茬割了,明年依然还能长出来;人头割掉了,还长得出来吗?即便此时立刻动员境内的鲜卑家属们鼓足干劲、昼夜生产,可培养出下一代的鲜卑将士们最快也得十几年的光景。
到哪里去寻找新的有生力量呢?这是摆在宇文泰面前最迫在眉睫的问题。邙山之败后,宇文泰终于想通了:打开军门,让他们涌进来——史称“广募关陇豪佑以增军旅”。
府兵制
这是一个伟大的开始。从此刻起,那些本只忙于耕织的汉人,终于也逐渐大量地进入了中央军队——要是从“五胡乱华”开始算,在北方这块土地上,汉人拿武器的权力已经被剥夺了两百多年。他们以前选择的是结坞自保、迎来送往,在自己的地盘上小打小闹而已,至于哪个族姓问鼎中原和他们毫无关联。
如今,他们终于也能用自己的手来参与军国大事,虽然还有太漫长的路要走。但谁都明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只有手中握有武器的,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管是民族,还是个人。
先是豪族的涌入,后来又有自耕农的加入,到了宇文泰的儿子宇文邕时,汉人在北周部队中已过半数。其实这是宇文泰唯一的选择,若没有关陇地方豪族的支持,他的功业便是无源之水,终会干涸。
汉人人头攒动地挤进来了,但要让这个好几百年在北方一直习惯被异族踩踏的民族一夜之间变得能征善战无异于缘木求鱼。“泼墨汉家子,走马鲜卑儿”,是当时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恢复汉人那种“虽远必诛”的尚武精神的确是一件让宇文泰费尽心思的事。在恢复他们的野性之前,宇文泰当然不敢赶鸭子上架——绵羊即便成群也永远不是一只狼的对手。
除了汉人的柔弱外,能征善战的鲜卑战士存在的一个问题也让宇文泰顾虑重重。比起高欢来,他属于外来政权,而他最核心的武川属下虽然都是知根知底的老乡,但有一点却始终让宇文泰心存顾虑——人心并未牢固到稳如泰山的地步。鲜卑战士的很多家属都还滞留于晋阳、洛阳一带,虽然在尔朱荣死的那一年,贺拔岳已经接了不少家属去落脚关中一带,但多数是男丁,其余的女眷都是天各一方。比如独孤信的妻儿老小都一直待在洛阳,他的长子直到北周灭了北齐后才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们团聚。贺拔胜的几个儿子都捏在高欢手中,最终成了高欢泄愤的牺牲品。而宇文泰自己的亲友滞留晋阳的也为数不少,后来宇文护(宇文泰的侄子)掌权时,他那被扣押的母亲还成了外交的人质,差点误了军国大事。
如果高欢用家属来招诱自己的属下,那肯定是非常奏效的,一旦人心离散,便会产生土崩瓦解的结果,那么留住将士们的心对宇文泰来说也是必须解决的燃眉之急。
一要恢复汉人的尚武之气,二要消除鲜卑将士们的思乡之苦,唯有两头并举,才能打造成一只战无不胜的虎狼之师。而除了这两点外,宇文泰还得解决好军队中胡、汉杂处的问题,免得造成东魏那种水火不容的局面。在如此艰难险阻面前,宇文泰最终排除万难,在痛苦的摸索之中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路——府兵制。这制度后来被北周、隋、唐一直沿用,继承并发扬光大,发挥功效达两百年之久,成为隋、唐建立攻无不克、四方来朝的赫赫功业的重要军事支柱。
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让汉人自身恢复野性是很艰难的,非得借助外力帮忙不可,而最现成的方法便是让他们借助鲜卑的外壳,重铸华夏雄武之魂——把汉人改变成鲜卑人!
更换人的族姓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更何况是如此大量地改变,万一安排不妥,有可能会产生玩火自焚的后果。但幸运的是,将鲜卑风俗和汉家仪礼混搭却一直被宇文泰运用得游刃有余。
鲜卑旧的兵制是八部制,属于游民部落组织形式,早已被汉化的北魏王朝弃置不用。而如今宇文泰却要重新抖落这旧衣服的尘埃,重新穿在西魏的身上。既然叫八部制,顾名思义当然得找出八个当家作主的人来。宇文泰自己早已是柱国大将军,于是他又加封李虎、赵贵、李弼、于谨、独孤信、候莫陈崇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亲信为柱国大将军。当然,为了发扬民主的风格,皇族里自然也要有人列席一下。结果元氏里比较听话的广陵王元欣被相中,也名列八柱国之中。不过元欣始终是个花瓶,没有带兵打仗的权力。
宇文泰自己依然高高在上,总管整个军事。整个西魏的兵权全部处于这八大柱国的统领之下,和皇帝之间全无关联了。除了这八大巨头外,自然还得增设其他的军衔,便于层层控制。于是在李虎等六大柱国下再分设十二大将军,像达奚武、王罴、杨忠等都是大将军。十二大将军下面再管理两个开府,共二十四人。如此一来,西魏的军队共分为二十四军,整个金字塔形的军事领导机构便基本形成了。
当官的有了,士兵自然少不了。按理说,既然是部落兵制,自然得从鲜卑族中挑选。可是,鲜卑人早已伤亡惨重,提供不了充足的兵源。所以这些新征的府兵除了原有的鲜卑士兵外,主要是从汉民中挑选。可汉人放着种田耕地那好好的日子不过,愿意跑到战场上流血卖命吗?何况当时当兵差不多是被认为跟当囚犯一样低贱的事。很明显,脑子正常的汉人是不会去当兵的。
可宇文泰却轻松做到了,让汉人欢天喜地地当兵去。他的对策便是提高府兵的待遇。只要被挑中当府兵,你身上的各种捐税便全免了。所以要想当府兵也很不容易,门槛很高。第一你非得家境好(六户中等已上),自己得有经济实力提供弓刀一具,不然官府肯定不会到你家要人。第二你家里人丁也得兴旺,男丁得在三人以上,官府才会挑人——目的便是要精挑细选,挑出身高体壮能打仗的。
这感觉很好,当初六镇的士兵可是跟罪犯为伍,当兵是件很不光彩的事。如今摇身一变,不仅可以稳吃皇粮,连苛捐杂税都全给免了,一旦建功立业,那更是光宗耀祖的事,于是参军的人也络绎不绝了。这种待遇汉人自然欢迎。而原来的六镇鲜卑更是热情高涨,重新又回到部落兵制年代,又回到鲜卑人当家做主的年代——人生又有奔头了。
一下子找来这么多人,自然得勤加操练。宇文泰招来这些人以后,上半个月主要操练步伐、巡防之类的基本功;到了下半个月,便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而这演习便是在同州一带进行。这些士兵在部队里也待得非常舒服,用不着牵挂家里一亩三分地的年成,不用打仗的时候还得担心家门口会出现那些凶神恶煞的征粮官——自然一心一意地当兵打仗。
重又回到鲜卑的部落时代,看似是宇文泰的一种倒退,其实不然。对宇文泰来说,暂时地恢复鲜卑野性是迎合当时的潮流的。尤其在军事领域,唯有如此才能激起鲜卑士兵无穷的战斗能力;唯有提高他们的待遇,才能激起他们战斗的激情。鲜卑兵制从形式上是对鲜卑士兵的一种安抚——现在恢复部酋制了,你们得好好干;从待遇上对参军的汉人来说也是一种诱惑,待遇提高了,自然要卖力气了。
与高欢一直纯粹依靠鲜卑族人打仗相比,宇文泰这种剧痛过后的选择明显要高出一筹:打仗不再是鲜卑人之事,汉人也应该参与。的确,宇文泰这次的举动是在被动情况下的一次主动抉择——是在被高欢揍得遍体鳞伤的困境中的选择。但既然情势如此,他便索性将胡汉杂糅,最终创建出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