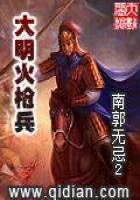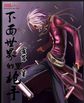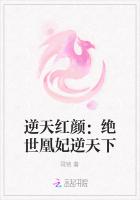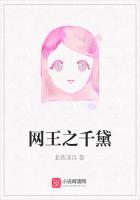打仗的队伍是初具规模了,但要这些人能在枪林箭雨中安心卖命,肯定得提供更大的实惠。在这三国鼎立的世界里,对宇文泰来说,目前最大的对手是高欢。高欢仗着北魏王朝留下的殷实家底和六镇鲜卑的军力,几乎年年都来扰乱。要是硬拼家底,宇文泰远不是对手——至少两次正面的交战他都败得一塌糊涂。
至于江南的梁武帝,这老头虽然行将就木,却自以为代表着华夏文化的正统。而且南北两朝对立已有百年之久,如今北朝又一分为二,南朝自然更是块难啃的骨头。
拼力气,他不是高欢的对手。高欢比他野,鲜卑六镇的精华都集聚在高欢手中,整个东魏弥漫着的都是鲜卑的气息。而他手中只有武川(六镇之一)一隅的兵力,要想在武力上与高欢争雄,的确是蚍蜉撼树。
比文化,他与萧衍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萧衍儒道释无所不通,南朝又被中原士人认为是华夏正朔所在。而关中经过历代战火,早已民生凋敝、斯文坠地,连“文化寻根”都无从找起,更遑论用文化功业吸引士人了。
三家比较起来,宇文泰的家底最差,处境最忧。如何冲出重围,灭掉这两个难缠的对手,是宇文泰一生都需探索的问题。面对重重困境,宇文泰经过苦思冥想,终于想出制胜之招——敌人的长处也正是他们的致命之处。
高欢看似强大,鲜卑兵源充足,可举国上下鲜卑化过于严重。的确短时间内活力无限,可长此以往,却会成为难以承受之重。鲜卑势力的庞大和独断,其实也是高氏家族的负担,使得高欢的每一步改革都举步维艰,任何一次的奖惩都几乎到了牵一发动全身的地步。
高欢迎合了胡化的潮流,依靠六镇,击败了尔朱家族而取而代之。或许高欢自己是清醒的,他还能掌控局面,还能主动地引领着这种胡化的浪潮。但在六镇胡化浪潮的吞噬下,他的子孙后代还能全身而退吗?成也六镇,败也六镇!关中的宇文泰对此洞若观火。
正是六镇的无往不胜,使得高氏家族过于迷信了鲜卑的武力,忽视华族的利益,造成境内胡汉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这种担忧,宇文泰没有——他的鲜卑精锐已伤亡过半。
而他的另一位对手——梁武帝,继承了华夏正朔,而且文治武功半世,整个天下看似莺歌燕舞,的确能讨得中原士人的欢心。但是表面上的繁荣已经遮掩不住南朝的奢靡不振。梁武帝的佞佛已让国库一空,整个民间怨声载道。梁朝的军队貌似强大,其实不堪一击。梁朝在北方如此混乱的局面之中,也只有陈庆之取得了昙花一现的战绩,可见在兵势上早已是强弩之末。
正是这半世的繁华让南朝故步自封,奢靡无度。而这种担忧,宇文泰也没有——他地偏人少,一穷二白。
一无所有就是宇文泰最大的财富,他可以大刀阔斧地改革。虽然他依靠鲜卑起家,而鲜卑势力在关中的地位并没有强势到可以凌驾一切。正是与当地华族之间这种势均力敌的局面,使得他们选择了妥协。而妥协便意味着融合和壮大。宇文泰轻松地上路了——这条路半个世纪前有人刚刚走过。
府兵制是宇文泰的第一步,当初他设计这套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收买鲜卑将士的人心。而这套原始的鲜卑部落兵制,竟然被宇文泰从汉家原始典籍《周礼》里找到来源——府兵的六军正好跟《周礼》的六军一一对应。而恢复周礼虽只是个面子工程,却也能在相当程度上来收买关中华族的人心——关中正是周王朝发祥之地。周文王凭借百里之地起家,经过父子两代苦心经营,终于灭商,天下归一。既然他们可以,当然我们也可以——所以还有比扛起周礼这面旗帜更能激励当地华族的人心吗?没有。这正是宇文泰的高明之处。
当然我们对宇文泰不能期望过高,他本身并没有这样的远见卓识——一直长在穷乡僻壤之地的他对博大精深的汉家文化并非十分精通。但作为一个老板,自己无需面面俱到,只要找一个懂行的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而宇文泰手下就有这样的人——苏绰。
苏绰
苏绰是武功人,他对西魏的影响,相当于诸葛亮之于蜀汉。可诸葛亮的功绩随着刘禅的败亡被一抹而尽,而苏绰的功业却依然薪尽火传,对后代影响深远。正是苏绰的存在,才让出自武川的西魏政权浸染了更多的文化气息,“文化建设”的局面也是一片形势大好。没有苏绰,西魏文化制度的华丽转身肯定要耽误很多年。
可苏绰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他被从兄苏让举荐给宇文泰后便一直沉默不闻,每日只是埋首公文而已,并未受到特别的青睐。不过,毕竟他的才气太大,想藏都藏不住。别人遇到公事上的疑惑之处,都非得来请他答疑解惑不可。可即便如此,他还是被搁置了一年多。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虽然很多执著地抱着这种信念的人其实往往都是石头。
一日,宇文泰和手下的周惠达商量军国大事,结果这位当朝仆射却无法解答。周仆射很老实,说要出去找个人商量商量。他找的人便是苏绰。面对这难题,苏绰如庖丁解牛般地给出了最佳答案。周惠达便迅速转呈给宇文泰。宇文泰非常满意,忙问何人所解。周惠达很厚道,忙推荐苏绰,说他有王佐之才。宇文泰听后很是欣赏,但还是很保守地给了苏绰一个著作佐郎的位置。倒霉的苏绰依然没有机会跨入宇文泰的核心圈。
转眼,宇文泰一日前去昆明池游山玩水,路上看到了一个西汉时代留下的仓池。这古池一下子勾起了这位柱国大将军刨根问底的兴趣,可他周围的这群粗人却不能给他答案。于是,立马又有快嘴的人举荐苏绰。这个让大伙搜肠刮肚的难题,到了苏绰这里便成了小儿科,三言两语便被苏绰一一点明。寻到正确答案的宇文泰很兴奋,心中那团渴望知识的火焰被博学的苏绰点燃了——他又转而问了很多别的问题,结果苏绰有问必答,两人越扯越开,直至三皇五帝、历代兴亡,全都天马行空地说了起来。面对宇文泰如此可怕的发散性思维,苏绰只有一种反应——应答如流。
宇文泰拜服了,他和苏绰一块骑马并行骑到昆明池,然后一块骑了回来。跟在后面的随从肯定要怒火连天了,本来是跟着宇文泰来钓鱼的,结果大伙连个鱼鳞都没捞到,就两手空空跟着回来了。不过,还有人钓到了鱼,他便是苏绰,他凭借渊博的知识终于钓到了宇文泰这条大鱼。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有点俗套,和其他君臣的风云际会完全一致。宇文泰和苏绰回城后,又是谈天论地,一直“缠绵”到天亮。苏绰彻底征服了宇文泰,他被任命为大行台左丞,参与决断所有军国大事。宇文泰文化制度改革的思想全来源于苏绰。苏绰寻到的依据是周官之礼——关中是姬周发祥之地,西魏采用周礼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借用周礼改革的人既有前人,更有后来者。王莽是先行者,后来的武则天、宋神宗也都是周礼的崇拜者。可他们的结局都一样,不是身败名裂,便是不了了之。唯一成功的却唯有宇文泰。因为宇文泰比他们聪明,他借用的是周礼这个壳,并不完全生搬硬抄。他把周礼当作了外衣,披披就够了,穿得太紧反而碍手碍脚。披着这样的一件汉家服饰也足够收拢关中豪族的心了,起码宇文泰让他们相信:这天下是有汉人的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