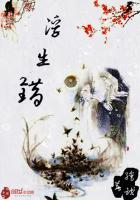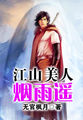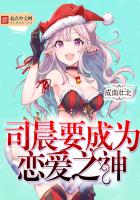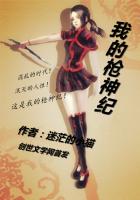不得不反的侯景
在东魏、西魏、梁这三国鼎立的世界里,侯景一下子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相比起高欢没落官宦的出身,侯景的身世更为卑贱——他连祖父的名字都不知晓。他身材矮小,而且天生还跛了一腿,刀剑弓马非其所长。这一切都似乎注定,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他要受人宰割。但事实却完全相反,这个可怜的跛子在少年之时就在乡里横行霸道,出道后更是让所有的人为之胆寒。与高敖曹、彭乐这些靠身体、力气获得尊重的人不同,他依靠的是智慧。
他在尔朱荣手下担任前锋时,击败过葛荣,从此威名大震;他在高欢手下时,打得贺拔胜单骑南逃;他在河桥之战中还击败过宇文泰,打得宇文泰毫无还手之力。然而这一切的胜利都改变不了他替人卖命的命运——和他一同出道的高欢一直压着他。可如今高欢死了,要换上那个膏粱子弟来继承家业了,侯景还能为之卖命吗?即便侯景愿意继续效劳,可高澄还能容忍他吗?想反,也不得不反,是侯景此时的真实窘境。
对侯景来说,造反的代价是巨大的,他的妻儿老小全被扣押在邺城。不管成功与否,这几十口人的人头落地是避免不了的。更重要的是,面对高澄,侯景的胜算并不大。侯景手下有十万人,还有河南十二州,可真的要造反,肯定要先跑掉一半。因为军队的家属几乎全集中于邺城和晋阳。但侯景还是要反,因为除了束手就擒外,这是唯一的选择。
侯景之所以敢反,是因为天下三分,他拥有巨大的斡旋空间。只要他倒向任何一家,都会让东魏心惊胆战。他要是投奔宇文泰,西魏唾手可得河南之地,一旦时机得当,攻打邺城也是迟早之事;而他要是投奔梁朝,梁朝也能将势力巩固到黄河南岸,东魏的局势也将岌岌可危。而高澄也看到了这可怕的未来,他竟然胆小地要杀崔暹以谢侯景。朝中的鲜卑权贵也煽风点火,纷纷指责正是崔暹的乱咬乱啃逼反了侯景。陈元康以汉景帝的晁错之事相喻,才让高澄痛下决心,决定讨伐侯景。
背离了高家,侯景当然得寻找新的东家。西魏和梁都是好的买主,对侯景来说,得好好掂量,选择一位。西魏跟高家是仇敌,当然会张着臂膀欢迎自己,派军增援是必定的。可宇文泰是何等狡诈之人,不好糊弄,一不小心,自己这点家底会全给他吞了。这东家心虽诚,但心也凶,得提防着。
梁朝跟高家和好了十年之久,你来我往,表面上一直客客气气,似乎不大愿意为了自己和高家翻脸。可人老了,心总会越来越贪,河南之地这么大一块肥肉萧老头怎不眼馋?十万人马和十年友谊相比,孰重孰轻,还不是一目了然的事。而且,比起宇文泰来,这萧衍老头好糊弄得多,而朝中掌权的朱异又是个见钱眼开的主,诱之以利,萧老头肯定来帮忙。
侯景的选择果然与众不同,他先到西魏请求援军,然后又立即到梁朝请援。这是侯景的狡猾所在,只要把所有的势力都搅和进来,他浑水摸鱼的机会就大得多。到时,这三家反目成仇,扭成一团,他倒可以坐山观虎斗了。不甘居于高澄之下,他难道愿为宇文泰、萧衍卖命吗?
一女二嫁,三国来会
西魏的反应很快,加封侯景为太傅、上谷公,但没有出兵。因为宇文泰吃过侯景的大亏,当然得谨慎一些,先得观察观察。
而梁朝的反应要复杂很多。虽然侯景的使者吹牛的本事不错,说是河南之地已尽归侯景所有,继而掌控宋齐之地也将易如反掌。但诱饵虽然鲜美,却没有勾起梁朝群臣的馋虫,反而遭到了他们的极力反对。反对的原因在于:他们脑子清醒,知道自己无能为力。
他们不愿打仗,因为打仗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好处。在梁武帝宽松的治国政策下,梁朝境内的民脂民膏就够他们搜刮了,何苦劳师动众地跑到北方去?
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确实不会打仗。常识告诉我们,那些连见到马都吓得半死的人是不会喜欢上战场的。当然他们还是说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得和东魏继续保持伟大的友谊,犯不着为了侯景和高家翻脸。
然而还是有一个人心动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位——萧衍。“若齐、宋一平,徐事燕、赵”的话打动了他,天下一统的机会就摆在面前,怎能让它擦肩而过? 真是一群鼠目寸光的家伙!但面对群臣的一致反对,他只得意味深长地说了 “机会难得”四个字。但无人领会他的微言大义。
萧衍下朝后,对侯景之事思虑再三,心里既割舍不下这块肥肉,又害怕战端一起,举国深陷泥塘,难以自拔。面对他的自言自语,权臣朱异嗅出了他的野心,立即建言:“侯景分魏土之半以来,自非天诱其衷,人赞其谋,何以至此!若拒而不内同‘纳’,恐绝后来之望。此诚易见,愿陛下无疑。”朱异,我们先得记住这个名字。他虽是梁武帝的红人,最大的权臣,可这家伙好像天生是为侯景生的,每一次愚蠢的举动总是给侯景带来惊喜。
除了朱异的恭维,让萧衍下定决心的还源自他自己的一个梦。两个月前,他做了个梦,梦见中原一带有敌境官员献地来降,当时还为这梦举朝欢庆了一番。今天,梦想成真了,侯景果然来了,而且更神奇的是:侯景决定投奔梁朝的那天,刚好和梁武帝做梦的日子吻合。
一切都是天意,天意当然不能违抗。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了:接纳侯景,出兵东魏!
当年元颢孤身一人来奔,萧衍都派兵护送,结果还占了洛阳;如今的侯景可是拿着千里土地、数万军队来的,局面要好得多。而且,北魏已一分为二,实力大大削弱,北伐更应胜券在握。然而,萧衍错了,时过境迁,南北实力的变化已超出了他的估计。
在这十几年的光阴中,南朝人在繁华中变得更加堕落、糜烂,而他们的敌人——当年不堪一击的鲜卑族,却在战争的狼烟中变得更加凶猛、剽悍。当南朝人变得更像羊的时候,他们又重新变回了狼。白袍军能取得昙花一现的战绩,全是因为有陈庆之这样的军事天才。可如今,梁朝举国上下还能找到一个能带兵打仗的良将吗?没有,一个也没有。
对梁武帝而言,这次北伐的确是一生中最好的时机。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还是把机会浪费得好。因为在战事上,对于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而言,机会往往也是最大的灾难。显而易见,萧衍没有这种能力。这回,我们得交代一下萧衍的年龄——八十三,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
这样的高龄,能活着在宫廷里伺候花花草草,已让人心惊胆战他的身体了;而如今却还要开疆拓土,决胜千里之外,过于勉强了。人老之时,戒之在得,对于此理,通晓儒家经典的萧衍肯定烂熟于胸。但他真正懂得这句话的含义时,却已深陷四面楚歌的绝境了——一切都悔之已晚。在做了如此可怕的一个决定之后,梁武帝并没有忙着细细筹划,而是再次去了同泰寺舍身,把自己卖出了天价——与十年前陈庆之北伐时如出一辙。而这一待,又是三十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