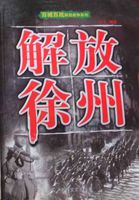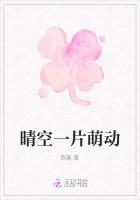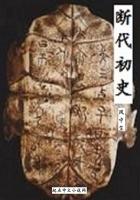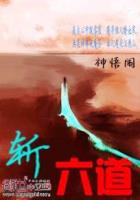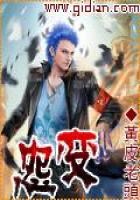侯景只负责动手,文字游戏自然有手下的王伟效劳。
卿本佳人
王伟博学高才,也是世家子弟,他的一生用“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形容最贴切不过。这位颍川的才子自从上了侯景这条贼船后,便成了侯景的左臂右膀。侯景和他是典型的狼狈为奸的关系。王伟有两个过人之处:能写出最美的文章,也能想出最狠毒的计策来。
侯景每一篇文辞俱美的文章全为王伟捉刀,而每一次毒计也当然少不了王伟的出谋划策。
先说说王伟的才华。他捉刀替侯景回复高澄的文章,让高澄都连连惊叹,忙问是何人所作。当得知是王伟时,爱才心切的高澄便斥责左右失察:其高才如此,为何不早日知晓?情形与日后武则天欣赏骆宾王的檄文时几乎一致。
王伟的才华帮了他不少小忙。日后他深陷牢狱,却依然恃才傲物。当梁廷的一个官员唾沫连连地喷他:死虏,复能为恶乎?
他只轻轻回应一句:“君不读书,不足与语!”结果那人却羞愧而退——虽然那官员好歹也是尚书左丞。
更绝的还在后头。
他在临死之际,知晓梁元帝萧绎爱才,便想靠此活命。他在狱中挥毫泼墨,写了五百字的长诗献给萧绎,以求一命。结果如他所料,这诗打动了梁元帝!要知道萧绎的父兄蒙难,江南百年繁华毁于一旦,全拜侯景、王伟所赐。王伟的罪孽千刀万剐并不为过,可萧绎全然不顾,决定赦免他。表层的缘由似乎是王伟才华太出众了,但更深的原因是萧绎和王伟为一丘之貉——有才无品。
可王伟没有时来运转,他虽料对了开头,却料错了结局。
才华太出众的人,容易引起小人的忌恨;而品行过于恶劣的人,则容易引起公愤。而这两条王伟都占了。
一看萧绎松口,旁边便有人小声嘀咕:陛下,王伟还有更奇异的文句!
萧绎当然不肯放过,忙命取来。一只眼的萧绎看到了毕生难忘的文句: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萧绎曾为湘东王)
这都是老三篇了,是王伟当时替侯景征讨萧绎写的檄文。话的确尖酸了点:四颗眼珠子的项羽都自刎乌江,你独眼龙的萧绎会掀起什么风浪?
阿桂一听闻跟秃头有关的东西都会暴跳如雷,贵为天子的萧绎的反应可想而知。萧绎平生最憎恨别人取笑他的生理缺陷。他的原配,那位“徐娘虽老,犹尚多情”的徐昭佩,便是经常化半面妆会见自己的老公,以此嘲笑萧绎独眼。最后徐娘被杀,世子萧方等(徐娘所生)也无辜牵连,从未得宠。
老婆都要除掉,王伟的下场更惨。对萧绎而言,父兄之仇可以忍,但绝不能叫他绰号!
王伟死得很惨,那张惹祸的臭舌头被钉在柱子上,而坏肠子被活生生掏出来。可王伟还是颜色自若,最后被仇家凌迟割肉而死。
到头来,王伟还是死在了自己的才华上:当初不写出这种流传百世的文句来,这小命估计还能保得住的。
再说说王伟的狠毒。他投奔侯景后,侯景的每一条毒计都有他的份。让侯景造反的是他,让侯景千里奔袭建康的是他,让侯景诈和诱骗梁廷的还是他,如今让侯景翻脸攻城的依然是他。
后世每一个横征暴敛的贪官后面肯定都站着一个一肚子坏水的师爷,而王伟非常成功地扮演了这个“师爷”的角色。侯景之所以不算是这世上最狠毒的人,是因为他背后还有个唆使他的人——王伟。
王伟劝侯景背盟的话很简单:“背盟而捷,自古多矣!”——历史有很多成功的榜样,我们也跟着干吧!
他替侯景写给萧衍的信几乎让萧衍吐血——羞愤交加,毫无办法。他在信中将梁廷上下数落了一番,最要命的说了一句:臣至百日,谁肯勤王?
这话说到了萧衍心疼之处,他舍尽所有疼爱他的每一个子孙,可如今竟无人来救!城中死者已八九,登城之人已不足四千,横尸满路;而他的子孙却在对岸莺歌燕舞,纵酒为乐,置之不理。萧纶的属下极力劝诫萧纶:今日宜分军三道,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可萧纶不从。援军的主帅柳仲礼也只顾饮酒,他的父亲柳津在城楼声嘶力竭地喊叫,柳仲礼毫不在意。
还算有人想立功:南康王萧会理、羊鸦仁、赵伯超趁夜欲渡过秦淮河攻击侯景。可关键时刻又是赵伯超临阵脱逃——这是他第三次逃跑了,结果这五千援军的脑袋被贼军堆在了城下。
看援军毫无作用,侯景的动作更快了:百道攻城,昼夜不息!
危急时刻,又是萧家子弟对于手下的军士过于苛刻,招致守城将士愤恨不平,结果监守自盗,引狼入室。
里应外合下,苦撑百余日的台城终于破了。
解脱,所有人的解脱
城破了,对所有的人都是解脱。城内的皇帝、太子不用再苦熬下去,短痛比长痛肯定痛快,绝望比起若有实无的希望更让人容易解脱;夹在中间的侯景,终于不用做夹心饼干,可以耀武扬威地登上文德殿了;秦淮河南岸的援军也不用耗费时日花天酒地了,只要诏令一下,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撤军了。
解脱,真是彻底的解脱!
侯景玩起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破城后,他派遣石城公萧大器到秦淮河号令援军:各位散了吧!
这一招还是冒险。侯景虽天子在手,可是实力远不及援军。只要援军继续围城,鹿死谁手,依然未知。
所有的将领都聚到柳仲礼帐下,面临两个选择——去,还是留。可真正能作决定的只有两人:爵位最高的萧纶和主帅柳仲礼。还是萧纶机灵,众目睽睽下,一句官话便把皮球踢给了柳仲礼:“今日之命,委之将军!”
柳仲礼也是老狐狸,直接把萧纶当成了空气,盯了老半天,一言不发。
他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以前攻城是救主;而现在攻城是谋逆。一夜之间,竟会如此天翻地覆!而祸根却是自己所种。
萧纶不敢主动,是他原先劣迹斑斑,本就背负着篡位的嫌疑,如今一旦下令攻城,不是明摆着置皇帝、太子于死地吗?投鼠忌器,他不敢轻举妄动!
柳仲礼本就是来花天酒地的,他只是名义上的主帅,这支貌合神离的军队根本不在他的掌控中。而现在,何苦要担负这种灭族的危险呢?
大伙儿都盯着柳仲礼。裴之高、王僧辩更是着急万分:将军拥众百万,导致宫阙沦落,正应悉力决战,何所多言!
正是援军的拖延,致使台城沦陷,现在是他们将功补过唯一的机会了。
可是,曾经胆气冲天的柳仲礼,如同被雷劈了一样,木偶人似的静止着,还是一言不发。
群龙无首,在重重叹息、捶胸顿足中,援军解散了。“十四万人齐解甲,其中无一是男儿”的一幕上演了:萧家子弟全部跑回本镇,而柳仲礼竟领着柳敬礼、羊鸦仁等将向侯景开营投降——名义上当然还是归属萧衍。
建康的沦陷,总让我想起开封的沦陷,同样让人扼腕。可那纯粹是积弱积贫的宋王朝打不过野蛮的游牧民族,真正的军事实力不济,我们服!但,建康的沦陷,梁王朝的败亡,完全是自掘坟墓。梁王朝有太多拯救自己的机会,却一次次主动葬送。比起靖康耻来,梁王朝的沦落更让人悲愤无语:明明还能续写繁华景象,却要建成千里坟墓。
这胜利与其说是侯景争来的,倒不如说是援军赠送的。
台城虽然破了,可侯景发现还有一座城横在他的心上:他竟然不敢面对萧衍,那个被他玩弄了无数次的老头,那个本应该匍匐在他脚下的人。
可他们还是会面了。萧衍依然高高在上,侯景在下缩成一团。后面有五百甲士给他壮胆——见一个临死之人的人还需这种排场,明显地心虚。
萧衍神色不变,很冠冕堂皇地慰劳他:“卿在军中日久,辛苦了吧?”
侯景一言不发,汗流浃背。
萧衍几乎变成质问了:“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儿犹在北地吗?”
侯景彻底晕了——与尔朱荣当时杀尽百官后如出一辙,只得由旁边的任约代答。
萧衍只得没话找话了,问:“初渡江有几人?”
这数字,侯景清楚,回答得干脆:“千人!”
“围台城几人!”
“十万。”底气足了。
“今有几人?”再问就危险了,可萧衍也停不住了。
“率土之内,莫非己有!”侯景的声音突然异常洪亮。他这时恍然大悟:天下都匍匐在自己脚下,自己已是这天下的主。
这时变成萧衍低头不语了——天下都是侯景了,自己还有什么脸高昂着头?男人的底气全来自实力。
退出大殿的侯景,依然汗流浃背,这时他似乎明白了一些。他不无惶恐地对自己的手下说:“我常骑马对敌,矢刃交下,毫无惧意。今见萧公,使人自惧。岂非天威难犯?”
万颗人头落地,侯景可以谈笑风生,可行将就木的萧衍却让他冷汗不断,萧衍的皇家气度可见一斑。仗可以打得随心所欲,可萧衍不能再见了。侯景下定决心,郑重其事地对手下说:“吾不可以再见之。”
在太子萧纲那里,相同的一幕又上演了。作为胜利者的侯景,面对自己的战利品,又是以礼拜见,依然窘迫得哑口无言。
侯景彻底地蒙了:明明是自己赢了,为什么自己的腰杆还是得弯下来?
而萧正徳可管不了这么多,这个内贼竟然天真地认为自己可以名正言顺地当上皇帝了。为了皇位,萧正徳付出的的确够多了:家产充了军资,女儿嫁了侯景,儿子死在了乱军中。现在是他加倍偿还自己的时候。
萧正徳正要挥刀杀入宫中,结果萧衍父子。可到宫门口,却被侯景的士兵拦住了。按照他们的约定,城破之日,便是皇帝、太子人头落地之时。可侯景怎么反悔了?当萧正徳还在云里雾里时,让他更懊丧的事又来了:他被侯景降成了侍中、大司马,而破城前,他至少还是名义上的皇帝。
萧正徳这时才恍然大悟自己被侯景耍弄了。儿子没了,女儿赔了,财产充公了,现在连皇位也鸡飞蛋打了,萧正德感到了莫大的委屈。他需要疗伤,要找个最疼爱他的人诉说他内心的痛苦和哀伤。他找到了最合适的哭诉对象——萧衍,那个他刚刚想举刀砍死的人。
就像他上回叛逃北魏又逃回一样,他渴望在叔叔,也是他最早称之为父亲的那个人那里得到原谅、安慰。
我实在想不出这世上是否还有比这更厚颜无耻的事,可是让我真正惊叹的却在后头。
面对这个几乎毁了社稷江山的侄儿,萧衍没有破口大骂,没有大发雷霆,没有捶胸顿足,只是引经据典地安慰了一句:“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孩子,别哭了,再伤心欲绝,也已木已成舟了。
或许,在这一句话里,他还藏着无尽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