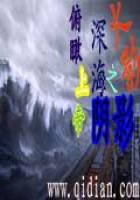而萧绎的处境也是如此:西魏、北齐的确可恶,可憎可恨,也暂时夺不去他要的江山;可兄弟侄子就不同了,因为他们也同样拥有继承这江山的权利,所以他们的威胁更大。退一万步讲,即便当了亡国奴,自己或许还能封个“违命侯”;可落在家人手里,那必定是尸骨无存了。
那么现在活着只有一种原则:以前的敌人现在都是要拉拢的朋友,而兄弟子侄都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趁着侯景之乱、萧家叔侄自相残杀,东魏(北齐)、西魏都占了渔翁之利。北齐占了淮南的大片土地,直至威逼建康;而西魏也毫不示弱,依靠萧詧内附,占了汉东之地,窥视江陵。
一直依靠江淮之地作为缓冲的梁朝,如今只剩了长江天险。没有江淮之地的缓冲,天险如同平地。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和祸首侯景的决战开始了,这时离台城破城已有两年的时光,萧绎真有耐心。本来,他还能等得更久些,不过这次是侯景主动挑衅,几乎倾城而来。
和侯景的决战
侯景这两年也忙着杀人,顺带清理建康附近的梁朝残余势力。他征服的手法依然单一―-以杀立威。比如在攻破广陵(扬州)时,便是城中无少长全部活埋,再来回驰射灭绝。自孙权以来历代君王苦心经营的三吴之地,生灵涂炭,数百年的繁华景象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而现在,他和萧绎两人间的恩怨也该清算了。
这两年,侯景一直打得顺风顺水,吴人的不堪一击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面对萧绎,他自觉有很大的胜算。可他忘了一点,怯懦和软弱也是会传染的,在三吴之地这块温柔乡里,他手下的战斗力其实也是江河日下,不可同往日相比,两年前那种博命式的疯狂早已消退。
侯景选择了快攻,轻而易举将长江上的重镇郢州(今武汉)拿下。当敌兵冲进房间时,郢州刺史萧方诸(萧绎宠爱的儿子,年方十五)正骑在监州鲍泉的肚子上玩过家家的游戏。无人抵挡,敌兵们唯一受到的惊吓是:鲍泉的胡须被萧公子用五彩斑斓的绳线扎成了怪异的造型,这让他们吓得不轻。
侯景的下一站便是巴陵(今湖北岳阳),离江陵只有一地之隔。一旦灭了萧绎,凯旋之日便是侯景登基之时。巴陵城规模不大,缩头缩脑地伏在长江边,看来指日可下。镇守巴陵的是王僧辩,曾经向自己投降过的将领。侯景真没料到会在南方碰到这么多北方来的老乡。
其实,侯景还有更好的选择,先留着巴陵,直攻江陵,萧绎则立刻完蛋。这是萧绎的一个赌局,他几乎把身家性命都押在了巴陵:王僧辩、王琳、徐文盛几位名将,还有大部分的兵力,都偷偷聚在了巴陵小城。
巴陵,小城池,根本不在侯景的眼里。过多过快的胜利已让他失去了理智的判断。现在他要席卷一切,不留一切障碍。侯景起脚,准备一脚踢开这块绊脚石。可他料不到,这块小石头不仅让他摔得鼻青脸肿,还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败亡之路自此开始。
攻城战开始了。他披甲立在城下,亲自督战,百道攻城。而王僧辩站在城上,四处打气。两个北方来客,指挥着一大群南方士兵,打得你死我活。一向轻易得手的侯景遭遇了劲敌,直至粮食吃光。接踵而来的却是疾疫,更是死伤大半。
而他的手下大将任约率领的另一支军队,被胡僧祐打得落花流水。再也撑不下去了,侯景第一次感到了恐慌,率领数千人逃回了建康,剩下宋子仙和两万人马防守郢州。不过,无济于事,时隔不久,宋子仙也被擒杀。
返回建康的侯景更加郁郁不乐,已有末日来临的恐惧。他手下的猛将基本死光,地盘也一点一点被萧绎蚕食,一向懦弱的南方军队竟如此顽强。侯景自觉时日无多,索性及时行乐,过把瘾就死。他已经前无古人地自封过“宇宙大将军”了,如今唯一能让他感到新鲜的也只有皇帝这个职业了。
很快,萧纲(史称梁简文帝)被废;时隔不久,他酒醉后被土囊压死。而他的儿子们也尽数被杀——侯景真是厚道,临死前还要帮湘东王萧绎的忙。而前太子萧统的孙子萧栋当时正忙着生产自救——种菜求食,一下子被拽去当了皇帝。不过好景不长,侯景又玩起禅让游戏,自己来当皇帝了。
皇帝的禅让,说容易,也容易,只要拳头硬就行;说难,也难,毕竟是个文绉绉的技术活,而侯景这粗人对文士的这些把戏一窍不通。
不过,有王伟在,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唯有这时,王伟才最真切地了解自己跟的老板有多土,自己混的兄弟有多掉渣。虽然禅让的把戏在尧舜禹时代就已上演,可这一回可能是最混乱的一次。禅让虽是假惺惺的,但总得庄严、肃穆;可侯景完全不需要这感觉,他的登基更像是黑社会老大上位。底下的徒众有数万之多,全挤在太极殿上看热闹,欢呼雀跃地一拥而上,庄严的登基大典沦为鬼哭狼嚎的场面。
唯有王伟脑子还清醒,要请立这位新皇帝的七庙。侯景对这些繁文缛节丝毫不通,非常谦逊地问道:“何谓七庙?”
王伟答道:“天子祭七世祖考!”——天子用来祭祀八辈祖宗的地方。
答后,王伟便向侯景要祖宗七代的名讳,说到时要给他们供奉点猪头肉之类的东西——免得叫错了名字,让哪个路过的孤魂野鬼白吃一顿,占了便宜。
对侯景来说,记人明显比杀人难。这七个名字让侯景很为难,他抓耳挠腮半天,总算挤出一个:“更早的我再也记不起了。唯一记得我父亲叫侯摽!”不过,这位新皇帝马上表示了他的担忧,“不过阿爷的鬼魂远在朔州,怎会千里迢迢跑到这里啃猪蹄?”
底下哄堂大笑。
这侯景比日后的朱重八还惨,人家朱和尚好歹还知道父亲叫朱五四,爷爷叫朱初一,比侯景多了一代。幸亏,侯景的手下还隐约记得他爷爷叫“乙羽周”。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其余的都由王伟胡编乱造,一并凑齐了。
可没当几天皇帝,侯景便不开心了。他几乎被王伟囚禁了起来:他不能随心所欲地打猎,他不能轻易外出,他和昔日的手下也隔膜了起来,不能一起饮酒作乐——因为王伟告诉他:你是皇帝,你得有分寸,你得注意你的安全。
加上外面噩耗频传,更让他坐立不安,他还是很怀念做宇宙大将军的逍遥日子。而一切都已不可挽回了。他常常自责:“我无事为帝,现在倒什么事都干不了。”
可王僧辩还是不请自来了,这中间还夹杂着从广州远道而来的陈霸先将军。这将军自己白手起家,无依无靠,便一心投靠了萧绎,手下有精兵三万人。转眼,芜湖又被王僧辩一举拿下,萧绎的军队离建康也只有数地之遥了。一切的戏都在重演,只是侯景成了萧衍,王僧辩成了侯景。
侯景慌了,不过他很清醒地记得自己还是皇帝,不管方式如何粗暴,总是从萧家人身上禅让过来的。慌乱之中,他做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事:下诏赦免王僧辩、萧绎的罪过。他总是这样富有创意,事不惊人死不休。这世上,哪还有做贼的,敢光天化日地喊着不追究被偷人家的罪过?
可王僧辩不领情,拒绝了他的好意,继续进军。侯景只剩下姑孰重镇可作抵抗。
至此,侯景已是心惊肉跳。
替他防守姑孰的是侯子鉴,这是侯景最后的希望。光是陆上交战,侯景的军队还是略有优势。侯景只交代了一句话:不许水战!任约的两万精甲便是死在胡僧祐的一千羸兵手里,战败的唯一缘由:那战斗发生在水里!骑惯马的叛兵在水里却只能任由南兵折腾。
侯景的担心果然兑现了,没几日,侯子鉴几乎单枪匹马地逃回来了。这位小侯经不起王僧辩的诱惑,奋勇参加了江上大战,结果吃了大亏。
杀人如麻的侯景害怕极了。他如同失宠的妇人一般,泪下如雨,蜷缩在被窝里,许久方起,连连叹息:误杀乃公!——这下把你爷爷害惨了。这时,他终于品尝到了萧衍当年被围的感觉。
可他比萧衍还要惨,起码萧老爷子还能硬挺着八十多高龄的身板,等着满堂儿孙前来勤王。侯景能指望谁呢?老东家高家吗?侯景早已和他们决裂了。当年侯景低三下四地哀求高澄放过他家妻儿时,得到的结果是:高澄把他妻子、儿子的面皮全部活剥,犹不解恨,又放到油锅里烹炸。
只能靠自己了!侯景从溧阳公主(萧纲女,嫁给了侯景)的温柔乡里挣扎出来,亲自在秦淮河岸排兵布阵,十里之中,步步设岗。秦淮河,已是他最后的防线了。两年前,数十万援军就在这里止步不前!他盼望着历史能再次重演。
可让他失落的是,敌阵中的陈霸先却一路当先,奋勇冲过秦淮河立下营寨,其余的部队也步步为营,接连驻扎过来。秦淮河这块屏障被轻易撕破了。无机可乘,侯景只能眼睁睁看着所有的梁军渡过河来。
再等等,总会有机会的。
侯景聚集了八百铁骑、万余人马准备突袭,因为梁朝的军队经常是被一击即溃,一哄而散的。只要他们军队里有赵伯超这样的逃跑将军,先行逃跑,继而形成大崩溃,还是有赢的希望。
可陈霸先又坏了他的好事。一看侯景的阵势,陈霸先便建议部队分处设兵,免得让侯景一下冲垮。侯景无奈,只能采取部分冲击的计策,先行攻击王僧志的军阵,颇有成果。可紧要关头,后面突然万箭齐发——梁军竟有两千弓弩手向侯景的军队射箭。
又是陈霸先的安排!侯景至死也不明白这位南朝将领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当时援军根本没他的人影。
要不想成为刺猬,只能后退,这是唯一的选择。这一退,陈霸先的骑兵却不善罢甘休,突然袭来,侯景只能缩到营寨里去。转眼,更大的噩耗传来:石头城的守将向王僧辩投降了。侯景只剩了自己临时搭建的营寨。
侯景非常疑惑:两年前,梁军只要看到自己军队的青袍,闻到自己的气息,便会不寒而栗,一击便溃;可如今,还是一样的军队,他们却如此顽强,自己的军队却沾染了他们先前的毛病,完全没有那种势如破竹的感觉。
缘由何在?人心而已。两年前,侯景的军队是冒死前来,攻不下台城,便是死,自然要死拼;而梁朝援军,却貌合神离、无心恋战,形同一盘散沙。两年过去了,侯景的军队早已气衰力竭,又接连败仗,毫无战心;而王僧辩的队伍却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因为他们只有一个主人——萧绎。
虽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侯景还是要死撑,起码要灭掉陈霸先。这是侯景的脾气:有仇必报。当年,他逃命之时,路过一小城,突然听闻城上有人骂他:“跛脚奴何为也!”
继续逃命,还是先报睚眦之仇?总得先掂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