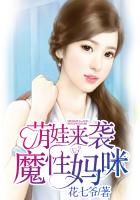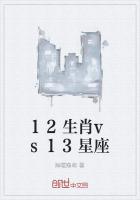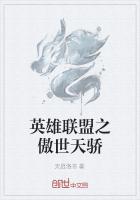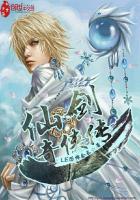而相比而言,留在江陵却有太多的理由。起码,萧绎的大部分手下都不愿去建康。萧绎的诏令受到了阻挠,大臣们的理由很简单:建康王气已尽,与北齐只有一江之隔,危机四伏。
这理由虽冠冕堂皇,可全出自私心。萧绎的属下多为江陵士族,他们哪舍得扔弃在江陵多年置办、搜刮的家业。三年前,建康是天堂,可如今是坟场。天子都要白手起家,自己当臣子的还不得要累死累活?
即便掘地三尺,也搜刮不了东西呀!千里无人烟,去搜刮谁?除了死人,没人可以用来盘剥。不过,既然在朝堂上,理由总得高尚一些:我们是怕北齐入侵,是为陛下您的个人安危担忧。
在这一片异口同声反对迁都的吵闹声中,还有几个人清醒。王谢家族的代言人——尚书右仆射王褒,说:“愿陛下从四海之望,早日入驻建康!”
结果,这话马上被淹没在一片唾沫声,群臣皆义愤填膺,纷纷痛斥:“周宏正、王褒等人为东人,一心东去,恐非良计!”
此言一出,东人又是反唇相讥,结果吵成一团。西人愿留,东人执意要迁,一时争论不下。萧绎也无所适从,只好微笑着宣布散会。
时隔不久,萧绎又再次召开群臣扩大会议——为表示民主,共聚了五百人,商议迁移事宜。为避免造成上次的争吵,萧绎耍了心眼,他一开场便立即表态:吾欲还建康,诸卿以为如何?
底下鸦雀无声,皇帝都表态了,还有谁愿意触怒龙颜啊?可萧绎还是很民主,便说:劝我去建康的,请撩起左手的衣服。
结果齐刷刷,过半之人,都露了左边胳膊:迁移的民主测评通过了。
那么早日上路吧——高欢从洛阳迁都邺城可是当日上路的。不过,我们得明白,自古到今,民主通过的东西多是不算数的——只有“明主”通过了,才能生效。
关键时刻,又有了阻碍。这回是“明主”——萧绎自己动摇了。萧绎杀人时从不犹豫,那是因为作决定的是心肠;可在危急关头,他却是拖泥带水,因为作决定的是脑子。他能说服他的臣下,却不能说服自己。
杜景豪,先给朕算一卦吧!对曰:不吉。
既然老天都认为不吉利,我何苦去趟建康这混水呢?那就留在江陵吧,这里毕竟没有战乱的干扰,依然繁花似锦。何况北齐、西魏都是虎狼,到哪里都一样。
其实,萧绎不知道,那位叫杜景豪的术士在启禀之后,回到角落里蹦出的第一句粗话却是:今天真是他妈见鬼了,竟会抛出这样的卦来!
公元553年就这样过去了,一切都相安无事。这一年,王僧辩驻扎在姑孰,陈霸先驻扎在京口,离江陵都是千里之外。而焚烧过王宫的王琳,则被安置得更为遥远——这位对萧绎忠心耿耿的将领被发配到了广州当刺史。萧绎怀疑他的忠诚,担心这位家奴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威胁,再次自断臂膀。
梁末的三大杰出将领,都和萧绎至少远隔千里之外。萧绎的坟墓又被自己挖得更深了点。
坟墓已经够深了,不过还不够大,还装不下萧绎肥胖的躯体。起码,还得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帮忙。或许你已猜到了:宇文泰。
西魏的狼子野心
在这三国鼎立的世界里,西魏本是最弱的一极,只有被动防守、伺机而动的份。可梁朝的侯景之乱、同室操戈,却让西魏渔翁得利,得了天大的好处,几乎一夜暴富起来。蜀地已在掌控,内有萧詧接应,江陵完全暴露在宇文泰的刀口之下。吞并江陵,对宇文泰而言,只是时间问题——这得取决于萧绎的友好态度。
事实上,萧绎是一直有求于西魏的,每次危难之时,他总是向宇文泰哭爹喊娘的。侯景来了,为了求援,他许诺将南郑之地割让给西魏;萧纪来了,为了解围,他竟请求宇文泰直接出兵蜀地。在这场血斗中,萧绎一直小心伺候着西魏大爷。可如今,异己全灭,萧绎的腰板也硬了起来。他不再低声下气,他目空一切,而这自大却是在对西魏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很凑巧的是,北齐和西魏的来使一起来了江陵。在接待上,他对北齐的礼数超过了西魏,让西魏来使很下不了台。可外交无小事,吃了亏的西魏使者立即向宇文泰禀报,诉说萧绎的不公。
而火上浇油的是,这时的萧绎竟然心疼起先前割让的土地来。羽翼未丰的他跟宇文泰讨价还价,而且态度很不恭敬。宇文泰终于爆发了,决定攻占江陵,收拾萧绎。
从深处来看,这只是诱因而已,向梁朝发展是西魏崛起,打败北齐唯一的道路。可萧绎再装几年孙子,宇文泰出手不会如此之快,历史或许是另一番景象。
此时的北齐已非常强大,西魏对他们的挑衅置之不理,立即向南出兵。五万兵马虽不多,不过都是能征善战之徒,而领军的是身经百战的于谨。无兵无将的江陵危在旦夕。
萧绎得到了战报,立即召集群臣商议。
一位曾出使西魏的官员信誓旦旦地说:我以前观察过宇文泰的脸色,肯定没这回事!这近似看相算命的话竟然被当成了佐证。大伙集体商议的结果是:两国通好,正如胶似漆呢!
君臣昏庸与建康侯景之乱时,如出一辙。
既然大伙都说没事,萧绎便继续在大殿上给群臣讲述《老子》的微言大义。这《老子》的讲座他已断断续续讲了几十天,为了这假消息中断了心里怪难受的——谁叫他是读书人呢!风雨江山,飘摇不定,一朝上下,依然醉心于这虚无缥缈的学问追求,想不亡都难!
转而,更坏的消息传来,言辞确凿:西魏与叛徒萧詧合军了,离江陵只有百里之遥。
这终于让萧绎紧张了,只得下诏内外戒严,并暂时舍弃心爱的讲座,到城外巡视防守工事。注意,是暂时!
随之,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发生了。派出去观察敌情的官员又传来了好消息:“境上安然无恙,前言皆儿戏也!”
原来虚惊一场啊!对这个近于掩耳盗铃的消息,萧绎也是半信半疑。不过,时不我待,还是继续大搞特搞文化活动吧——老子的《老子》还没讲完呢,各位臣工继续听讲。
讲座继续,西魏的马蹄声已在边境响起!生死存亡之际,梁朝君臣都穿着军服,站在朝堂上,继续听讲萧绎最后的一课“道德经”。比起这种舍生忘死的最后一课,法国人都德宣扬的境界算个屁!
西魏的军队势如破竹,旋即攻到江陵城下。统帅于谨老谋深算,立即断掉了萧绎东逃之路。刚出征的时候,于谨便已算过了萧绎所有的应对措施,且料定萧绎会采取最差的一种——死守江陵。
他知己知彼,对萧绎的评价也非常吻合:懦而无谋!而自以为是的萧绎的确是这样一个人。
在迟缓和无知中,萧绎已经失去了所有主动的机会,如今除了死守待援之外,他已别无选择。可这时,谁会来救他呢?或许从那一刻起,他明白自己走上的竟然是和父亲同样的路。他在城上哀叹,他的嫔妃开始哭泣,整个江陵陷入了和建康之围一样的惶恐之中。
他想起了王僧辩,想起了王琳,这两位千里之外的亲信大将。此时已鞭长莫及,可他依然还心存幻想。他征诏远在千山万水外的王琳为湘东刺史,让其入援,可身在岭南的王琳舍了命也只能赶到长沙;他急征建康的王僧辩为荆州刺史,可已为时已晚。
为了生存,萧绎异常顽强,他给王僧辩写出这样的信: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大哥,来吧,来救我吧,我会一直等待你来。
远水救不了近火,一切努力都是枉然。萧绎在江陵城上,看见西魏军队潮水一般拥过长江,除了四顾叹息,他已无任何举动。时隔不久,于谨在外筑起了长围,江陵与外界完全隔绝了。
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建康之围的悲惨一幕竟然在六年后,又如出一辙地在江陵上演了。只是,主角不再是萧衍,而是换成了他的胖儿子萧绎。太快了,快得让我们目不暇接。
没有梁军的援兵来救,西魏的进攻非常得心应手。数日之后,江陵外城在顽抗后终于陷落。在如狼似虎的西魏军队前,梁军所有的袭击都毫无效果。萧绎只得退入子城保命。他已经完全绝望了。
萧绎曾是自负到天上的人——我藏的书汗牛充栋,我的知识学富五车,我南征北伐,我消灭了所有的异己。可今天,我为何走到了穷途末路?到底,是谁的错?他在大殿中暴躁异常,寻求让他毁灭的答案!
他找不到多好啊!可是他找到了,而且偏执得认为一定是它造成的:他所藏的万卷图书,他花了一辈子心血收集的书籍。他本是多么迷恋这些四处收罗来的奇珍异本。因为,这种感觉太好了。这普天之下,只有他才拥有。
既然,今天我注定毁灭,那么也让这些书陪我而去吧!这数万卷藏书,都是属于我一人的,和天下苍生无关,和千秋万代无关。历代难得善终的帝王,让珠宝,让美人,让宠妾,让图画陪葬的,数不胜数。可拉这么多书一起陪葬的却仅有萧绎一人!因为只有他拥有这么多书,因为只有他懂得这些书的价值。
舍人高善宝在萧绎的嘱咐下,点起了火,十四万卷书,熊熊燃烧。十四万卷书,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要知道围城的西魏,全国上下加起来的藏书只有八千卷。即便,它后来统一了北齐,也只有一万五千册。那么,可以说,当时天下几乎所有的图书都藏在南方,都集中在萧绎手里(大半都是从建康运到江陵来的)。搜集这些书很不容易,也几乎花去了萧氏父子两代人毕生的心血。
由于是皇家藏书,多数还是孤本,从此便永远消失。至此,南方的古籍基本消亡殆尽。到隋朝时,文治武功虽强,可皇室藏书才勉强恢复到三万卷。到了唐朝,所能搜集的也就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虽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可再也达不到江陵藏书的规模了。
这一把火,是秦始皇焚书以来,对书籍伤害最深的一次,空前的浩劫!对书伤害最深的人,竟是对书感情最深的。而事后,萧绎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读万卷书,犹有今日,故焚之。
萧绎,本也要觅死觅活地跳进火坑,和书一同火葬的,却被左右拉住了。在火光照映之下,他又重重地将宝剑砍在柱子上,立时折断。他发出一声长叹:
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这一声叹息,和他父亲的“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竟是一样的酸楚。
从萧绎这里我们起码懂得这一点:读书和做人是两回事,不懂得做人,无论读多少书,你永远都是白痴。
不过,我们别小看萧绎的魄力。岂止是书,他连人都要一起陪葬:我一个人死太寂寞了,在地下,我依然还要做你们的王!江陵城里的数千囚徒,为此差点成了他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