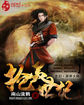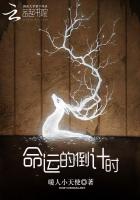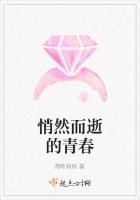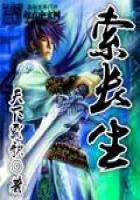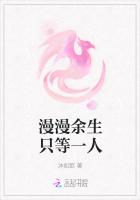编者同时指出,对左翼文学的研究,“我们是有许多经验教训的”,“除将其‘妖魔化’以外,也曾有过‘独尊左翼’的时代,今天我们重提左翼文学的话题,自然不是又要来‘翻烙饼’。一位作者说得好:关键是要改变那种‘整体主义的肯定或否定’的简单模式,用一种比较复杂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研究对象,尽可能地揭示其矛盾的各个侧面”。《丛刊》发表的两篇有关延安作家(广义上的左翼作家)的论文《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杨联芬,1998年第4期)、《为农民的写作与农民的拒绝———赵树理模式的当代境遇》(范家进,2002年第1期),即被评论者认为是“显示了新一代研究者在处理复杂的研究对象,追寻与揭示作家创作与所处时代政治、文化……体制与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潜力”。
危机感与学科检讨中的分歧
当然,新世纪研究的内外环境都并不平静。2002年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八届年会上,就有不少学者谈到了“学术环境正日趋恶化”:“学术的体制在此之前,2000年所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的学术讨论议题之一即是“左联和左翼文学”研究。参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纪要》(秦弓,《丛刊》2000年第4期)。
《编后记》,《丛刊》2002年第1期。
参见钱理群:《关于新一代的研究者的观察与思考》,《丛刊》2004年第1期。
化、商业化,权力与利益对学术的渗透,学术的腐败,表面繁荣下的学术泡沫化,这些都会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无聊感与荒谬感:我们的学术还有意义与价值吗?”于是就有了“一方面是学术的腐败,另一面却是庄严的学术坚守”的概括,以及“抵制权势的压迫与诱惑,商业与时尚的诱惑,坚守学术的独立性与科学性”,发扬“持重”的会风、学风,同时加强学术研究的“创造性与批判性”,“与当代中国社会保持对话关系”的呼吁。2001年上海大学与2004年汕头大学主持召开的两个学术讨论会都以“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为题,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如论者所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的命题,它仿佛已经变成或即将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打开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因而为思想与学术的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同时又产生了日趋严重的生存的困惑,思想的困惑,以及学术的困惑。有的学者认为,“社会生活在日趋复杂化,新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层出不穷,而我们的知识生产却明显滞后”,我们已经“无法把握急剧变化中的社会”,“今天的文学研究已经没有能力来解释周围的世界”。由此产生的是知识分子自身及其学术研究的危机感,对现有研究格局的再检讨,以及挣扎的努力与“突围而出”的新的追求与设想,如主张交叉学科的介入与“文化研究”的倡导等。同时存在的是另一种危机感与学科检讨:“全球化尚颇遥远,就算真的‘来了’,也还不必首先由文学来与之对话。”他们这样提出问题:“文学创作和研究能否不必肩负对时代新变作出及时‘反应’的任务?能否不必汲汲于追求对时代‘有用’,作家或学者能否‘只拉车不看路’,即能否在任何‘宏大叙事’消失的时候,在‘大方向’一片模糊的时候,进行各自的创作与研究?作家的创作与学者的研究,是否都应该指向某个‘宏大叙事’或某个人人必须关心的‘大方向’?”因而发出了使现代文学脱离“反应论”与“有用论”的“掌控”,“获得自由与自觉”的呼吁。论者并不笼统地反对文学对时代的反应,而是强调“文学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八届年会闭幕词》(钱理群),参看《新世纪“学术坚守”的象征———中国现代文学第八届年会综述》(岳凯华),《丛刊》2003年第2期。
参看《全球化状态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体的建构》(袁盛勇)、《作为视野和方法的文化研究》(倪伟),《丛刊》2002年第3期。
应时代的基础与目的,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内心的内容及内心的变化”,因而认为“继续深入研究现代作家内心‘反应’时代的方式,包括深入研究‘反应’时代的出发点与归宿,即他们各自内心的实际内容,以及无论怎样的‘现代心灵’被确立的方式、根据与极限,在今天仍然值得反复强调。取消了对这一核心问题的研究,所谓‘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将没有落脚之地”。还有些学者却感到了学术“知识化”的危机:“文学所固有的智慧、感性、经验、审美、想象力、生命理想、生存世界……这些都没有了,都在知识体系和学院化制度中丢失了”,因而发出了“重建文学性”的呼吁。———看来1990年代中后期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论争到新世纪仍在继续,但显然已有了新的社会、思想文化与学术的背景,因而具有某些新的内容与意义。
100期纪念
《丛刊》到2004年第3期,是总100期。在这一期里,引人注目地推出了“现代文学的文献学问题座谈会专辑”,把“重建现代文学的文献学”作为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来:这就构成了对80年代初期与中期王瑶等老一代学者关于“建立现代史料学”的呼吁的一个呼应。就《丛刊》自身而言,它的总100期就与发表王瑶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与马良春的《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学”的建议》的总5期(1981年第4期)、总22期(1985年第1期)也形成一种呼应:这本身即意味深长。这既是回到学科发展的“原点”,又有新的发展,并带有明显的时代新特点。如论者所说,问题的重新提出,是具有多方面的意义的:既是“着眼于学科的基础建设”,也是“针对学术商业化所带来的学风的危机的一种抵抗与坚守,(因而)强调学术研究的科学性,重新提倡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的鲁迅学术传统”,“同时也包含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即把现代文学的文本还原到历史中,还原到书写、发表、结集、出版、典藏、整理的不断变动的过程中,去把握文学生产与流通的历史性与其时代政治、郜元宝:《“价值”的大小与“白心”的有无———也谈现代文学研究新空间的开创》,《丛刊》2004年第1期。
吴晓东:《重建反思性的学术立场》,《丛刊》2004年第1期。
思想、文化的复杂关系”。———这样,《丛刊》在走完了自己的100期的历程时,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2004年5月5—12日,6月9—24日参见钱理群:《关于史料的“独立准备”》,《丛刊》2004年第3期。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答来访者问一、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以下简称“杨”):我们还是从80年代谈起吧,一般来说,每个时代都有它主导的问题意识,您觉得80年代的问题意识是什么?
钱理群(以下简称“钱”):目前大家对于80年代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把80年代过于理想化了,好像80年代是一个完全自由的时代。这种看法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却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80年代相对于“文革”来说是一种解放,但实际上一直有不断的“敲打”,比如清污、反自由化等等,对思想的控制始终是有的。当时最大的潮流就是“思想解放”,但“思想解放”并不仅仅是对“文革”而言的,也是对当时的现实禁锢而言的,所以80年代一直有一个“挣脱历史与现实束缚”的冲动,这是我们在考察80年代时不可忽视的思想和心理背景。
杨:所以当时你们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些社会环境和学科环境。
钱:对,实际上是涉及到几个背景的,首先是1983年有一场论争,当时南京188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大学教授许志英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在当时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说得很明确,“五四”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但许志英在文章中认为是“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就动摇了这个毛泽东的结论。其实当时有相当一批人在思考这个问题,许志英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而且他写出文章来了。记得1978年我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时候,就有一个题目:“谈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
杨:那这个题目是谁出的?王瑶先生吗?
钱:我估计是严家炎老师出的。这是一个一直有争论的问题,李何林在30年代的一场论争中就明确表示“五四”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
杨:但是李何林后来改变了他的观点。
钱:30年代瞿秋白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所以他说“左翼文学”是对“五四文学”的反动,因为“左翼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个观点在三四十年代的学界,在毛泽东的理论出现之前几乎是公认的,只不过立场不一样,有人认为资产阶级领导是好的,有人认为是不好的。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后来李何林到了解放区之后就面临这个问题,当时他就非常困惑,究竟是谁领导的呢?他经过思考后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所以“五四文学”领导权问题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当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1978年我们入学的那道试题我估计是严家炎老师想看看我们学生的看法,实质上大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毛泽东特殊的权威性,在80年代以前大家是不可能质疑他的观点的,“文革”结束后,才有可能提出这个问题。许志英的文章代表了当时比较敏感的学者的看法,文章发表以后,实际上得到了学术界很多人的赞同,但是后来在“清污”中好像是胡乔木对这篇文章表示了不满,于是遭到批评,就弄得学术界很紧张,于是组织严家炎、樊骏等人发表文章,对许志英的文章进行批评。上面要求是批判,但是这两个人的文章都写得我们所走过的道路189很严谨,很缓和,尽可能采取学术争鸣的态度而不是政治批判的态度。这件事情当时我们都知道,私下里都在讨论,我们是赞同许志英的观点的,但都觉得许老师太老实,不应该这么直接去碰,所以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采取了另一种策略:把时间从“五四”提前,这样就把这个问题消解了。
杨:也就是通过时间的提前把领导权问题消解掉了。
钱:对,为什么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动因就是一方面要回避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提出不同的看法。当时许志英的文章及其争论提醒了我们:现代文学这门学科还是在“党史”的笼罩之下。所以我们现在要突破它,就是要摆脱现代文学史作为党史的一部分的属性,摆脱政治对它的控制,但是直接提到“五四”又为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不允许,所以干脆把时间往前提,使这个学科能够从革命史的附属中解脱出来。
还有一个是学科研究的背景,当时很多的年轻学者都有两个想法,一个是走向世界,另一个就是打通近、现、当代。具体到我们三人,恰好具备这个条件,陈平原当时偏向于研究近代,黄子平是研究当代,我主要研究现代。当时我们是很自觉地在这么想,这么去努力。这些想法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里面都有所反映,比如1985年第1期王富仁的文章《在广泛的世界文学的联系中开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道路》,它代表了走向世界的方向,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举动,现在大家可能都不记得了,就是出了一本书:《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作家》,这本书的特点就是旗帜鲜明地强调走向世界。
杨:你们都参与这本书了吗?
钱:都参与了,都有文章,这本书是我们这批“文革”后的现代文学的年轻研究者第一次集体亮相。
杨:后来你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面有走向世界的提法,就是受到这个的影响吧?
钱: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也很有趣。当时《丛刊》的编辑和现在一样,也是有执行编委,那个时候的执行编委都是我们的老师,这一期正好是乐黛云老师负责,当时她是我们的副导师,她选我做她的助手,她比较放心我,实际上就是让我来编,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利用这个权力,集体策划了这一期。我们可以看看这一期的目录,首先是论坛:“现代文学史研究要破关而出”,发表了张中(我们北大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同学)的《近、现、当代文学史的合理分工和一体化研究》。另外特意办了两个专栏,一是“近、现、当代文学汇通”,发表了黄子平的《同是天渊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另外一个专栏就是“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下研究现代文学”,选的是陈平原(《林语堂与东西方文化》)等人的文章,还有“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专栏,选的是温儒敏翻译的文章。其实这一期才是我们三人的最早合作。
杨:这一期应该是1985年7月出来的,和你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间比较接近。
钱:差不多前后。黄子平的文章《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把古代、现代、当代联系在一起,当时影响非常之大。你看还有陈平原和夏晓虹的文章(《五四白话文学的历史渊源》),当时他们正在谈恋爱,我还开玩笑,说这一期正好当作送给你们的爱情礼物。
杨:我记得在你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前,在1982年、1983年左右,就有人提出“百年文学史”的说法,比如陈学超的《关于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我记得是发表在《丛刊》1983年第3期。那“百年文学史”的提法和你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有何不同?当时为什么没有使用“百年文学”这样一个概念,而是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是不是要强调一种当代意识?
钱:当时我们考虑到,陈学超的那个提法是从鸦片战争说来的,我们觉得他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的。
杨:是从近代史的角度来谈的。
钱:对,我们主要强调要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话“鸦片战争”显然构成不了一个转折,比如龚自珍,我们觉得他是古代文学最后的一个大家,但他不是开创者,而是最后的终结者,而“百年文学史”就要把龚自珍放在里面。但是在我们看来龚自珍并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开始,所以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偏重从19世纪晚期开始,这个陈平原更有发言权,当时他正在研究那一段。
杨:对,当时他正在研究苏曼殊等人。
钱:我们认为最多只能从晚清开始,晚清那就比较接近20世纪文学了。这样就摆脱了政治社会史的划分标准,更强调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
杨:后来你们在万寿寺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言的是陈平原,但据说幕后的策划人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