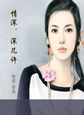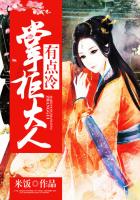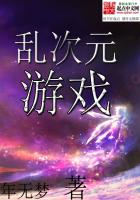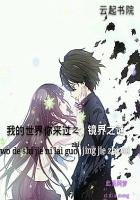钱:这是我们从不同的知识背景出发,不约而同的共同想法,谈不上是谁先策划。我们都是“哥儿们”,谁代表发言都无所谓,推陈平原作代表,是因为他在我们中间年纪最小,由他开炮,更有冲击力,而且他刚来北京,也需要亮一个相。再加上第一次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就必须讲清楚“发生学”
的问题,陈平原熟悉晚清,当然他讲最有把握。
80年代对于我们来说面临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当时我们还是青年学人(虽然从年龄上来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了),我们需要争取自己的发言机会,争取自己的言论空间。就我个人来说,考入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已经38岁了,当时王瑶先生跟我说,我知道你急于在学术界表现出来,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要厚积薄发,后发制人。我沉默了七年,在1985年才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时候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已经有了一些成熟的看法。所以当时我们非常感激那些首先发表我们文章的人,《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首先发表在《文学评论》,跟当时的编辑王信关系很大,紧接着《读书》连着六期发表了我们的“三人谈”。
我们三人比较早得到关注是黄子平,他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研192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究林斤澜的文章:《沉思的老树的精灵》,一举成名,所以他和陈平原与《读书》有一些来往,因为当时这些杂志都比较注意新人。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有一个编辑叫高国平,他找到了黄子平,问黄子平身边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同学,黄子平推荐了两个,一个是赵园,一个是我,赵园就写了《艰难的选择》,我是《心灵的探寻》,当场拍板出版,收入“探索书系”。还有一个就是浙江文艺出版社,主要是李庆西,他既是批评家又是编辑,出了一套书,黄子平、陈平原的都有,但没有我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年纪大了,这一套书影响极大。
还有就是几个刊物,一个是《文学评论》,王富仁、赵园、刘纳、汪晖、陈平原、黄子平全部是通过它出名的,另外一个就是《丛刊》,我先是助手,后来是编委,再到副主编,《丛刊》就成为我们共同的一个阵地了,另外还有就是《上海文学》、《上海文论》,福建的《当代文艺探索》。
杨:《上海文论》的创刊比较晚,影响要晚一些。
钱:好老师,好编辑,好杂志和出版社,还有我们自身的努力,80年代的学术研究的小环境实际上是很好的。
杨:您提到的这些实际上是一个文学场的问题,当时的文学场对你们是很有利的。那王瑶先生当时知道你们要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吗?
钱:其实当时这些想法都是一种共识,我们的很多举动如果没有老师的支持是不可能做成的。比如1985年第3期的《丛刊》,如果没有乐老师的支持,就不可能让我来编辑。实际上“走向世界文学”也是乐老师的思想,当时她正在提倡比较文学。我们当时上面有两代人,一个是王瑶那一代,一个是樊骏、严家炎那一代,所以当时有句话叫做“老中青结合”。其实我们的这些想法,也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前一辈他们就已经在考虑了,他们更早,他们是先行者。
杨:对,比如王瑶老师和严家炎老师提出了“现代化”的观点。但是我觉得他们讨论的不是很深。
钱:所以你不能说这是我们的独创,实际上是整个学科发展的一个结果。
在这之前,有一个更大背景的讨论,就是“如何开创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
杨:我觉得你们当时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说法实际上是对严家炎老师他们的框架不太满意的,他们当时主要是“回到乾嘉”,搞实证和史料,重新发现和发掘以前没有提到的作家、作品等等,比如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
等等,但是好像他们对整个文学史的框架还是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钱:8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是拨乱反正的阶段,这个就包括发掘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作家,还有一些作家被遮蔽的另一面。
那个阶段是有很强的政治性的,它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从1983年《丛刊》第3期开辟“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专栏,就意味着现代文学研究进入了学科自身建设的新阶段。
顺便说一点:这个专栏是樊骏、严家炎先生主持的;当时的现代文学研究,是在王瑶、唐、李何林、贾植芳、钱谷融几位先生的指导下,而具体的组织工作主要是樊骏、严家炎先生做的,樊骏先生起了更大的作用。因此,你们要研究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樊骏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思想,他所作的组织工作,特别是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视、培养与影响,是不可忽视,应该认真研究的。这次他主持的“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
的讨论,就是由老、中、青三代学人共同参与的。也就是在这一次的讨论中,提出了“文学现代化”的概念和标准;现代文学的当代性(这也是樊骏首先提出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内涵和外延;研究方法的革新等问题,你刚才提到的陈学超(他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也是我们那一届的研究生)的“百年中国文学”概念,也是在这次讨论中提出的。以上这些讨论,对我们后来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都是有影响的。1985年的创新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讨论的基础上召开的,而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为我们这一代提供一个发言的平台。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发出我们这一代研究者独立的声音。我们发言的中心,就是要提出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这也是我们当时感觉到的学术发展的一个客观要求,就是在对局部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进行“重新估定价194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值”(这是五四的口号,80年代也继承下来了)以后,需要一个整体的突破,进入宏观、综合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文学作为学科的总体进行重新估量和思考,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渊源、发展线索、阶段、进程,整个学科的基本格局,文学史编写体例等关系全局的问题”(参看赵园:《1985:徘徊、开拓、突进》,《丛刊》1986年第2期)。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次会上提出的,上海的陈思和在会上也提到了“新文学的整体观”的问题。所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是很自然的,是学科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后,具体的研究是没有进行下去的,后来1987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应该和它有一定的关系吧?黄子平和陈平原为什么没有参与它的写作?
钱:那本书是怎么产生的呢?最早是山西一个杂志叫《山西教育》,它约王瑶先生写一个文学史的系列讲座来连载,是带有通俗性的。王先生自己不写,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当时我刚刚研究生毕业,也想发表文章,所以我找了温儒敏、吴福辉,当时王先生希望我们把他女儿王超冰带一带,所以加上她。从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恰好我当时我正在教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实际上我写的部分都是我的讲稿。我们开始也不是很重视,主要是完成任务,也借此发表我们对现代文学的思考成果,后来才想到要出版,出版的统稿是我做的,然后写了个序,写那个序的时候正好我们在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杨:那个序基本上是一个启蒙主义的东西。
钱:对,那个序言基本上是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但是其他三个作者并没有参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我们的写作又是单独进行的,没有商量,所以问题就出来了,序和后面的正文内容有些脱节。后来1998年的修订本就把序拿掉了。其实当时没有更多的想法,就是出书,当时出一本书是很难的。书出来后社会反响也不大,主要是我们当时没有名气,后来之所以影响大了,和我们的学术地位的提高有关系。
杨:这种情况我倒不是很清楚,我就是把这两个版本拿来作了一下比较,修订版把序言去掉了,于是我就以为是你改变了对“启蒙主义”的态度,或者说不再坚持“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了。另外就是你在修订版里面提出了一个“审美”的东西,又提到“现代化”,我就以为你可能是把“启蒙”的边界放宽了。
钱:修订本有两个指导思想,一是它是教科书,不是私人著作,不能把太多的个人见解放进去。那个序言基本是我的观点,既不能代表温儒敏,也不能代表吴福辉,把它去掉是很正常的。还有把标题全部改了,以前的标题有鲜明的倾向性,那些标题都是我取的,去掉后是为了强调教科书的客观性,减少主观性和容易引起争议的东西。第二个指导思想是要把当时该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体现出来,比如增加了通俗文学,单章作家增加了沈从文和赵树理。沈从文是因为经过研究,我们意识到他的重要性(我们另一位同学凌宇就是专门研究沈从文的)就单列了一章。赵树理单列一章是我坚持的,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了取得平衡,就是不要搞得太“右”,记得毛泽东说过: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别种倾向,我受这个观点影响很大,就觉得在重新肯定被否定的自由主义作家时,也不能忽视左翼作家,文学史写作要注意二者的平衡。当然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赵树理,我对他的语言很欣赏。我们的想法是既要吸收最新的成果,又要和潮流保持适当的距离。因此,书出来以后,有两种评价,有的觉得太激进,有的又觉得还是有点保守,有“左”的遗迹,我们则认为这是教科书,必须如此。
现在看来,这本《三十年》至今还有生命力,跟我们的这一态度和选择有关。
杨: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是1998年出来的,而在1988年陈思和等人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中,第一期的文章就是批判赵树理的,如果按照他们的思路,赵树理肯定是不能列单章的。
钱:对,我们当时就是不想跟潮流太紧,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能够留下来长久一点。
杨:1988年上海的学者就开始提出“重写文学史”,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比196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你们要更激进一些。
钱:在我们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同一个会上,陈思和就提出了“新文学的整体观”。他们后来提出“重写文学史”,我们确实事先不知道什么消息,但他们提出来后,我们是很赞成的。后来在镜泊湖会议上,我们提出南北合作,他们在上海搞,我们在北京呼应。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丛刊》的编委了。
(杨:你就用《丛刊》来配合他们。)1988年底他们在上海开了一次大型的座谈会,我们《丛刊》1989年第1期就开了一个专栏,发表了汪晖写的《关于〈子夜〉的几个问题》,那就是我组织的(杨:上海那边发了一个蓝棣之的对《子夜》的重评的文章),那是我们在镜泊湖会议上商量好的。顺便说一点,考察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镜泊湖会议是不可忽视的,那是我们这一代古、现、当代研究生的一次大聚会,是京、海年轻学者的一次主动合作。参加会议的有北京的研究古典文学的张中、钟元凯,研究现代文学的我、吴福辉(他是会议的主持者)、凌宇、赵园、王富仁,研究当代文学的黄子平,还有上海的王晓明、陈思和、蔡翔等等,讨论中心就是如何打通古、近、现、当代,如何发挥我们这一代的作用,当时我们有很强的群体意识和主动性。镜泊湖会议以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编《丛刊》1989年第1期。那一期还有一个大动作,就是搞了个“论文摘编”,把与“重写文学史”相关的论文都摘了,包括黄子平和李稢的那个对话。那一期是明显的配合,煞费苦心,费了很大劲,这些在该期的“编后记”里面都提到了。
杨:那为什么当时你们没有想到“重写文学史”提法?
钱:怎么说呢?“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就包括了“重写”的意思,另外与北京上海两地的学风有关系。北京的学者很少合作提出问题(“三人谈”是很少见的例外),上海则喜欢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制造新的概念,北京都是配合他们。北大的传统是强调个人,很少开会,很少提口号,但是我们都参加别人提出的问题或者活动,这主要是学术传统的原因。至于我和陈、黄的合作是有缘由的,主要是当时我们三人都是一个人在北京,每天没什么事情就待在一起。但我们后来也很少合作了,主要的合作只有三次,一次是“三人谈”,一次是编“漫谈文化”系列丛书,一次是准备编一本绘图文学史。前两次都出我们所走过的道路197了书,最后一次因为发生政治风波,就流产了。
杨:“重写文学史”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要具体,是个案的研究,而且首先就是拿当代开刀的,我感觉就是当代实际上被取消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被取消、否定了。
钱:陈思和、王晓明都是脚踩现、当代两只船上的,和我们不太一样,我和陈平原都不谈当代,黄子平虽然是当代的,但他的兴趣越来越转向于史的研究,这与上海的那批学者是不太一样的。
杨:对,我也觉得你们史的研究多一些,但是上海的学者因为身兼二任,可能受到批评的影响多一些。
钱:我对当代文学的关注到1985年就停止了。
杨:你看,这是明显的区别,陈思和就说他为什么重新对当代文学感兴趣,就是在于“寻根文学”的兴起,让他很激动,于是想要重新研究当代文学了。
二、80年代的知识气候和学术传统杨:那您谈谈您的知识背景吧,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1960年到1978年,您在贵州待了整整十八年,这十八年您都在读什么书?
钱:我在《我的精神自传》里面也谈到了相关内容。我在大学时候主要读的是19世纪文艺复兴以来的俄国文学。在贵州主要是读鲁迅,当时我有一个很大的雄心,就是要把鲁迅读过的书都读一遍,我根据他的全集开了书单,但当时在贵州找不到那些书。当时主要就读两个方面,因为鲁迅是强调受压迫的民族的文学,我当时缺这一块,很奇怪,贵州安顺的图书馆很小,但是有很多北欧啊、南欧啊一些小国家的文学。另外就是读庄子,因为鲁迅受庄子的思想影响198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很深。然后就开始读马克思,我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我在一篇文章中讲过这个问题,其实读这些的动机都是奔着鲁迅来的,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就是鲁迅和周作人的比较研究。
杨:难道80年代初您没有读一些新的西方理论方法之类的书吗?80年代夏志清、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很流行,当时您读了吗?对您有何影响?
钱:西方的理论读得不多,但是夏志清和司马长风的书都是看过了的。夏志清对我的启发主要是他对几个作家的发现,一个是张爱玲,一个是师陀,还有端木蕻良,因为我认为一个文学史家的功力主要在于发现作家,所以印象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