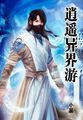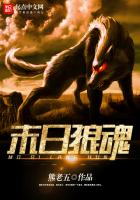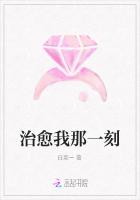高举“鲁迅‘五四’”旗帜的学者17了解了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就可以懂得,写于1939年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作为一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李何林先生,对这场论争的一个介入与发言。他与陈独秀一样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阐释“五四”的发生,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放松中”的“兴起”,“代表这兴起的民族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影响也日益显著起来”,“‘五四’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正是在此种觉醒下勃发起来的(俄国的‘十月革命’也给这一运动以很大的影响),相应着这种经济政治的情势,于是在文化方面就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出现”,而“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是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怀疑精神,提倡个人主义,提倡废孔孟,铲伦常”,而“这些内容,都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就是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反对封建思想”。这些论述显然是比较粗略的;后来,李何林先生又写了《中西市民社会的文学共同点》一文,从“市民社会的文学”的角度,从文学发展的源流与发展,来探讨“新文学”的产生与性质,如李何林先生自己所说,他的写作动因是想“藉以证明这新的历史观或科学方法的正确”。此文可注意之点有二:“市民社会的文学”的概念提出本身,自然是以西方文学的发展为参照的,但论述的着眼点却是“它们的一般和特殊,同点和异点”,因而有了以下的说明:“本文的市民社会是广义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把孕育近代工业资本的封建社会内的商业资本主义也包括在内;所谓‘市民’,是商业资本发达以后的城市市民,虽然可以包括工业革命以后的大工商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但也包括小商人及手工业者等等在内;所以它不是单指近代资产阶级而言,市民社会也不单是狭义的工业革命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有了“以鸦片战争为界”的两阶段的划分:之前是“封建社会的商业资本阶段”,“以后的中国近百年社会,虽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但是有着主要的近代市民社会的成分与趋向,因此我把它作为中国市民社会的一个段落,放在本题的范围之内”。
而文章的具体论述,则集中于“新文学”的语言、文体和这样的“市民社会”
的关系,于是,就有了“中西市民社会初期均有新语文的新文学产生”、“小说是中西市民社会的叙事诗”、“政论文学是中西工业市民阶级兴起时的斗争武器”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绪论》,《李何林全集》第3卷,页4—5。
这样的命题的提出与讨论。这里对“经济基础”与“阶级”、“社会”,以及作为文学本体的“语言”、“文体”关系的探讨,显然是既坚持“经济基础的最终的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与阶级分析的方法,但又避免将其简单化、直线化的一个自觉的、最初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还有同写于40年代的《文学与商业和政治的关系》一文。此文有一个副题:“评沈从文先生的《文学运动的重造》和《文艺政策探讨》”。针对沈从文的“新文学与政治和商业发生了关系,是其堕落的原因”的观点,经过具体而详尽的讨论,指出:“新文学运动本来是资本主义的玩意儿,它必定要与商业制度发生关系,借商业制度以广传布的”,而“古今中外文学都与政治有关”,沈从文所提倡的远离商业与政治,“由学校奠基,学校培养”的纯学术、纯文学的文学“重造”不过是“渺茫的”心造的幻影,而且有违于新文学的本质。人们自不难注意到,这样的关于“文学与商业和政治关系”的争论,直到今天仍在继续,李何林先生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文学、新文学的特质的阐释,也就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40年代李何林先生还写了一篇重要文章,即《读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
文章一开始便肯定谭书是一本自己所期待的“用进步的科学方法写作,不忽略文学本身的源流或发展,并兼顾与其他上层文化关系的文学史”著作,更充分肯定了作者所提出的文学史写作的“基本观念”:“(1)要把握历代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2)要把握文学的社会基础;(3)要探求文学形式的各种渊源(‘形式的变革多半被内容规定;但是内容对于形式的变化,也只是主要的因素,却不是唯一的因素’);(4)要把文学家的个人生活环境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并作出了如下评价:“以上这些方面都足以证明作者并非只是机械地应用唯物论或者笼统简单地以经济基础去解释文学现象,而是用进步的观点,从多方面去解释文学现象的。”这都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家正在努力克服“机械地应用唯物论”的幼稚病,在艰难地寻找一条恩格斯所提出的科学、正确地“应用”“新理论”。《中西市民社会的文学共同点》,《李何林全集》第4卷,页138、140、141、143、150。
《文学与商业和政治的关系》,《李何林全集》第4卷,页156、157、161—162。
《读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李何林全集》第4卷,页166、168。
高举“鲁迅‘五四’”旗帜的学者19的道路。应该说,在这方面,李何林先生是具有相当的自觉性的。
有意思的是,在1955年批判胡适运动中,李何林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批判胡适唯心论文学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的文章,重提胡适与陈独秀当年的那场论争。尽管在当时的语境下,不免有将学术上的论争无限上纲为政治问题的“左”的倾向,如将胡适所发表的不同意见说成是“和马克思主义文学史观对抗”,进而断定胡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死敌”,“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中国文学革命运动的死敌”,等等。但仍可以看出,李何林先生所坚持的是当年论战的基本立场,而且因为有了时间的距离,也就有了更为科学的分析。比如他这样谈到陈独秀在论争中的得失:“陈独秀的‘产业发达,人口集中’,当然不是科学的历史唯物论;但在当时(《科学与人生观·序》写于1923年)他是企图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从经济基础的变动去解释新文学运动发生的原因;‘经济史观’或‘机械唯物论’都在所难免。这种朴素的唯物论的运用,虽然显得简单和粗糙一些,但在当时的学术界还是有它的进步意义的。”
在论及胡适的观点时,他在肯定其观点的合理成分的同时,仍坚持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而与胡适划清了界限:“我们虽不否认胡适所提出的‘我们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有了全国各地通行的大同小异的官话’,‘有了欧洲近代国家国语文学次第产生的历史可以供我们参考,因而主张文学革命’———这三方面和新文学运动多少有些关系。同时,我们也不否认‘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满清帝室的推翻,民国成立’替新文学运动扫清了道路;但我们和胡适不同的是:我们认为这些‘政治势力’之所以形成,也是由于鸦片战争以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页477—479。
正是在这篇文章里,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斗争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来这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
后的经济基础的变动的‘最后之因’,不是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无干”;“这就是胡适的文学观和我们的文学观,胡适的文学史方法与我们的文学史方法的不同,他解释文学史现象,是向个人传记里面去找原因,把文学和文学运动当作是个人的东西;我们并不否认个人的东西,但我们把个人的东西和整个的文学现象当作社会现象来考查,当作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来考查,要研究形成它的社会原因,最后还要追查到‘最后之因’”。人们不难注意到,近年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的考察中,胡适的意见似乎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或许正因为如此,重温论争中陈独秀、李何林等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家的意见,应该是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与价值的。
(二)高举“鲁迅‘五四’”的旗帜《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的倾向性李何林先生在1982年所写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重版说明”里,特意点明他的研究的“倾向性”,这是关系到他的基本的学术立场与观点的,在他看来,“任何文学史,或文学运动、文学思想斗争史的编著者,表现在他的‘论述’部分中都有倾向性”,“所谓倾向性,就是倾向于赞成一方的思想,反对另一方的思想;而在引述双方的文章时又似乎很客观,但‘论述’起来就表现出并不客观了。世界上有真正客观的文学史、思想斗争史吗?”
而且李何林先生并不讳言:“这本书的倾向性,首先表现在前面的两幅铜版像:鲁迅和瞿秋白,而且标明他们是‘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在该书的序言里,更是高度评价鲁迅“在近二十年内各时期里面中国文艺思潮的浪涛中”所起到的“领港”与“舵工”的作用,以及瞿秋白在“中国新兴文艺理论建设中的地位”。
《批判胡适唯心论文学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并驳斥他所自吹的对于新文学的所谓“贡献”》,《李何林全集》第4卷,页25—26、28。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82年版重版说明》,《李何林全集》第3卷,页3。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序》,《李何林全集》第3卷,页6、7。
高举“鲁迅‘五四’”旗帜的学者21这样的论断,不仅如作者自己所说,为“当时一切反对派所不允许”,而且为当时的文学史家所不能接受。尽管在1930年李何林编选的《中国文艺论战》出版以后,曾有读者邢桐华来信提出鲁迅“在中国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与艺术家和战士,十个胡适之换不来一个鲁迅先生;十个郭沫若也换不来鲁迅先生的几本小说和数集杂感;五个郁达夫,四个周作人,都换不来鲁迅先生对中国的难磨的功绩”,李何林在回信中也表示“怀有同感”,但在许多人心目中,新文学与新文学思潮的“领港”与“舵工”仍是胡适等人,而非鲁迅。这在1935年、1936年所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这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文学第一次大规模的历史整理与叙述)的“导言”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胡适所写的《建设理论集》的长篇导言里,所突显的是他自己,以及陈独秀、周作人的理论贡献与作用,只字未提鲁迅;倒是郁达夫在《散文二集》导言里,朱自清在《诗集》导言里,都给鲁迅的散文、新诗创作以极高的评价;鲁迅自己在《小说二集》导言里,也这样谈到自己的贡献:“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82年重版说明》,《李何林全集》第3卷,页4。
邢桐华来信与李何林回复均收《李何林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5、2。
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313—314。
之外,运动的发动者与有影响者,都以自己的各自不同的理解、追求与实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上打上个人的烙印,甚至形成某种传统。于是,在总体的“五四”
之下,还有“陈独秀、李大钊‘五四’”,“胡适‘五四’”,“蔡元培‘五四’”,自然也还有“鲁迅‘五四’”等等。
后人,也包括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在对“五四”进行回顾,研究,叙述与评价时,事实上如李何林先生所说,是不可能不自觉与不自觉地表现出某种倾向性的,即在对“五四”精神有总体的认同或批判之外,也还包含有对前述不同的个人“五四”的不同理解与评判。在我看来,这或许正是一个契机:有可能由此形成不同的“五四观”及相应的不同学派。在这样的观照下,李何林先生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对鲁迅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新文学思潮史中地位的突显,就具有了重要的史的意义:这是第一部自觉地认同“鲁迅‘五四’”,突出鲁迅所代表与开创的五四传统的文学思潮史著作。由此形成了李何林先生独立的学术立场与独特的新文学史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他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新文学史的历史实际所获得的重要成果。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的风风雨雨中,他始终自觉而顽强地坚守着、发展着这样的学术立场与以“鲁迅‘五四’”为核心的新文学史观,以至在他临终前可以毫无愧色地作出这样的自我评价:“六十多年来,为党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的人才,坚持‘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发扬鲁迅精神,驳斥了鲁迅生前死后一些人对鲁迅的歪曲和诬蔑,保卫了鲁迅思想。”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鲁迅‘五四’”学派据说有的朋友曾讨论过现代文学研究界中的“李何林学派”的问题;在我看来,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确实存在着一个或许可以称作是“鲁迅‘五四’”的但如果仔细阅读李何林先生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仍可以发现,他在序言里所鲜明地表达的价值判断,并没有真正落实到他的历史叙述中,这里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涉及文学史理论的一些重要问题,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自传及著述经历》附录《1987年8月1日自制悼词》,《李何林全集》第1卷,页5。
高举“鲁迅‘五四’”旗帜的学者23派,李何林先生是举旗帜的代表人物之一,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许多前辈,如王瑶先生、唐先生也都是这样的举旗帜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