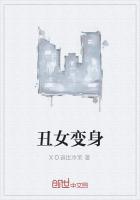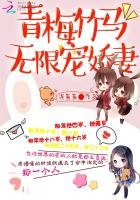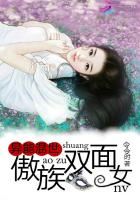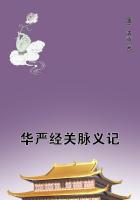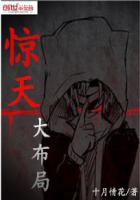应该说这样一种“鲁迅‘五四’”观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曾经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因而出现了十分复杂的情况。或许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不断有人对“鲁迅‘五四’”甚至“五四”传统本身提出质疑,如果是一种严肃的学术探讨,这样的质疑是有助于现代文学研究多元化的格局的形成,而且可以期待由此形成不同的学派;但如果因此而形成了对“鲁迅‘五四’”,以至整个“五四”传统的否定与消解,形成对“鲁迅‘五四’”派的压抑,则同样不利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健全发展。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李何林先生,探讨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贡献的意义所在,或许我们可以借此对李何林先生和其他前辈所开创的这一“鲁迅‘五四’”学术传统,进行科学的总结,并寻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这一传统的道路,这应该是“开创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三)历经磨难而信仰弥坚的风范最后,我还想讨论李何林先生这样的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历史命运问题: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却又是不能回避的。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被查禁李何林先生曾多次谈到他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出版不久,即被查禁(见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所收《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查禁成为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回避的原因是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评价所引起的意识形态乃至权力的介入,发展到极端,就将“鲁迅‘五四’”唯一化,对其他人的“五四”形成了某种压抑,而“鲁迅‘五四’”本身也出现了许多李何林先生所说的“歪曲”,以及投机者的渗入,并在事实上形成了对“鲁迅‘五四’”的不同理解与阐释,出现了许多分歧。而这样的分歧在学术研究中是永远存在的,因此,这里所说的“鲁迅‘五四’”学派本身,也只是大体上的价值理想上的相同或相似,而在进一步的理解与分析上仍是存在着歧义的。也因此没有学校请他教书,只能改行。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曾被视为洪水猛兽,视为非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必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马克思主义本质上的批判性决定了他的真正信奉者也必然为专制体制所不容。近年来总是有人有意无意地掩盖、遮蔽这一事实,美化国民党专制政权,这是颇为奇怪的。
《近三十年中国新文学运动大纲》的困境当1948年5月,李何林先生逃脱国民党的追捕,来到华北解放区,并被任命为华北大学国文系主任,他自然会有一种解放感,并期待着可以自由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来进行被中断的现代文艺思潮史的研究。于是,他很快就依照《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的纲目,加上抗战以后的十年,写出了《近三十年中国新文学运动大纲》,但没想到却因此陷入了困境。这是因为这时的解放区的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已经确定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方针;对这一点,李何林并无抵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的方向”定位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是与李何林的“鲁迅‘五四’”观相符合的,事实上,李何林在《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序言中就不点名地引用了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陕北公学讲话中对鲁迅的评价。但是,问题在于李何林与毛泽东的“五四观”既相同又不同,如前文所说,李何林从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关系的分析出发,断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毛泽东则为了中国共产党争夺思想李何林并据此作了发挥,说“埋葬鲁迅的地方是中国新文学界的‘耶路撒冷’,《鲁迅全集》中的文艺论文也就是中国新文学的《圣经》”。(《李何林全集》第3卷,页6)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的演讲由胡风在他主持的《七月》月刊(重庆出版)1938年第3期首次发表,毛泽东的“鲁迅观”也就在大后方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产生了很大影响。而据李何林在《1982年重版说明》中交代:“在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全国反共高潮(1939年冬—1940年春)的前夕,在法西斯统治的四川,我没有说是毛主席说的,用了‘有人说’三个字。”(《李何林全集》第3卷,页4)高举“鲁迅‘五四’”旗帜的学者25文化政治领域的领导权的需要,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位为“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所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文化运动。本来这样的分歧是可以通过学术争论来解决的,但解放区所建立的新的思想文化体制却要求毛泽东思想的绝对领导,不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而且任何思想、学术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于是,就有了1948年10月、12月时为华北大学领导的何干之与钱俊瑞的两次来信,尽管采取的是尽量说理的态度,并直接引述了毛泽东的观点,作为说服的依据;但内在的政治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一位传记作者所说,大有“必须修正”之势。但李何林却并没有立刻放弃自己的观点,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我当时虽然觉得他们说的也有理由,但并未能使我心服”。直到后来与范文澜交换了意见,又经过长时期的思考,才“认识到他们的见解的正确”,并于1950年写出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性质和领导思想问题———〈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自评》,基本上接受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
应该说,李何林对毛泽东五四新文化观的全面接受,既有原有基础,又经过后来的认真思考,而且此后从未动摇,直到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人重提当年的论争,认为真理是在李何林先生这一边,李先生却表示:“我现在倒不这样看”,仍然坚持在《自评》中已经认定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论”。但他同时又表示,领导思想的问题还是“可以讨论的”。《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遭批判尽管李何林先生“心悦诚服”地放弃了自己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的一些观点,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就自然日益为要求所有的拙作《远行以后———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对此有详尽分析,可参看该书页36—39。
参看田本相:《李何林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158—159。
参看《〈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自评》,《李何林全集》第3卷,页1—9;《我的文学研究与教学生涯》,《李何林全集》第1卷,页4。据李何林先生所说,最后说服了他的是范文澜所说的“无产阶级思想在这个运动中虽然数量比较小,质量却比较高……这是从发展的一方面着眼所得的结论”这一段话。李何林因此而检讨自己“在蒋管区虽然也看过一点辩证唯物论的书,记了一些书本上的法则或教条,但不能运用于实际,遂把一个衰老没落的似乎强大的事物(资产阶级思想)遮盖了新生的发展着的量虽小而质高的事物(无产阶级的思想)的领导作用”。
识分子都成为驯服工具的体制所不容,终于在1959年至1960年间,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所谓“李何林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起因不过是他写了一篇题为“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的短文,就文艺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独立见解。在宣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独立思考的学者,却遭到了无情的批判与压制,这个事实或许更为严峻,而且更加发人深省。
面对这样的对他而言也许是过于严酷的现实,李何林先生表现出“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大家风度,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决不动摇,可以说他至死都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个坚定的“鲁迅‘五四’”派。李何林先生留给后人的历经磨难而信仰弥坚的风范,也许是更加值得我们永远怀想的。
2004年9月10—12日,29—30日参看田本相:《李何林传》第十五章《“一个小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初在作四十年代小说研究的时候,就读过《贾植芳小说选》,当时即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并且决定要将其写入计划中的《四十年代小说史》里。但这部小说史迟迟不能问世,心里总觉得欠了贾先生(以及40年代未能得到正确评价的作家)的一笔债,是作为文学史研究者的一种失职。最近,偶然翻点藏书中的四十年代小说,这本《贾植芳小说选》赫然在目,心又为之一震,觉得无论如何也得写点什么了。
(一)在文学创作起点上与鲁迅的相遇而我此时的研究兴趣却首先在文本之外的“故事”:它的写作,发表,出版,结集……过程中的作者与作品的生命故事。于是,我注意到了贾先生在“编后记”里对背景材料的介绍,这篇《从小说创作看贾植芳先生》也就从这里读起。
收入《贾植芳小说选》的第一篇《人的悲哀》是1937年4月发表于冯雪峰、茅盾、胡风联署,而由胡风实际主持的《学习与生活丛刊》第四辑《黎明》上的。
据贾先生回忆,他当时还是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学生,在日本一个大学挂着学籍,是因为在东京神保町的内山书店看到《丛刊》的头两本:头本题为“二三事”,以鲁迅的遗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为书名,第二本题为“原野”,以艾青所翻译的法国诗人凡尔哈伦的长诗《原野》为题名,他正是从这样的“刊物的作者阵容和编辑风格上认识到它是高举鲁迅先生的战斗文学旗帜前进的严肃的28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文学刊物”,这才决定将1936年秋冬刚写出的小说投给《丛刊》。应该说,青年贾植芳对《丛刊》的性质、编辑意图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因为我们从胡风的回忆中知道,编《工作与学习丛刊》是冯雪峰交给他的任务,目的是要在鲁迅逝世之后,通过这个刊物,“和鲁迅的老朋友以及他晚年接近的青年取得联系,在思想上和创作上学习并发扬鲁迅精神”。而在胡风的理解里,“鲁迅精神是全民族、全体劳动人民的精神财富,继承并发扬鲁迅精神只能放在劳动人民的斗争实践上面,也就是,把希望放在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结合着,能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真实和斗争意志的作者,尤其是成长中的青年作者身上”。因此,胡风在编《丛刊》时,除了按照冯雪峰的意图,发表了一批鲁迅的老朋友(如许寿裳、李霁野)与他周围的年轻人(如曹白、力扬)的文章与美术作品,同时以更大的篇幅发表初露头角的新作者的作品(如艾青、端木蕻良的诗与小说),注意从业余作者中发现文学新人。
贾植芳的《人的悲哀》就是这样被他从自然来稿中选拔出来的。在这一辑的“校后记”里,他以抑制不住的喜悦这样写道:“《人的悲哀》是一篇外稿,也许读起来略嫌沉闷吧,但这正是用沉闷的坚卓的笔触所表现的沉闷的人生。没有繁复的故事,但却充溢着画的色调和诗的情愫,给我们看到了动乱崩溃的社会的一图。”
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编者与作者之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也可以说是一次历史的相遇:当冯雪峰、胡风在鲁迅逝世以后试图继续高举鲁迅的文学旗帜时,青年贾植芳自愿、主动地站到了这面旗帜下,从此走上了极不平凡的人生与文学的不归路。
这条道路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坎坷不平的。据胡风说,当初采取以书代刊的“丛刊”形式,就是考虑到“登记出杂志一定得不到国民党的批准”④;但第二辑《原野》出版后不久还是被国民党禁止了。而在两三天以后,同一机关又有公事到代售的书店,说在报上看见有《原野》的广告,不晓得内容反动与否,着缴呈若干本云。这就是说,“禁止了还不晓得内容反动与否,或者说,还不晓得内容反动与否就禁止”。面对这样的荒唐的检查制度,胡风立即著文加以揭露,指出:“‘统制思想’政策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继续,这个政策胜利的时候就是中国的‘沙漠化’的完成。”但胡风的抗议,却引来了更严厉的管制:《丛刊》第四辑(也就是发表贾植芳小说的这一辑)原题为“街景”,是用美国共产党刊物《新群众》上的一幅石板画命名的,但排成后就得到书店的通知,说前三本都被禁止了,这一本虽已排成,仍不能出,只好拆版。
因此,在很长时间内,胡风都以为这一期刊物(自然也包括贾植芳的作品,连同他自己的评价)已被扼杀在摇篮里,不见天日了。但48年后的1985年,上海书店要影印《工作与学习丛刊》时,才发现后来不知是谁(估计是书店)还是将第四辑印出,但改换了封面,辑刊题目也改为“黎明”,于是,贾先生的《人的悲哀》也就死里逃生,侥幸问世。这真可以称之为“书的悲喜剧”了。今天我们重读《人的悲哀》,很容易就注意到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是鲁迅式的意象:“门前的街沿上,一只稀见的身材高大的羊,态度轩昂地领着一群仪容大相悬殊的小羊走着。”———这也是鲁迅在《一点比喻》里描写过的隐喻性场景;“我转过身,像一匹受伤的兽,忿怒得燃烧得不顾那些睡客,脚步沉重地踏着楼梯,跑上楼去”———仿佛鲁迅的《孤独者》里的那匹“受伤的狼”的“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那声嗥叫,重又响起。而小说最后的点题之笔:“我的敌人已不是先前可怖的侦探,而是现在自己的怯懦,因为我有了一个避难所,人是惯于苟安的……”,“我应该走一条(自己的)路……”;还有那笼罩全篇的恐惧与绝望,以及被“历史的沙土埋得重重的,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我似乎躺在荒原里或者闹市,许多可怕的东西,渐渐成形,猛兽般向我袭来,监房的血泪和铁镣,寒冷和阴森,咒骂和啜泣……”:这些也都是鲁迅式的。
鲁迅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写到他的这种被掩埋的窒息感。如“沉重的沙……沙漠在这里,恐怖的……”(《热风·为“俄国歌剧团”》);“……许多青年的血,层层郁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为了忘却的记念》。
今天的读者更为注目的,或许就是作品中处处显现的小说主人公对外部世界的感觉与联想的奇峻,像“我恐惧地望着四周,人们的态度一如乌云退后的太空,明快而闲适,闲适得简直有点残忍”;“连阳光也显得灰沉,像喝过砒霜后难看的面孔,死滞在这里”;“空气像一根新的绳子”;“当他脚步踏上楼板的第一声,全楼响起一片空前的震动,像是弱小者的绝望的呐喊”;“他趁势把两手伸得高高的,支起脚尖,凄凉地打了一个大哈欠,嘴城门般的张圆,然后放下脚跟,嘴又猛地紧闭,两手随着死了般的摔下来”;“我就上了楼,背后是一群奇异的眼睛,像送葬行列后的眼睛,饱含着惊奇和悲哀”:这些文字都具有一种震撼力,给人以新奇感,尤其是那种“痛苦而神经质”的感受世界的方式,也都是鲁迅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