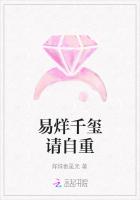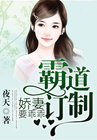我们还是从上海的另一位学者张新颖的自述说起吧。他在其专著《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的“后记”里,这样谈到自己在研究中,“对既成的思路和方式的不安和疑惑”,以及从中挣脱而出的过程:“本来我的设想是:把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当成一个具有完整过程的整体,就像一个生命一样,来描述它的发生、发展、高潮、衰落,这样的描述能够提供一个清晰的脉络,提供一个相对独立和自足的系统。如果这样来描述和研究,一定会获得很多研究者的首肯,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这样来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我们不但这样思考,也希望别人这样思考,更严重的是,我们希望事物也像我们思考的那样发生、发展,那样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可是当我真正深入到研究中去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设想只能是一个设想而已,事物根本就没有像设想的那样发生、发展。在研究中我得出了一个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基本看法:它不断发生,甚少发展,王晓明:《重建统一的个人生活》,文收罗岗:《面具之后》,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256—257。
不成系统。在一二十年代就出现的现代意识不一定就在后来的时间里得到继承和发展,说不定多年以后还要重新来过;后来者的水准和高度不一定就超过先行者;它散乱地出现,不可能有一个自足的系统。”不难看出,张新颖这样的新一代的研究者所质疑与竭力要摆脱的,正是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我们研究界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历史决定论、历史进化论的,本质主义的文学史观;正如张新颖们所觉悟到的那样,按照这样的文学史观所描述出来的井然有序的合目的性的文学史图景,必然是对历史的简化和抽象化,“复杂化的甚至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文学史的原初景观就轻而易举地被抽象掉,整合掉了”,这实质上是一种唯意志论的曲解。与这样的历史观同时受到置疑的,是对研究者自我角色的传统定位:长期以来,研究者都充满了自信,以为有权对历史事件、人物作出权威性的,甚至是终审判决性的评价,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历史审判者的角色;而且我们还坚信自己能够发现某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历史必然性的阐释者的角色。现在却产生了怀疑:尽管仍不能完全避免评价,但至少对评价权威性发生了动摇,更毋庸说判决了。有的学者因此而提出了研究者的历史叙述者的角色定位,并由此产生了文学史叙述策略的选择:强调突出历史事实的叙述,多侧面、多方位、多层次地展现原初景观,不回避其中的矛盾冲突与悖论,突现历史细节,以“直面文学史的复杂的经验世界,直面原初的生存境遇”,给读者提供尽可能广泛和开阔的想象与评价的空间,等等。当然,对这样的角色定位与叙述策略,也同样存在着质疑,一切都还处在探讨的过程中;但研究者自我角色的认定的变化,仍是引人注目的。
历史决定论、进化论的本质主义的历史观的破除,也引发了对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曾有极大影响的借助现代性理念所建立起来的文学史观念的质疑。
吴晓东在他的获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里,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观念体系中一直隐含着‘传统—现代’的二元论模式,这种二元论,建立在以‘进步’的目的论为内含的线性的时间观念之上,从而在价值判断上体现为新与旧的鲜明的分野。现代性的理念为历史的理性注入了价值论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后记》,三联书店,2001年,页292—283。
吴晓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同上。
新一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213的依据,因此,那些无法纳入革新、进步、未来范畴的事物,都可能因其保守、落后、垂死而逐渐丧失存在的合理性,最终被历史的记忆所淡忘”,“线性的价值准则从而导致了单一的审美判断和取向。我们很难看到那种新与旧杂陈的繁复的美感,也很难看到超越于传统———现代之外的更具兼容性的审美视角”,由此提出的是“重建更为复杂的文学史叙事,以及重建更为复杂的中国现代审美主义的历史脉络”的任务和目标。这自然是有启发性的。
思考更深入一步,就对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些“未加论证即作为前提使用的命题、概念和价值标准”提出了质疑和反思。罗岗正是在他的系列研究中不断地提出追问:何为“文学”?何为“现代”?何为“现代文学”?如他自己所说,之所以要提出这样一些“需要重新思考的论题”,“恰恰是因为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根本不成其为问题,而是被当作一个自然过程的结果加以接受的”,于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文学’被建构起来的历史语境,有意无意地遗忘了簇拥着‘现代文学’的各种力量,有意无意地简化了由多种力量共同铸就的‘文学’的复杂涵义”。这样,“文学”(“现代文学”)就成了词典、史书与课堂上的“一种知识,它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权威性,却失去了和历史的鲜活的联系;它理所当然地成了对诸种文学现象进行分类、规划和评判的标准,却失去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反思起点”:“社会历史文化是通过何种途径将‘文学’建立起来的”,“‘文学’又是如何透过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管道’生产出来的”,也就是“文学”是如何“转化为一种变动的‘话语实践’”,“现代文学”的观念与体制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罗岗在他的获奖论文《“分期”的意识形态》里,又以《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为个案,把追问指向关于现代文学的知识生产,即对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与研究,竭力揭示现代文学史叙述中的“‘时间’和‘分期’的背后”隐藏的“‘知识权力’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带动的制度运作”。他也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与目标:将“已经被‘自然化’的新文学历史再次‘历史化’”,以求“从变迁的历史中,从吴晓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罗岗:《作为“话语实践”的“文学”———一个需要不断反思的起点》,《现代中国》第二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与现实的对话关系中来重新理解新文学”。这些年关于现代文学的观念与体制建构的研究,有学者命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制度”研究,包括作为文学制度的社会背景的“知识分化与新式教育,大众媒介与都市文化”的研究,“文学社团与组织制度”、“文学论争与批评制度”、“文学媒介与传播制度”、“文学审查与评奖”、“文学的接受与反应”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以及对作为文学知识生产的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研究,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其出发点与研究动力也许并不尽同于罗岗,但其对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的开拓与推进,却是显然的事实。
也有年轻学者对学术界颇有影响、几乎是不易之论的观点提出质疑。刘永泰在他的获奖论文《人性的贫困和简陋———重读沈从文》中,就对沈从文研究中“看重人的自然属性而轻视乃至排斥人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倾向,提出了批评———这样的倾向,其实不仅存在于学术界,在90年代的创作中也是相当“时髦”的。作者从“人有丰富的规定性,人性结构是人的多种属性的统一”
这样一个理论基点出发,对沈从文作品中所建造的“人性神庙”及其意义作了更为复杂的分析。一方面指出,“很多人都乐观地认为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人性的同步发展”———这样的观点直到80年代的中国,还是相当流行的;而沈从文却看到了“发达的社会性非但没有促进人性结构的优化,反而使人的自然属性的正常伸展受到严重压抑,整个人性结构处于扭曲变形之中”,“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其作品的价值所在。作者同时提醒人们注意:绝不能因此而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未受文明污染的爱情”视为“健全的人性”,因为“那是人性的诸多要素没有充分展开前的原始的完满,原始的丰富”,而如马克思所说,“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作者的具体观点可能会引起争论,但如我在给罗岗的“获奖评语”中所说,“这正是其价值所在:它打破了囿于既有‘结论’,在使其精细化或重新组装上‘大做文章’的学术研究的平庸状态”,“这样一种‘重新研究一切’的胆识,‘发现并提出问题’的眼光与能力,显示了年青一代学者可贵的学术锐气,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罗岗:《“分期”的意识形态———再论现代“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3卷2期,2001年3月。
参看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刘永泰:《人性的贫困和简陋———重读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
新一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215我在前述评语中,紧接着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而作者又没有陷入空泛议论或故作翻案文章,而是对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史现象进行精细的个案分析,……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从而把自己的‘置疑’放在‘理解’的基础上;这样,作者提出的问题就能够真正成为‘学术问题’,而不是媚俗的炒作。这是更为难能可贵并应予以提倡的。”这里所提出的学术研究的新起点,必须是“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是“学术问题”而不是“非学术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重新研究一切”,其内含的是在扎扎实实的知识基础上而生发出来的怀疑精神,是对中国文学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严肃思考、研究与反省的科学态度;在具体操作中,它又是以大量的原始史料的重新发掘与审视为基础的。我注意到新一代的研究者在回述自己的研究历程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在图书馆里孤苦读书,埋头于旧报刊的灰尘里的情景,这对于我,正是十分熟悉的:我们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导与要求我们的,唐先生、王瑶先生……都是一再强调要多读旧期刊,这样才能真正进入历史情境中去。这可以说是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好的经验与传统:学术视野的新开拓必然带来史料的新发掘、新审视,而学术的新突破又必然是以翔实的史料作为依托的。
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研究一切”是应该以重读作品,重新接触、发掘第一手史料作为起端的。这样,学术的创新才能建立在坚实可靠的科学的基础上。
在“重新研究一切”的自觉的同时,还有一个“自立标准”的自觉。张光芒在他的获奖论文《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哲学建构》里,提出应该“真正把中国现代启蒙主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或个体来看待”,他指出:“任何外来思潮在本质上都必然是‘他者’”;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与发展,曾经受到外来思潮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外来思潮如何参与到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建构之中,这确是应该认真研究的课题,但却不能因此“从‘他者’的思想体系出发,以‘他者’的原理、范畴为评判标准,而必须回到历史的现实性对应关系中,寻找其内在的思想理路与实质内涵”。这里所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要。我们知道,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曾经受到所谓“撞击—回应”模式的深刻影响,而这一模式是有着明显的“欧洲中心论”的印记的,如何从中摆脱出来,确立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独立自主性,是90年代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另张光芒:《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哲学建构》,《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一方面,我们所说的新一代研究者,他们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曾受到西方理论与西方汉学研究的深刻影响,这从一个方面构成了一种研究的优势———我在与这些年轻学者的交往中,就深深感到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修养是远胜于自己的;但这同时也可能存在着一个“陷阱”,即很容易驾轻就熟地将自己的研究强纳入某个现成的西方话语体系中,成为证明某种西方时髦理论正确性的例证,从而失去研究的独立自主性———事实上,这已经成为某些“新潮研究”的致命弱点。现在“自立标准”问题的提出,表明新一代学者对此已经有了新的自觉,这对于确立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的双重独立自主性,自是意义重大的。年青一代这样的自觉意识,与前述“重新研究一切”的自觉,在我看来,都会对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前景产生深远影响。
(三)
以上讨论的,主要是观念与研究思路的变化。下面,再具体地讨论这次获奖文章所显示的研究的若干新的特点。
首先,有好几篇论文都把目光转向现代文学的起点,进行溯本求源的“发生学”研究,而且处理的是两个最关键的、难度也最大的问题:现代文学观念与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与形成。这十分引人注目:它是最能显示新一代学者的眼光、魄力与研究实力的。王风的获奖论文《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以刘师培为个案,把对新文学的探源伸向晚清以来的中国学术发展的脉络,以编年史的方式,描述一个有着明显学术渊源的带有纯文学倾向的传统文论体系,如何在晚清的背景下与西方学说发生某种契合,在某些具体学术论争的刺激和推动下,出现了现代转化的可能性。这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生成史的一个重要环节,现在通过作者精细的辨析和梳理得以呈现,并借此“展现晚清文化某种气质”,也使“读者对先驱者当日探究中国文学观念现代化进程的艰难起步有了感同身受的体会”。这也显示了中国学术界跳出了前述“撞解志熙:《王风〈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获奖评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