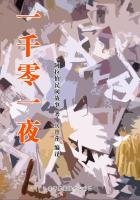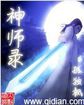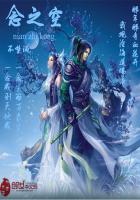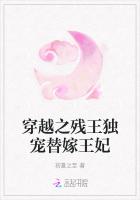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本书好几篇论文都谈到端木蕻良先生“几乎从创作的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思想性”,他一再强调:“文章的深度就是思想的深度”,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个精纯的思想系统,而想写出了不起的作品,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没有思想的人绝不会体验身受的生活是什么。过去一般指示者,多说什么从实现生活来体验哪……之类的话,其实没有思想的体验是完全无用的,一个农夫想让他说明自己的生活为不可能,但是一种刻苦的观察,可以得到这些”。因此,他可以说是完全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眼光来烛照他的描写对象的;他这样提示:“我很想让读者在看《科尔沁旗草原》的时候,能注意到它背后的一种特定的经济结构来”,如曹革成先生所说,他的这部小说“很明显有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理论在里面,他是把政治小说做成文学艺术作品很成功的作家之一”④。这些方面都是很能显示左翼文学创作的特点的,但也正是最容易引起批评的地方。
多年来学术界一直盛行着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仿佛明确的理性介入,对④逄增玉:《论端木蕻良小说创作的两种追求与风格》。
端木蕻良:《文学的宽度,深度和强度》,1937年12月16日《七月》第5期。
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后记》。
转引自马伟业:《论端木蕻良文学创作的深度和强度》。
作为左翼作家的端木蕻良253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思想性的自觉追求就必然地导致文学性的削弱,这其实是缺乏分析的。理性分析如果不能与“结实的生活血肉统一起来”,确实可能出现“作品的形象不堪承受作者理性思考所赋予的意义”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一种必然,就端木的创作而言,固然有些作品不同程度存在这方面的缺憾,但理性之光的烛照在更多的方面,使端木的创作得到升华,获得了他所追求的文学的“宽度,深度和强度”,获得了论者所说的特殊价值:他的作品对“特定历史时期原生态的文化形貌”,“对当时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世俗生活、家庭生活状态”的极为精细的刻画,“特别是对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的细节描绘蕴涵着各式各样的物化信息,具有经济文化和历史文化的认识意义,是近代东北经济生活的形象的切片”———这也许是一个更值得重视的文学事实。端木蕻良的创作实践证明了:作家“对原生态社会存在的经验直觉、体悟”和“感性描绘”与“知性分析”是可以统一的;对社会人生、政治、经济的现实关怀与对人的生命存在的超越性关怀是可以统一的;对具体形象刻画的写实主义的“真”与追索形象背后的意蕴与意义的象征主义的“深”是可以统一的;或如作家自己所说,“诗的想象跟哲学的理解以及心理的观察”是可以“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在这方面,端木蕻良先生是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的,值得认真总结。
这里,实际是包含了某些理论问题与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诚然,我们曾片面强调理性、理论的作用和对思想性的追求,而忽视以至根本否认非理性的直觉、感悟与感性描绘、艺术追求,但是否可以反过来不加分析地否认理性、理论的介入,忽视或否认作品的思想力呢?说到底,这是关涉到我们对“文学与文学性”的理解与想象:文学难道真的就是“绝对非理性,纯个人性”的,那种与社会绝缘、将思想逐出的“纯文学”是真实的存在吗?文学的功能难道仅限于审美,而可以忽视或否认文学的认识作用吗?等等。这些看起来都是常识,但如不从理论上加以澄清,在我看来,是很难对包括端木蕻良在内的左翼作家及其文学作出科学的评价的,而且也不可能对其确实存在的历史教训作出真正触及要害这是我在《四十年代小说研读札记》一文中对端木创作所提出的批评。现在看来,我也许过分地强调了这一方面,而忽略了理性介入对端木创作的积极意义,这也多少反映了前述流行理论的影响。
尹建明:《端木蕻良小说的文化视界》,马伟业:《论端木蕻良创作的深度和强度》。
端木蕻良:《〈曹雪芹〉前言》,可参看尹建民:《端木蕻良小说的文化视界》,马伟业:《论端木蕻良创作的深度和强度》。
的科学的总结。
这里还需要提及一种似是而非的评价:仿佛左翼文学对思想的追求压倒了对艺术的追求,因而在艺术上总是粗糙的。对所谓艺术的“粗糙”,其实也是应该作具体的分析的:有的确是由于急促而缺少艺术的从容运思带来的某种艺术上的缺憾,这种情况即使在端木蕻良的创作中也时有出现,某些左翼作家的创作中则更为严重,这都是无须讳言的;但这也并非左翼作家所专有,被许多研究者看好的非左翼作家也有粗糙之作,可见艺术的粗糙和左翼作家对思想性与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被一些研究者批评的“粗糙”其实是左翼作家对不同于传统艺术趣味的新的美学风格的一种追求与实验。如一些研究者所注意到的那样,端木蕻良自称“性格的本质上有一种繁华的热情”,自己与故乡人民双重的奴隶地位“形成一种心灵的重压和性情的奔流”,也就着力追求艺术上的“强度”:人物塑造上的“强动作”、“直立感”,小说意境的阔大,节奏的急促,语言的力度与独特修辞,等等,从而形成了“重,粗,大”的艺术风格。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也有类似的风格,如果用传统的审美眼光看,是很难被接受的;因此,鲁迅特意提醒人们:“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这里所显示的,正是左翼文学在艺术上的反叛性、异质性,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创造性。在我看来,左翼作家(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就是鲁迅所说的永远“不满足于现状”④,由此而形成了其永远的批判性(反叛④端木蕻良:《我的创作态度》。
参看逄增玉:《日神文化与东北作家群的创作》,马伟业:《论端木蕻良文学创作的深度和强度》。近年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研究者都比较注意端木蕻良创作中的“两副笔墨”,这对揭示其创作风格的丰富性是有意义的;但这不应该导致价值判断上的倾斜,应该说无论是“重,粗,大”,还是“轻,细,小”,都是各有其美学意义与价值的,而且端木蕻良创作的主体风格还是偏于“重,粗,大”的。
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
参看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是在界定“真的知识阶级”时提出这一标尺的,同时提出的还有永远“为平民说话”。在我看来,左翼作家(左翼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为平民说话”就是站在被压迫的工农群众这一边,因此,鲁迅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我以为这是对30年代的左翼文学的一个经典性的定义。端木蕻良创作的倾向性表明,他的文学无疑是属于左翼文学的。
作为左翼作家的端木蕻良255性,异质性,非主流性)。而这样的批判、反叛必然是全面而彻底的:不仅表现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倾向、政治立场,而且也反映在对既成的艺术秩序的反叛与不循常规的创造。因此,前述“左翼文学不注重艺术形式”的说法完全是一种成见与误解:左翼文学的一个本质特征即是它的艺术上的“实验性”。很多论者都谈到端木蕻良在小说艺术与文学语言上的探索所显示的“野性”即“非正统倾向”:在这方面端木蕻良在左翼作家中也是有代表性的。
当然,对代表性也即共性的强调,并非要否定端木蕻良在左翼作家中的个体的存在及其鲜明的个性。左翼作家本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鲁迅这样的“五四”老将,他们大都有中国传统士大夫家庭背景与文化传承(或如鲁迅说的“因袭的重担”);另一部分年轻的左翼作家,相当多的人是出身于社会的底层,或有着复杂的底层生活经验的,像端木蕻良这样出身于豪门巨族、流淌着贵族血液的,并不多见:这或许就是端木蕻良在同辈左翼作家中多少显得有些特殊之处吧。更重要的是,特殊的家庭背景所形成的端木蕻良所特有的精神气质更使得他显得有些异样:正像研究者所分析的那样,一方面,父辈传下来的“莽原子民的奔放、剽悍”之风培育了他“繁华的热情”与堂吉诃德式的拯救天下苍生的英雄梦;另一方面,“大草原的空旷与寂寞、母亲的悒郁、走向没落的士大夫的大家族生活”又赋予他“细腻与善感的本性”,“彻骨的忧郁”与孤傲,哈姆雷特式的优柔寡断,“长于沉思、冥想,迟疑于行动”。在《科尔沁旗草原》里,有一个小说主人公丁宁的性格组合公式:“民粹主义(虚无主义)+利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感伤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丁宁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端木蕻良对自己庞杂的思想体系与多重精神气质的一个概括,在我看来,是相当准确的。正是这样的庞杂的思想与多重气质内在地决定了他既倾向革命,成为一个左翼作家,又与革命格格不入,终于是左翼作家中的另类。应该说左翼作家中也有不少人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思想与精神气质的矛盾,有的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逐步自觉不自觉地克服(或压抑)了革命所不容的思想与气参看孔质,终被革命所接纳;也有的则本性难改,与革命始终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端木蕻良大概就是其中的一位:尽管他也曾努力地调整自己,却始终坚守着固有的自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我看来,就是他无法摆脱自己更为内在的彻骨的孤傲的贵族气。这样,端木蕻良在同辈左翼作家中始终处于“不被人理解、不被人认同的孤独”状态,遭遇到“被抛出群体之外的冷落”,就是不难理解的:这正是隐藏在种种人事纠葛背后的更为重要的历史内容。
这样,作家端木蕻良自身的精神历程与境遇就具有了一种“史”的意义;而研究者尤其感兴趣的是,这样的精神史已经外化为端木蕻良作品中的“丁宁———兰柱———石龙(我觉得也许还要加上曹雪芹)”“自我形象”发展史,这是构成了端木蕻良创作的一个重要底蕴的,这方面的研究也才开始。这或许表明,端木蕻良的研究还孕育着新的可能性,现有的研究成果,打开了思路,开拓了广阔的研究前景,我们应该向所有的默默耕耘的作者表示敬意。我的这篇读后感,正是由他们的研究引发的,也应该道一声“谢谢”!
参看前文与孔海立:《端木蕻良和他的小说(1933—1943)中的自我形象》。
参看前引陈悦与孔海立的文章。
令人大开眼界的文学史景观257令人大开眼界的文学史景观———读《20世纪贵州文学史书系》这些年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出了不少的专著,但像《书系》这样系统、全面地叙述一个地区的20世纪文学发展历史的,我还从未见过,这是自有开拓的意义的。而我最为看重的还不是这一点,而是这套书的写作,对我们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启示。
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首先注意到的是它的源头。这些年,晚清文学、民国初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始终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目前这类研究大都限于少数中心城市,这就多少有些遗憾。这回一打开《书系》,每部著作的开篇第一章都有关于从晚清到五四的贵州文学现象的梳理与研究,这在我至少是大开眼界的。于是我因此知道了1907年7月17日贵州第一份报纸《黔报》问世,并辟有发表文学作品的“杂俎”、“谐谈”、“短篇小说”栏目;作者说:“若与京、沪等地报纸出现的时间相比,却几乎晚了近半个世纪”,但我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这一事实。现代报刊的出现,无疑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新质因素,对现代思想、文化、文学的变革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从在京、沪等城市出现,到在贵州山区落户,是一个由中心向边缘逐渐扩展的过程,看似很慢,意义却非同小可:历史变革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往往是要看它对边远地区的蔓延、渗透程度的。因此,1905年,贵州最早的铅印印刷厂遵义官书局创办;1908年,贵州最早的白话小说《越南亡国史》(未署名)在《自治学社杂志》创刊号发表;1913年10月,贵州第一部新剧作品《维新梦》(黄齐生等著)在贵阳达德学堂公演;1919年1月,新剧《人道引》(即《黑奴吁天录》)在贵阳公演;1919年3月,少年贵州会创办白话文报纸《少年贵州日报》,成为宣传科学、民主新思潮的重要阵258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地;1919年6、7月贵州报刊上出现了第一批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新小说……这样一些史实的发掘与考订,以及各专著所描述的:梁启超与贵州政治文化界的深远关系与影响(《散文史》);这一时期贵州的以“达德戏班子”为中心的新剧创作与演出,魏香庭的改革川剧(《戏剧史》);小说创作中的“文白并存”的格局(《小说史》);“古典诗歌向现代新诗转型的缓慢历程”(《诗歌史》)……都能够丰富与深化我们对世纪初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中国文学变革图景的认识。在这方面,似乎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研究空间,目前这样的偏于史的发展线索的梳理,还只是一个开始。
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年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外延与内涵的认识都有新的拓展。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汉民族文学中心”的破除,引入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叙述;“新文学中心”的破除,引入了曾作为新文学(新小说,新诗,话剧)对立面的通俗小说、旧体诗词、戏曲发展历史的叙述。对这样的变化也有朋友持不同意见,他们仍然坚持“现代文学”的研究应是“新文学”的研究。这里确实涉及对“现代文学”(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现代”(“20世纪”)它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是同时有某种质的规定性,这又同时引出了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范围……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确实重大,应充分展开讨论与争辩,同时也不忙作结论,持不同观点的朋友完全可以按自己的主张去进行研究,无须求统一。而且,在我看来,将少数民族文学、通俗文学、旧体诗词与戏曲引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叙述,这绝不是简单的拼盘式的“1+1”,它所引起的是研究格局的根本变化:不再是孤立的分别的研究,而是从“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新小说”与“通俗小说”,“新诗”与“旧体诗词”,“话剧”与“戏曲”……二者的既对立、竞争、制约,又相互渗透、影响的“关系”中去把握作为多民族文学的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20世纪小说史、诗歌史、戏剧史的生态发展,由此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文学史景观。———我曾在好几个场合与文章里,鼓吹这一设想;但我知道,真正实行起来,会有许多的困难,单是原始材料的发掘、梳理,就非一日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