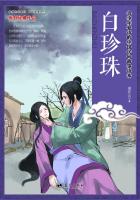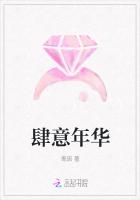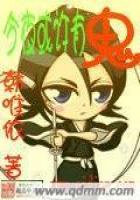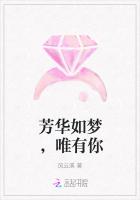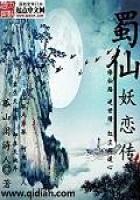现在,我在这套《书系》里却看到了这样的试验。与其说这是不谋而合,不如说是贵州文学的特点决定了作者必须打破原有的单一的文学史叙述格局。
如书系“总序”所说,“不论从现实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贵州都是多民族的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各民族文化之间既有差异,又有交融互相促进的令人大开眼界的文学史景观259一个多元体系”。另一方面,前文所提到的贵州文化的外来输入性的特点,又使它的文化中保留着不同时代、区域的文化的影响的痕迹。
这样一个多元的文化结构也许在贵州的戏剧中表现得尤为典型。据《贵州戏剧史》的作者王颖泰先生的研究,贵州戏剧计包括以下多种成分:土著民族的戏剧,如布衣戏、侗戏;流传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民间小戏,如傩戏和灯戏;汉民族的地方戏,如贵州花灯剧、黔剧(最初称文琴戏)、贵州梆子;此外,还有从外地流入贵州的古典戏剧(杂剧、传奇等)与地方戏曲(如京剧、川剧、评剧、越剧、豫剧、湘剧等),以及从海外传来的戏剧(话剧、歌剧、音乐剧、舞剑等)。
多剧种的并存,相互影响、渗透,又坚持各自的特色,充分地满足了生活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人民的多种艺术需求,同时也保留了极其丰富的戏剧遗产,这其中的艺术经验,是值得认真总结的。《贵州戏剧史》一书中,对侗戏《珠郎·娘美》有过专节的详尽、精到的分析。《珠郎·娘美》先是作为叙事歌与故事在侗族地区民间广泛流传,后由本民族作家于1921年(一说1910—1916年)改编成侗戏,由民间戏班在侗族聚居与汉、侗杂居地区用“双语(以侗语为主,杂用汉语)”演出,以后又传至省外,并在流传中进行加工、改造。据作者的研究,清代侗戏作家大多从汉族传书、戏曲中选材,而《珠郎.娘美》却是直接根据本民族民间叙事歌与故事改编,“这使侗戏文学真正成了反映侗族生活的新文体”,这本身就是有时代特色的。而在长期流传、不断改造的过程中,不但侗族自身的民族色彩越来越浓,而且从内容到戏剧形式都对汉族戏剧有所吸纳,研究者甚至认为其中也有五四新文化的某些影响。如作者在“绪言”中所说,目前已出版的一些戏剧史著,均未将少数民族的戏剧纳入研究视野;在我看来,《贵州戏剧史》(以及其他几部专著)的独特之处与贡献不仅在于特别关注民族戏剧(文学)的叙述,而且充分注意并展示不同民族戏剧(文学)的相互渗透、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在这方面,也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研究空间,本《书系》的研究只是一个开始。
《20世纪贵州诗歌史》的作者在“绪言”中,有一段论述也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在贵州)古典诗歌向现代新诗的转型经历了缓慢的历程,直到20年代中期才出现以蹇先艾为代表的新诗人,诞生了有规范化意义的新诗”,“由于新诗诞生的迟缓与发展的嫩稚,在前半个世纪的贵州新诗还不像在全国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取代旧体诗词成为主潮,而是新诗与旧体诗词并存,同步发展,这就是260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贵州诗歌创作的分流(现象)”。作者认为,这一现象说明“贵州边缘文化的地域环境,使贵州的诗歌创作与全国诗歌发展拉开了极为复杂的距离”。作者对贵州诗歌发展中的“新诗与旧体诗词并存,同步发展”的“分流”现象的概括,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但我认为,与其说这是一个弱点与不足,不如说这正是贵州诗歌发展道路的独特之处,而且从本书最后一章《旧体诗词谱新声》看,这一特点是保持到“新时期”的。这一“贵州现象”本身就是可以丰富与深化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图景的认识的(作者未能将“新诗与旧体诗词的同步发展”作为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可能是一个遗憾)。类似的现象,在我看来,也存在于戏剧领域:从《20世纪贵州戏剧史》的叙述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外来的话剧、歌剧等戏剧形式的引入,确实构成了20世纪贵州戏剧发展中的新的因素,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但在贵州普通观众中产生广泛影响,真正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的,还是民族戏剧与地方戏曲,而它们自身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革的。这就说明,如果我们戏剧历史的叙述仍然拘于话剧史的单一格局,将民族戏剧与地方戏曲排除在外,不仅是严重脱离戏剧实践,违背历史真实,而且也不利于戏剧的多元化的发展的。因此,像《20世纪贵州戏剧史》这样采取“戏剧思潮、话剧与歌剧、传统戏曲文学、民族戏地方戏”四条线索交织的复杂的叙述结构,是对现有研究格局的一个突破,对20世纪戏剧史的写作,以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都是有启示意义的。
2001年3月10日写毕于燕北园新的可能性与新的困惑261新的可能性与新的困惑———读1998年出版的几本现代文学史著作笔记(一)《中华文学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集体研究项目,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华艺出版社,1998年。
全书共十卷,可谓重量型文学史著作。我感兴趣的自然是五至七卷的“近现代文学编”,所描述的是“从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夕,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划分与这些年比较流行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十九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
的划分不同。这首先是显示了对这一段文学的一个总体把握与理解的:如“绪论”中所说,在作者看来,这是“一种转型期的文学”,是一个“绵延三千余年的古代文学体系,终于为崭新的现代文学体系所取代”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最后“基本完成”于40年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文学)”,“至此,近现代文学主潮与文学体系转型都统一到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学的总方向”。———这里的概括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作者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文学)体系”也就是“崭新的现代文学体系”,或者说,它为中国的文学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
模式;而这一模式,在作者看来,是具有“方向”的意义的:不仅是“主潮”,而且要“统一”整个文学的发展。作者的这一判断,以及背后的“历史发展的合目262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的”论与“必然趋势”论,大概会引起学术界不同评价;而我自己是并不赞同的,以后或有机会再作详尽的讨论。这里所要说的是,在“绪论”里所提出的上述关系全局的重大判断,却没有贯串全书以后各章的叙述,有的甚至还有抵牾。
这种不协调、不统一的现象,是集体写作难免的,我曾参与写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初版本也有过这样的问题;但因为前述论断关系到对这一百五十年文学的基本认识,如果仅仅提出而不与文学史的叙述结合,毕竟是一个较大的遗憾。
以“近现代文学编”命名本身,还显示了作者谨慎而稳健的学术姿态,这倒是我所赞同的。在我看来,文学史写作或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教科书式的———本书应属此类,本年度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山东本、广东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也都属于此类;另一类是表达学者对文学史的一种个人的观照的私人著作。前者着重于在知识的积淀与讲授中传递某种人文精神传统,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可接受性,同时又要体现一定时期的学术研究水平,也就是说它是以文学史教材的形式将已有的研究成果肯定下来,普及到初学者中。因此,它需要不断地修订;而每一次修订又必须是“渐变”式的,即所谓“移步不换形”:在未充分成熟之前,原有的文学史叙述框架一般不作大的根本性的变动,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具体文学流派、文学现象的描述上———这些部分应该是这类教科书式的文学史的主体,它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可靠的文学史事实,进一步的分析与概括应留给使用教科书的教师与学生;而这些分析与描述则应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严格的选择,体现前沿性与科学性、准确性的统一。这样不断地积累,积小变为大变,由量变到质变,时机成熟,整体结构、体系的变动就成为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结果。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6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唐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修订本:在保留(或部分保留)了唐本中老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又加入了本书编撰者及学术界的新的思考与探索,作了较多的变更,显示了近二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水平。
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与突破,同时如“本卷后记”中所说,又“提出众多新的课题与难点”:在这两个方面都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
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本书将现有的近、现代文学史研究纳入“中华文学通新的可能性与新的困惑263史”研究的总体结构中。如果说从本世纪20年代末开始,到50年代初基本完成的近、现代文学史研究独立体系的建立,是一个从古代文学史研究中分离出来的过程;现在到了世纪末又开始了一个将二者整合到一个大的历史叙述结构中的新的研究过程,这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显然,从“分离”到“整合”,并不只是外在的机械“合并”,而是意味着研究理路上的变化:如果“分离”的关注重心是近、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变革,以及随之带来的异质性;“整合”当然无须以否认、抹杀近、现代文学的新质为代价,但在新的叙述里,近、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历史联系将呈现于前景位置,这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近十年来,晚清文学与文化、学术思潮研究成为一个热点,正是要理清从古代文学向五四新文学转型的内在发展线索;本书第五卷“近代文学”即是吸收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而成为全书最引人注意的部分。相对而言,以后的“现代文学”部分虽在具体论述中也有所涉及,但却未能更清晰地突现出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传统的内在联系———我至今仍然记得王瑶先生所作的概括:这种联系是一个由隐到显,由不自觉到越来越自觉的过程;这正是需要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来加以更为精细的描述与展开的。纳入“中华文学通史”的大叙述,同时引起的应是现代文学史叙述内部组成与结构的大变动;这在下文将有进一步的讨论,这里所要谈的是,将近百年的文学置于“中华文学”的千年历史发展中来考察,所必然引起的对作家、作品的重新筛选与评价,这些年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事实上一直在进行中;而本书采取了既积极又谨慎的态度,比如在基本保留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传统位置之外,又突出了沈从文、艾青、赵树理、张恨水的文学史地位,这对今后的文学史叙述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我仍然觉得在作家、作品的筛选上,可以更加严格一些:现在进入史的叙述的作家、作品还是太多。由此而造成全书比例的严重失调:“古代文学”仅占四卷,“近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各占三卷,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过去有过“厚今薄古”的提倡,其效果并不好,我想今天在文学史的学术研究中似无继续贯彻的必要。
作为“中华文学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文学”卷“增添了以往现代文学史很少写到过的通俗文学、电影文学、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并且分别设立专章、专节”(见第六卷“后记”),这自然是最引人注目的。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叙述内容的简单增添与研究对象的扩大,264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而且意味着文学史观念的一个突破。其中最有意义的就是“新文学中心”的破除,引入了通俗文学的叙述;“汉民族文学中心”的破除,引入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叙述;以及“大陆文学中心”的破除,引入了台湾文学(本书将其作为“沦陷区文学”的一个部分)的叙述;而儿童文学、电影文学、民间文学等的引入,则是意味着“现代文学”概念的扩展。———当然,对这些引入与扩展学术界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的,这是关系着“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性质、对象、范围……的大问题,是需要通过严肃、认真的学术讨论与争鸣来解决的。在我看来,也不必一定要取得一致意见,可以按照各自不同的理解去写出不同的现代文学史。我自己是赞同这样的引入与扩大的,因此我认为《中华文学通史》近现代文学卷所跨出的这“第一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我更为关注的是这“第一步”所引发出的新问题。
首先是新引入的文学叙述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与相应的运用。我主要指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叙述。在第七卷二十四章第一节“满族文学”中,列入了端木蕻良、李辉英、舒群、马加、关沫南等一批满族出身的作家,但在具体论述中却看不出与满族文化(文学)有任何关系。这就给人一个印象,所谓“少数民族文学”就是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的创作,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其实据本书介绍,回族作家马宗融先生早在40年代即已指出,回族文学不应该仅仅是回族作家写出来的一般性作品,其创作中必须具备为本民族所特有的“独创风格”,包括“回族感情”和“回族独用的语言”等等文学基本因素。这当然适用于所有的少数民族文学。我想,即使不一定非要反映少数民族生活,风土人情,运用少数民族的特殊用语,至少应含有少数民族的情感与心理。记得朱光潜先生曾经说沈从文的寂寞中包含了少数民族的孤独感,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的某些著作也是可以视为少数民族文学的。———顺便说一句,尽管第七卷十五章列有“苗族作家沈从文”的标题,在具体描述中,却没有相应的分析,这也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