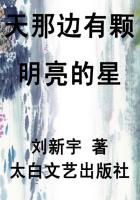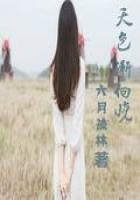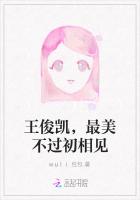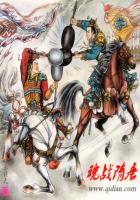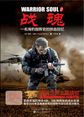但这样的批判性反思,也是存在着陷阱的。一是推向极端,就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二是批判的思想资源问题,如果将其单一化,也是非常危险的。这样就会导致对革命本身的全盘否定,和对革命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绝对肯定,那就会从一种意识形态专制走向另一种意识形态专制,从一种盲目性和奴化状态走向另一种盲目性和奴化状态。这正是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所发生过的真实的历史过程。因此,当我意识到历史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革命理想与精神在事实上被抛弃,并因此产生了严重后果,在这样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下,将革命理想、精神的合理内核从其历史的失误中剥离出来,抢救出来,使之成为新的批判性的精神资源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就是历史的需要,更是我内在生命的欲求。于是,“消灭一切人压迫人、奴役人、剥削人的现象”的彼岸理想,追求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对被压迫者、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注,和社会底层人民的血肉联系,对一切压迫、奴役、侵略的非正义行为的反抗,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博大情怀,坚强意志,等等,在自我生命的深处得到了新的激发。但同时,我又警惕于将革命理想化、美化,将革命异化造成的血污淡化,以至合法化的任何企图与倾向,坚持拒绝遗忘的批判立场。
这样的既坚守又批判的态度,在现实生活中常显得旗帜不够鲜明,“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就像鲁迅说的“蝙蝠”,有点“骑墙”的味道,要遭到各方面的批评和不满是当然的。而自己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也常陷入犹豫不决的困境。而这样的尴尬,又是复杂化选择必然带来的,改不了,也不想改了。其实任何人,任何历史研究都只能在一种有缺憾的价值状态中存在:这或许是一种我愿意接受的更为真实的存在。
最后,还要说一点:贺桂梅在和我的讨论中,还谈到了他们这一代个人和历史发生关联的方式问题,这就涉及到成长于革命年代的我们这一代学人,和后革命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学人之间的差别,对革命历史的不同立场、态度问题,这应该是饶有兴味的。贺桂梅说,“我们常常困居于个人的小小悲欢之中,如此容易忘记历史或感知不到历史。也就是说,历史是一个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去理解的对象”,我们的历史研究缺乏“强大的情感动力”,“越来越糟糕的一种状况是从知识到知识的‘纯学术’操作,研究者成了冷漠的‘剖尸员’和知识生产的程序管理员。我们缺少的恰恰是钱老师所说的‘血肉’。自然,这并非因为我们缺乏钱老师们作为漫长而酷烈的20世纪历史的亲历者的经验,我想更重要372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的是一种反观、思考并提升个人经验的习惯和能力”。
这里就形成了两代学人的不同的自我反省,带着不同的问题意识去反思革命历史,就会有不同的观察、感受,进而产生认识、评价上的某种差异:这都是很有意思的。如前所说,我们这一代面对的主要是革命的异化带来的社会灾难与精神毒害,我们要努力从中挣脱出来,因此,我们的反思必然是更带批判性的———这样的批判,不仅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我们这一代对革命的异化,特别是革命旗号下的专制在现实生活中的继续存在,是更为敏感的;而且在我们看来,革命之发生异化与革命理想、精神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是纠缠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尽管也试图从中抢救出合理的成分,但却认为这样的抢救是应以彻底的批判为前提的。而年青一代的许多朋友所敏感与反省的,却是他们所成长的时代对革命的全盘否定,革命理想与精神的缺失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自身的精神损伤,因此,他们希望唤回丧失了的革命理想、精神,包括在革命精神照耀下的治学道路与学术精神,希望从我们身上多少保留着的革命精神传统与革命时代的学术传统中吸取某些精神滋养。从这样的立场与态度出发,他们就认为,我们的批判性、自省性的反思,是不必要的,至少是过分的。———我很有兴趣地注意到了这样的差异和批评,不仅认为这是必然产生的,而且认为我们正可以从这样的差异与相互诘难中,获得教益。我就从这次座谈会中,一些年轻朋友的不同意见中得到启示,提醒自己在进行批判性反思时,一定要防止重犯“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的历史错误,更不可放弃自己的基本信念,背叛自己:那也是一种自我异化。
但我也想借此提醒年轻的朋友,也算是不同意见吧。我注意到,一些年轻朋友并不否认革命中的历史失误,但对他们来说,这只是理论上的承认,或文本上的材料,而不能进入具体的历史情境,因而缺乏切肤之痛,容易被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所迷惑———坦白地说,这些理论也曾迷惑过我自己,使我曾长期不能正视历史的血腥。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代价论”,即认为所有的失误,以至罪恶,都是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获得历史的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应该理解,以至忽略不计的。我在一篇文章里,对这样的高论有过这样的回应:你想过你所说的“必不可少的代价”,“意味着什么吗?这是成千上万的美好的生命的丧失,是无数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是幸存者永远不能平息的痛苦的记忆,是铭刻在整个民族心灵上的精神创伤啊。怎么能够以一个旁观者的冷如何回顾那段革命历史373静,如此轻松地谈论这样的所谓‘代价’呢?”(参看《面对21世纪:焦虑、困惑与挣扎》,收《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当然,我的这一回应,在政治家,特别是革命政治家看来,是小资产阶级的感伤主义、人道主义:在当年的革命时代我就受过这样的批判,我也曾努力地想克服,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原点,这或许也是我最终也没有改造好的一个证明吧。这也证实了洪子诚先生的一个自嘲:我们这批“30年代后”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充满了“小资情调”。
2007年12月27、28日重写374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史料的“独立准备”及其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说起来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创建我们这门学科的老一代学者,无论是王瑶先生,还是唐先生、李何林先生,从一开始就强调学术研究必须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关于史料的整理结集和审订考核工作,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的一代学者,如马良春先生、樊骏先生,以及今天到会的几位老先生,都为“现代史料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如人们所公认的,鲁迅的文献整理,无论是辑佚,还是校勘、版本,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成为我们今天的讨论的基础。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认识上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且不说至今还有人将史料工作视为“小儿科”,在职称评定中史料研究成果不予承认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就是在前几年,还有位著名的学者、作家公开扬言,现代文学作品不存在校勘的问题,并以此为理由否定学者所做的其作品的汇校本的意义与价值。不过,我们今天重提文献问题,也还有一个想把我们的认识再深入一步的意图。记得王瑶先生当年在谈到“要尊重历史事实,就必须对史料进行严格的鉴别”时,曾经指出,“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有一大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应有的重视罢了”(见《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因此,对传统的文献学的借鉴,今天仍是我们从事现代史料研究的一个基本功,这是毫无疑问的。
而我们要提出讨论的是,对现代文献的辑佚、整理与鉴别,有没有与古代文献不同的新问题,因而就有一个是否要建立一些新的规范,提出新的原则与方史料的“独立准备”及其他375法的问题。这也就是刘增杰先生在提交会议讨论的论文《〈师陀全集〉编校余墨》里所提出的“从传统方法到现代校勘的转型”的问题。我完全赞成刘先生的这一分析:“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文学作品的样式、传播方式、作者的写作手段都发生了变化,从而伴随着新的校勘任务,产生着新的校勘形态”,进而“推动着从传统校勘学向现代校勘学的转变;催促着人们通过对现代作家文本校勘的实践,总结出一些新的校勘原则与方法”。我想,这正是我们这个座谈会所要重点讨论的。我因为几乎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自然不能贡献什么意见;不过看了几位先生的文章,觉得他们的一些思考很有启发性。比如,刘增杰先生强调“期刊成为(现代)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这就使作品的校勘和传统的校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王风强调现代书写所出现的新问题对现代文献整理所提出的新课题,诸如“繁体字、异体字、俗体字以及方言字乃至于作者的生造字”
的处理,“标点符号和分段”问题的提出。王风说得很好:“对于现代文本,标点是先在的,本来就是文本的一个部分,因而其地位应该与文字是等同的,文字方面的校勘体例也应该贯彻到标点符号。至于分段就更是如此,(对于现代文本)分段是其最大的修辞。”刘增杰与解志熙都谈到“传统作品的校勘对象,多为已作古的作者的作品。现代文献的校勘对象,则大部分是活跃于文坛的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新的时代校勘(也包括辑佚———钱注)的要求已经不完全是从文字到文字,从书本到书本,校勘(辑佚)开始和社会调查、访问知情者等多项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并运用新的校勘(辑佚)手段,扩展着自己的活动空间”。这里所提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希望在这次座谈会以及以后的讨论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展开。我还注意到一点,以上问题都是这几位先生在他们的实践(编校《师陀全集》、《废名集》与《于赓虞诗文辑存》)基础上提升出来的;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先生在进行新文学文献的辑佚、整理工作,只是如解志熙所说,他们默默奉献成果,“却很少把他们的经验和工作方法写下来,所以新文学的文献工作迄今似乎仍限于自发的或自然的状态,顶多只是个别的师生间私相传授,而缺乏古典文献学那样被共同意识到的学术传统和被大家自觉遵守的工作路径,以至使有志于新文学文献研究的年轻学子们在今天难免暗中摸索之苦”。
我建议,我们这次座谈会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创议;更自觉地实践,更自觉地总结经验,以逐渐建立现代文学的文献研究的新原则、新方法、新规范、新传统。
这应该是建立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新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今天这样强调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规范问题,毋庸讳言,是有现实的针对性的,或者说,是表示了我们的一种忧虑的。这些年,现代文学作品的出版热持续不减,可以说各出版社争先恐后地出版各种现代文学作品的选本,现代作家的选集、文集,以至全集。这从一方面说,自然有助于现代文学作品的普及与研究,其中高质量的文集、全集也确实集中体现了现代文学的文献研究的学术成果,有的选本则体现了新的学术眼光,有一定的学术含量。但同时也应该正视其中的严重问题。这主要是粗制滥造与整理的混乱。有些文集、全集的遗漏(篇目遗漏与成句成段的遗漏),误收,误排,大面积的删节改动……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而任意的删节改动,尤其令人不安:连“学术研究的安全运转”(这是王风文章提出的一个概念)都成了问题。解志熙在他的文章里提出“精校,不改,少注”的原则,特别是“精校,不改”这两条,实在是切中时蔽的,而且是学术研究的可靠性的一个基本保证。解文提到的鲁迅在30年代所发出的警告,确有重温的必要:“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朝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改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病后杂谈之余·二》)。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今人乱出文集、全集而现代典籍亡,因为他们删改原文,且错误百出。”
我一直觉得20世纪90年代与新世纪初的中国,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有惊人的相似,这又是一例。历史的“重来”现象曾使鲁迅那一代人焦虑不安,我们今天也陷入了类似的困境。仔细想来,这两个时代在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受到商业化的冲击这一点上,也确有相似之处。错误百出的文集或全集,即是一种伪劣的文化商品,为降低成本与抓住商机,就将学术排除于文集与全集的编辑工作之外,以至出现了王风所说的“不知分辩‘校对’与‘校勘’,一股脑委之出版社校对科,卸责于‘手民’”,不承认“校比勘对,以定去取,本就是编者而非编辑的责任”这一基本常识的咄咄怪事。而删改原文则或出于政治的考虑,或隐含按“与时俱进”的原则“重塑前人形象”的动因。这也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它所折射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或许是使我们更为忧虑的。这自然不属于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范围。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对学术研究的常识与基本学术伦理的坚守与维护。我建议,这次座谈会是不是可以将“不删史料的“独立准备”及其他377改原文”作为文献整理工作的“第一原则”提出来,并呼吁“抵制现代文学作品整理与出版工作中的粗制滥造之风”,以免除现代文学典籍已经或还要继续遭遇的厄运。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实际上是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紧密相连的,这背后更有一个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发展的全局性的思考。现在很多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都在寻求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性与新的突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这次座谈会也是这样的寻求的一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