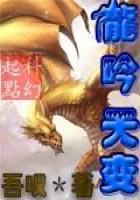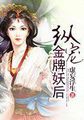这里,我想重提鲁迅的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经验与传统。大家知道,鲁迅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招来了许多非议和攻击。其中一条就是说他的这一著作是以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献概论讲话》“作蓝本”的,鲁迅则反驳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的独立的准备。”(《不是信》)学术研究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因此,后人参考前人的著作,对其使用的史料与观点有所吸取,都是必要与必然的;但参考却不是“作蓝本”,后者是“依葫芦画瓢”,是将他人的研究成果作重新组装,变的是表面的模样,骨子(无论是观点还是材料,以至结构)里却没有变,说难听点,就是变相的抄袭。可惜直至今日,还有许多学者以参考为名,行变相抄袭之实。当然,以某个可信的著作作为蓝本来编写讲义,是可以的,许多教师也是这么做的,其主要功能是传授知识;但这样的讲义只能发给学生作参考,不能作为独立的学术著作。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某个“抄袭事件”,我估计就是将讲义当学术著作出版,又没有说明出处,自然就被抓住了。也还有另一种情况,材料是别人用过的,或人们所熟知的,但用新的观念重新照亮,作新的阐释。对这样的著作,恐怕要作具体的分析。有的新观念并不是自己的,或经过自己真正消化的,不过是搬用时髦的理论,来重新组合现成的材料,以论证新理论的有效性,而对研究对象没有任何新的发现,说得不好听一点,这是玩魔方,而并非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其价值是可疑的。但有的作者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与方法,独特的眼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因而对研究对象有新的感悟、理解和阐释,有自己的发现与真知灼见,这样的著作是有价值的,有的还有相当高的价值。
但我自己更倾慕鲁迅有自己“独立的准备”的治学之路:不仅有理论的独立准备,也有史料的独立准备。他在写作《中国小说史略》之前,就作了辑录《古小说钩沉》的工作,为准备《中国小说史》的写作,又辑录了史料集《小说旧闻抄》,编选了《唐宋传奇集》。在《〈中国小说旧闻抄〉再版序言》里,他这样描述自己作史料的“独立准备”的辛苦与欢乐:“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可以看出,鲁迅所谓的史料的独立准备,是包括两个方面的,既有辑佚(新史料的发掘、搜寻)———在他看来,唯有不断发掘新史料,才能去“凭心逞臆”之弊;又有选定版本、校勘、辨伪这样的整理工作———在他看来,唯有“辄加审正,黜其伪欺”,才能“求信”(参看鲁迅:《〈小说旧闻抄〉再版序言》、《〈唐宋传奇集〉序例》)。对于鲁迅,这样的史料的独立准备,是新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他曾经说过:“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而历史的遮蔽与涂饰的主要表现,就是观念、意识形态的遮蔽所导致的历史事实的遮蔽。因此,如果我们想冲破重重涂饰“示人本相”,就必须从被遮蔽、掩埋的历史史实的重新发掘开始。鲁迅在回答如何“着手”时,谈到了他的计划,就是“先从作长编入手”
(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书)。当然,鲁迅也说过,“文学史资料长编”并不是“文学史”,但他同时又强调,这样的资料长编,“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1932年8月14日致台静农)。鲁迅是强调“史识”与“史料”的统一的,史料需要史识的照亮,但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却是研究“入手”的基础。固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治史者都是史料专家,但对于文学史研究者,重要的研究课题,自己动手作史料的“独立准备”,是完全必要的。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老师们就是这样培养我们的:我在读研究生时,为研究路翎就先编他的《著作年表》,从笔名的鉴别,著作(包括佚文)的发掘入手。后来写《周作人传》,首先做的就是编了30万字的《周作人年谱长编》,并进行逐年的作品、思想发展的概括与分析,写了10万字左右的笔记,还对周作人与其同代人的关系作了史料的考释与整理,约10万字(文收《周作人论》)。最后写出来的《周作人传》有40万字,史料的准备也有50多万字。我当时给自己定的写作目标,除了要真实地写出我对于周作人及那一代人的认识与生命感受外,史料的“独立准备”及其他379就是史料要翔实,并尽量求全即将当时条件下可能搜集的材料全都收入,以为后来者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现在看来,《周作人传》这本书至今还没有被人们忘记,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是这本书的写作是有自己的“独立准备”,首先是史料的独立准备的。坦白地说,以后的写作,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我来说,写得太快是一个主要原因)在史料上就没有像《周作人传》这样下工夫,但仍然坚持了这一条:每写一部重要著作,一定从史料的独立准备入手。而且据我的体会,随着学术眼光、思路的变化,必然有一批新的史料进入研究视野;而随着史料发掘的深入,新的学术思想与方法也得到了深化,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良性的互动过程。我自觉追求的研究的新意与创造活力,正是有赖于这样的新的学术眼光,以及被激活的新的史料,从《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到《1948:天地玄黄》无不如此。近年来当我把注意力转向被遮蔽以至被强迫遗忘的历史的研究———例如我正在进行的“1957年学”的研究,以及准备多年的“文革”史的研究———时,史料的发掘更是成了第一位的工作,某种程度上这是在进行史料的抢救,因此,每一条史料的发掘背后几乎都有一个故事,这也是一部历史,充满血和泪,联结着人的活的生命。
这就说到了另一个我以为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人们通常把史料看作是“死”东西,把史料的发掘与整理看作是一个多少有些枯燥乏味的技术性的工作,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史料本身是一个个活的生命存在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迹,因此,所谓“辑佚”,就是对遗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的创造者人的生命)的一种寻找与激活,使其和今人相遇与对话;而文献学所要处理的版本、目录、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上的人的一种书写活动与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学)生产与流通的体制与运作方式,如几位先生在其文章中所提到的“从手稿写定到报刊发表再到结集印行”的过程,作家对作品的不断修改所造成的“文本的不确定性”,严厉的审查制度与“钻文网”
的策略所造成的版本的复杂性,“繁体字、异体字、俗体字、方言用字乃至作者的生造字”的运用与变动,标点的运用与变动等等,无不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生命内容。而对史料的认识、处理,更是关涉到研究者的历史观、文学史观。当年鲁迅如此强调野史、笔记里的史料价值(鲁迅的这一认识已被今天的学者普遍认同),显然是他的重视非正统的边缘文化、反抗正统文化的文化观、380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历史观的反映。刘增杰先生在其文章中也谈到了文学观的问题:“将笔记、日记、书信、未刊稿收入全集,不仅面临着资料搜求问题,更涉及到编者文学观的转变,不断提高对上述史料重要性的认识。”李书磊的文章谈到“普通人的笔记本对研究当代文化史的意义”,强调“作为(意识形态信息)的接受者的芸芸众生是社会的主体人群,他们尽管不是文化的主导力量却是社会文化的主要载体,任何文化蓝图、观念意识要想获得实现是绕不开他们的,他们的思想与精神才呈现为社会文化的现实”。在我看来,这也是表达了一种新的文化史观的。
实际上,我们今天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作为一个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来,不仅是着眼于学科的基础建设,也不仅是对学术商业化所带来的学风的危机的一种抵抗与坚守,强调学术研究的科学性,重新提倡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的鲁迅学术传统,同时也是包含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即把现代文学的文本还原到历史中,还原到书写、发表、传播、结集、出版、典藏、整理的不断变动的过程中,去把握文学生产与流通的历史性及其与时代政治、思想、文化的复杂关系。这或许可以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同行在探讨学科发展的新路时的一个参考意见吧。
2003年12月20日发言,2004年2月9—11日整理、补充学术研究的承担问题381学术研究的承担问题———和北大研究生的一次谈话大家都是学院中人,因此,今天我要谈我所理解的学院研究,在我看来,应该有三承担。
首先是自我承担。费孝通先生曾将他和他的老师潘光旦先生作了一个比较,并说了一句很好的话:“我们(费孝通)这一代,比较看重别人怎么评价自己,而老师看重的是对不对得起自己。”搞学术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自己要对得起自己,你的自我生命能不能在学术研究中得到创造、更新,是否有意义、有价值。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评价自己,更应该不断追问的,是学术研究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它是外在于我的生命的还是内在于我的生命的?能不能在学术中得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是更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今天提出来,是有着它的特殊意义的。我们不必回避,学术也可以是一种谋生手段,毕竟像鲁迅所说,第一是生存,第二是温饱,第三才是发展。在我们的现行体制下,在你成为副教授之前,谋生是主要的。我要提的问题,是在生存、温饱基本解决“以后”,用我们通常的说法,就是达到小康,做到了衣食无虞“以后”,我们应该作怎样的选择?
这是当下中国大学里大多数教师、学者都面临的选择,因为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大学教师、学者的生活状态,也包括研究生的生活,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已经不是我们读研究生时的80年代初、中期那样,“搞导弹的不如买鸡蛋的”,而是完全倒过来,而且二者的距离越来越大了。也就是说,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甚至是高于国民平均水平的生活和研究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进一步追求什么?你的学术研究对于你意382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味着什么?
应该说,现在依然有许多大学教师、学者将学术研究作为谋生的手段,不过,现在的“谋生”要求就更高了,已经不是“一间屋,一本书,一杯茶”(这是我们80年代的奋斗目标),而是几套房子,豪华享受了。在为数不少的人那里,学术是一个谋取更大更高更多的名和利的工具。这就是我经常所说的,这些人开始的时候,下了一点苦工夫作学术研究,因此也获得了一些学术成绩与相应的学术地位,于是就利用这些学术老本,最大限度地获取最大的利益:政治、经济、学术的利益。这样的学术研究的最大利益化,学者自身也利益化、功利化了,整天混迹于官场、商场、娱乐场与名利场,不仅成了鲁迅说的“无文的文人”,更成了“无学的学者”。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学者”这样的选择,是得到现行体制支持,甚至是鼓励的:只要你听话,一切都向你开放,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而且已经制度化了。这就是我在好多场合下,都谈到的“新的科举制度”。总之,就是“请君入瓮”,或者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就有了被体制收编的危险。本来,名利之心,人皆有之,只要是以诚实的劳动(包括学术劳动)去获取名和利,追求生活的享受,这都无可厚非。问题是,这背后有一个陷阱,体制设置的陷阱,当你将获取名和利,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唯一动力,最高目标,而且这样的追逐名、利的欲望不加节制,你就必然地被体制收编,最后,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你就是“学官”、“学商”、“学霸”(学术权力的垄断者),而不是“学者”了。这时候,你什么都有了:名有了(数不清的头衔),钱有了(数不清的灰色收入),更有了势力(数不清的门徒,哥儿们),但就是没有自己了:完全走到自己当初追求的反面了。这时候,你看重的,就是“别人(官员,“学术界”)怎么看你”,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你的地位、利益,而不再考虑是不是“对得起自己”
了。前不久曾引起轰动的那位人大教授,因为别人对自己的学术提出批评而失态,其潜在心理,就是太看重“别人怎么看自己”,于是就作出了“对不起自己”
的蠢事。这其实是当下大学教育界、学术界追名逐利,以至竞相被收编之风的一个变态表现。
我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学术研究对我们自身生命的意义”的问题。这是另一种选择,当我们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就应该淡泊名利,追求简单的物质生活,丰盈的精神生活,回到人的本性上来———人在本质上还是精神的学术研究的承担问题383动物。作为学者,就要回到学术本来的意义上来。学术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劳动,它的意义与价值———无论是社会意义和价值,还是对学者自身的意义和价值,都是精神层面的。关于社会意义和价值,我在下面还要谈,这里要说的,是我们自己能不能从学术研究中得到生命的快乐、意义和价值?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关于劳动的说法:这个劳动是外在于你的,还是内在于你的?是否定你自己,还是肯定你自己?是使你感到不幸,还是幸福?你的精神力量是不能发挥的,还是自由自在的?马克思把前一种劳动称为“异化劳动”,后一种是“自由劳动”。在我看来,在我们具有了基本的生存和学术研究的条件以后,就应该从名缰利锁中解脱出来,使我们的学术劳动成为一种自由劳动,成为我们内在生命、精神发展的需要。
以上所说,都是讨论学院里的老师、学者的选择。诸位还是研究生,充其量还是“未来的学者”。因此,我讲的这些,你们可能觉得有些隔。但我不认为与你们无关,这关系着你们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要选择学术研究作为你们的职业和事业。以前每有学生想考我的研究生,我总是对他们说,你们如果是为了找一个饭碗,最好不要来考研究生,因为如果仅仅是为了物质生活的需求,路子很多。研究生是最苦的工作,很多工作比这好赚钱得多。所以我说,只要你有碗饭吃,就别来考研。说实话,做任何工作,都是有所失,也有所得的。学术研究———当然,我讲的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他要付出的代价,就是生活总是相对清贫的,或者说,和你付出的劳动,不相匹配,一天到晚爬格子,耗尽了脑汁,所得到的稿费,是有限的,根本不能和普通的白领相比。这就是学术研究的“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