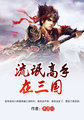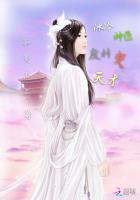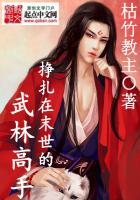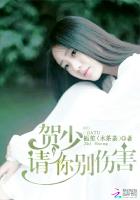李元吉不但经常“打仗”、打死人,还特别喜欢打猎。他用来捕捉鸟兽的网就有三十车,拥有这么多网的人应该算得上是大唐“网民”一族了。那么多捕网,对生态的破坏不容忽视,估计那些鸟儿早就将他这个“鸟人”列入黑名单了。这位酷爱打猎的专业“三打”皇子在“打猎界”有句名言:“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
不知道他这句话是否涉嫌抄袭汉武帝的“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这句更名的名言。打猎在那时候和现在打高尔夫一样,是上层贵族的休闲运动。可这位上层人士在打猎的时候总是不分场地,经常毁坏农民伯伯的庄稼,史载其“常与诞游猎,蹂践人禾稼”。“诞”指的是他的姐夫窦诞。窦诞因为“尚帝女襄阳公主”而成为大唐驸马(友情提醒:这里的“尚”是表示公主屈尊“下嫁”,凡臣下娶皇帝的女儿都称“尚公主”,“尚公主”并不是指姓尚的公主哦)。
其实,“蹂践人禾稼”这种损坏公私财物罪,对花花公子李元吉来说,大概算是最不值得一提的小意思了,他还有许多让人毛骨悚然的爱好,拿活人当移动靶就是他的业余爱好之一。和宇文化及喜欢在大街上急速跑马不同,李元吉喜欢在大街上“当衢射人”。具体内容是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找一个看着顺眼或不顺眼的人,拿出弓箭对着他便射,射中了,算那个被射者倒霉,医药费自理。当然,要是那些被射的“活靶子”比较机灵,对着箭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后再来个“我躲、我躲、我躲躲”的话,那就是最完美的了。因为这个变态的李皇子“当衢射人”的目的就是“观人避箭以为笑乐”。幸亏那时候没有冲锋枪,否则的话,他肯定会迷上“观其避弹”的,如此,则所有“避弹”者都会无一幸免地完蛋的。
“避箭”游戏是“蝗子”李元吉白天玩的室外节目,每到夜晚,他还有更禽兽不如的室内活动:“宣淫他室”。他带着一帮亲信卫兵,直接闯进任何一户民宅,对自己看中的任何一个女人任意实施奸淫。一座偌大的太原城被一个年少的首长弄得“百姓愤怨”。就是这样一个始终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歹毒恶男,后来竟也曾觊觎大唐皇帝的宝座。在他的两个哥哥,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为皇位明争暗斗时,他积极煽风点火,希望大哥干掉二哥,然后他这个三弟再“做掉”大哥,夺取天下。他曾经野心勃勃地对自己的手下心腹放言:“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在他的眼里,只要没有了文武双全、足智多谋的二哥李世民,放倒老实巴交的太子大哥李建成只是小菜一碟。从这个方面看,真的要感谢李世民果断发动了“玄武门事变”,倘若真是让这么一个恶少登上皇位,那唐朝多半要和隋朝一样,要出一个“李二世”的。
真是令人费解,和李元吉很含糊的二哥李世民相比,这兄弟俩好似是河豚和海豚,名字差不多,形状差不离,但本质差太大,河豚的内脏之毒见血封喉,而海豚却温顺聪明,让人感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同样是一母所生的弟兄,做人的差别咋就这么大哩!
在太原任意胡为的李元吉如果有窦诞和宇文歆的尽职尽责的辅佐、提醒和监督,应该是有所收敛的,但窦诞这个姐夫当得太不称职了,他不教舅老爷学好,反而纵容他耍坏,在这个问题上说他助纣为虐也不算过分。事实证明,李渊找女婿“辅佐”儿子的行为是继重用李元吉之错后的错上加错。因为窦诞对李元吉的任何丧尽天良的行为都不加以规劝和制止,和另一个辅臣宇文歆的忧心力谏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屡谏屡被拒的情况下,极富正义感的宇文歆向李渊打报告“表言其状”,就是将这位皇子的种种恶行写成内参,上报到他爹地李渊那里。李渊见孺子如此不可教,生气地下令将李元吉撤职罢官。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也能算得上是李渊“大义灭亲”,做出了个英明决定,给了个圆满结果。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小儿子问题上错一错二的老子李渊又做出了一个错三的决定,在免去李元吉并州(太原古称)总管职务后仅二十天,又将其官复原职。
对于李渊这一朝令夕改的任命,史书上给出的理由说是因为太原城许多民众亲自到长安请愿,要求将李元吉李领导继续留在太原,列出的理由无非是“太原的发展不能没有李大人”、“没有李大人,我们白天吃饭吃不下、晚上困觉困不着”一类。当然啦,这些和现在的“万民伞事件”异曲同工的群体请愿事件都是李元吉自导自演的,真实情况应该是,要知道这种人离开,太原人民一定会像送瘟神那样,敲锣打鼓地送行的。
最后,李渊在“广大群众”的一致请求和强烈要求下,再次任命李元吉主政太原。很显然,李渊的这一决定是有自己的意图的,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太原的丑恶行径,但他却明知故犯,使李元吉这个“李霸天”又回去了。究其深层次原因,是李渊对别人的不放心。因为太原对他本人乃至整个大唐都太重要了,他不愿意把这样一个对国家举足轻重的城池交给外姓人防守,他太担心别人依城割据,陷落太原了。
可是,越怕失去就有可能越快失去。正是他的这一没有原则的愚蠢任命最终导致了太原的失守。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三月底,就在李元吉官复原职一周后,盘踞在太原以北马邑郡(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率军向太原发起了攻击。刘武周自两年前杀掉了自己的老上级王仁恭自立后,就抱紧了突厥的大腿,跟突厥穿上了同一条裤子。他早就垂涎太原,爱上太原已经不是两三天了。但由于李渊工作做得很到位,和突厥的外交关系很铁很把,所以刘武周一直不敢染指太原,只能望着太原吞口水。然而,随着李渊建唐和唐军相继剿灭了薛举父子和李轨后,突厥对唐朝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
隋末中原大乱以后,以前年年向隋朝进贡的东突厥突然间“身份置换”,玩了个“6”字倒立,一路六六大顺变成了顶天的“9”字,不但不用再向隋朝送钱送物,反而有许多隋朝割据大员争着抢着为他的衣食住行买单,连美女这类突厥十分稀缺的“床上用品”都源源不断地送往北方。在被巨大的幸福感晕眩了一段时间后,突厥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自己永远当爷,就不能让隔壁的隋朝有爹出现,只有让他们永远停留在长不大的儿子、孙子阶段,最好的状态是一窝小侏儒,这样,凭着人高马大,自己就可以永远在一群小矮人中间游刃有余。所以,当马邑的刘武周、朔方的梁师都、榆林的严子和等新生婴儿政权请求成为突厥的加盟商时,突厥不但满口应承,还批发给他们“定杨天子”“解事天子”“屋利设”(“设”是突厥对别部主管军事首领的称谓,类似于汉政权的亲王)等荣誉称号。
那时候,向突厥递投名状、拜门槛好像是一种很流行的政治行为,无论是中原还是北方的割据军事集团,都主动向与隋朝搭界的东突厥称臣或妥协,薛举、窦建德、李轨、高开道、王世充等人都先后称臣于突厥。和突厥地皮相接的李渊也不例外,他虽然不提“称臣”二字,但也是大打擦边球,和突厥签订了一系列“友好条约”。太原起兵时,为了保证后院安全,他向突厥承诺了西征长安过程中的战利品分成,“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征发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按照这个劳务合同分成,基本上是动产归突厥,不动产属李渊,突厥捡了个大便宜。也正是如此,突厥始毕可汗才信守合同,大力支持自己的民族兄弟李渊西争天下,因为李渊走得越远,他得到的利益分成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