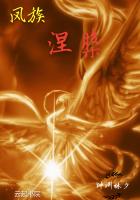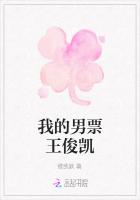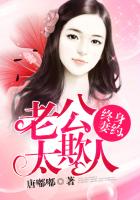格物致知之说,王心斋(艮)最优。心斋为阳明弟子(心斋初为盐场灶丁,略语《四书》,制古衣冠、大带、笏板服之,曰:“言尧之言、行尧之行,而不服尧之服,可乎哉?”闻其论曰:“此绝类王巡抚之谈学也。”时阳明巡抚江西,心斋即往谒,古服举笏立于中门,阳明出迎于门外。始入,据上坐;辩难久之,心折,移坐于侧;论毕,下拜称弟子。明日复见,告之悔,复上坐,辩难久之,乃大服,卒为弟子。本名银,阳明为改为艮),读书不多,反能以经解经,义较明白。谓《大学》有“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语:致知者,知事有终始也;格物者,知物有本末也。格物致知,原空文,不必强为穿凿。是故诚意是始,平天下是终;诚意是本,平天下是末。知此即致知矣。刘蕺山(宗周)等崇其说,称之曰:“淮南格物论,谓是致知格物之定论。”盖阳明读书多,不免拖沓;心斋读书少(心斋入国子监,司业问:“治何经?”曰:“我治总经。”又作《大成歌》,亦有寻孔、颜乐处之意,有句云:“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故能直截了当,斩除葛藤也。心斋解“在止于至善”,谓身名俱泰,乃为至善;杀身成仁,便非至善。其语有似老子。而弟子颜山农(钧)、何心隐辈,猖狂无度,自取戮辱之祸,乃与师说相反。清人反对王学,即以此故。颜山农颇似游侠,后生来见,必先享以三拳,能受,乃可为弟子。心隐本名梁汝元,从山农时,亦曾受三拳,而终不服,知山农狎妓,乃伺门外,山农出,以三拳报之。此诚非名教所能羁络矣。山农笃老而下狱遣戍,心隐卒为张江陵所杀(江陵为司业,心隐问曰:“公居太学,知《大学》道乎?”江陵目摄之,曰:“尔意时时欲飞,却飞不起。”江陵去,心隐曰:“是夫异日必当国,必杀我。”时政由严氏,而世宗幸方士蓝道行,心隐侦知嵩有揭帖,嘱道行假乩神降语:“今日当有一奸臣言事。”帝迟之,而嵩揭帖至,由此疑嵩。御史邹应龙避雨内侍家,侦知其事,因抗疏极论嵩父子不法,严氏遂败,江陵当国,以心隐术足以去宰相,为之心动,卒捕心隐下狱死),盖王学末流于颜何辈而使人怖畏矣。
阳明破宸濠,弟子邹东廓(守益)助之,而欧阳南野(德)、聂双江(豹)辈,则无事功可见。双江主兵部,《明史》赞之曰:“豹也碌碌,弥不足观。”盖皆明心见性,持位保宠,不以政事为意。湛甘泉为南京吏部尚书亦然。罗念庵(洪先)辞官后,入山习静,日以晏坐为事,谓“理学家辟佛乃门面语。周濂溪何尝辟佛哉?”阳明再传弟子万思默(廷言)、王塘南(槐时)、胡正甫(直)、邓定宇(以赞)官位非卑,亦无事功可见。思默语不甚奇,日以晏坐为乐。塘南初曾学佛,亦事晏坐,然所见皆高于阳明。塘南以为一念不动,而念念相续,此即生生之机不可断之意(一念不动,念念相续,即释家所谓阿赖耶识,释家欲传阿赖耶以成涅槃,而王学不然,故仅至四禅四空地)。思默自云静坐之功,若思若无思,则与佛法中非想非非想契合,即四空天中之非想非非想天耳。定宇语王龙溪(畿)曰:“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圣人也不做他。”张阳和(元忭)谓此言骇听。定宇曰:“毕竟天地也多动了一下,此是不向如来行处行手段。”正甫谓天地万物,皆由心造,独契释氏旨趣。前此,理学家谓天地万物与我同体,语涉含混,不知天地万物与我,孰为宾主。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亦然,皆不及正甫之明白了当。梨洲驳之,反为支离矣。甘泉与阳明并称。甘泉好谈体认天理。人有不成寐者,问于甘泉。甘泉曰:“君恐未能体认天理耳。”阳明讥甘泉务外,甘泉不服,谓心体万物而无遗,何外之有?后两派并传至许敬庵(孚远),再传而为刘蕺山(宗周)。蕺山绍甘泉之绪,而不甚心服。三传而为黄梨洲(宗羲)。梨洲余姚人,蕺山山阴人。梨洲服膺阳明而不甚以蕺山为然,盖犹存乡土之见。蕺山以常惺惺为教。常惺惺者,无昏愦时之谓也,语本禅宗,非儒家所有。又蕺山所以不同于阳明者,自阳明之徒王心斋以致知为空文,与心意二者无关,而心意之别未明也。心斋之徒王一庵(栋)以为意乃心之主宰(即佛法意根),于是意与心始别。蕺山取之,谓诚意者,诚其意根,此为阳明不同者也。然蕺山此语,与《大学》不合。《大学》语语平实,不外修己治人。明儒强以明心见性之语附会,失之远矣。诚其意根者,即堕入数论之神我,意根愈诚,则我见愈深也。余谓《中庸》“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二语甚确。盖诚即迷信之谓。迷信自己为有,迷信世界万物为有,均迷信也。诚之为言,无异佛法所称无明。信我至于极端,则执一切为实有。无无明则无物,故曰不诚无物。《中庸》此言,实与释氏之旨符合。惟下文足一句曰“是故,君子诚之为贵”,即与释氏大相径庭。盖《中庸》之言,比于婆罗门教,所谓“参天地、赞化育”者,是其极致,乃入摩醯首罗天王一流也。儒释不同之处在此,儒家虽采佛法,而不肯放弃政治社会者亦在此。若全依释氏,必至超出时间,与中土素重世间法者违反,是故明心见性之儒,谓之为禅,未尝不可。惟此所谓禅,乃曰禅八定,佛家与外道共有之禅,不肯打破意根者也。昔欧阳永叔谓“孔子罕言性,性非圣人所重”,此言甚是。儒者若但求修己治人,不务谈天说性,则譬之食肉不食马肝,亦未为不知味也。
儒者修己之道,《儒行》言之甚详,《论语》亦有之,曰“行己有耻”,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修己之大端,不过尔尔。范文正开宋学之端,不务明心见性而专尚气节,首斥冯道之贪恋。《新五代史》之语,永叔袭文正耳。其后学者渐失其宗旨,以气节为傲慢而不足尚也,故群以极深研几为务。于是风气一变。国势之弱,职此之由。宋之亡,降臣甚多,其明证也。明人之视气节,较宋人为重。亭林虽诮明心见性之儒,然入清不仕,布衣终身,信可为百世师表。夫不贵气节,渐至一国人民都无豪迈之气,奄奄苟活,其亡岂可救哉?清代理学家甚多,然在官者不可以理学论。汤斌、杨名时、陆陇其辈,江郑堂《宋学渊源记》所不收,其意良是。何者?炎黄之胄,服官异族,大节已亏,尚得以理学称哉?若在野而走入王派者,则有李二曲(颙)、黄梨洲(宗羲)。其反对王派者,今举顾亭林、王船山(夫之)、陆桴亭、颜习斋、戴东原五家论之。此五家皆与王派无关,而又非拘牵朱派者也。梨洲、二曲虽同祖阳明,而学不甚同。梨洲议论精致,修养不足;二曲教以悔过为始基,以静坐为入手,李天生(因笃,陆派也)之友欲从二曲学,中途折回,天生问故,曰:“人谓二曲王学之徒也。”二曲闻之叹曰:“某岂王学乎哉!”盖二曲虽静坐观心,然其经济之志,未曾放弃。其徒王心敬(尔缉),即以讲求区田著称。此其所以自异于王学也。梨洲弟子万季野(斯同)治史学,查初白(慎行)为诗人,并不传其理学。后来全谢山(祖望)亦治史学,而于理学独推重慈湖,盖有乡土之见焉。
阳明末流,一味猖狂,故清初儒者皆不愿以王派自居。顾亭林首以明心见性为诟病。亭林之学,与宋儒永嘉派不甚同,论其大旨,亦以修己治人为归。亭林研治经史最深,又讲音韵、地理之学,清人推为汉学之祖。其实,后之为汉学者仅推广其《音学五书》以讲小学耳。其学之大体,则未有步趋者也。惟汪容甫(中)颇有绍述之意,而日力未及。观容甫《述学》,但考大体,不及琐碎,此即亭林矩矱。然亭林之学,枝叶蔚为大国而根本不传者,亦因种族之间,言议违禁,故为人所忌耳。(《四库提要》称其音韵之学,而斥经世之学为迂阔,其意可知。)种族之见,亭林胜于梨洲。梨洲曾奉鲁王命乞师日本,后遂无闻焉,亭林则始终不渝。今通行之《日知录》,本潘次耕(耒)所刻,其中胡字、虏字,或改作外国,或改作异域,我朝二字,亦被窜易。《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仅存其目。近人发现雍正时抄本,始见其文,约二千余言。大旨谓孔子云:“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此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非谓臣事之也。又言,管仲大节有亏而孔子许之者,以管仲攘夷,过小而功大耳。以君臣之义,较夷夏之防,则君臣之义轻,夷夏之防重,孔子所以亟称之也。又《胡服》一条,刻本并去其目。忌讳之深如此,所以其学不传。亭林于夷夏之防,不仅腾为口说,且欲实行其志,一生奔驰南北,不遑宁居,到处开垦,隐结贤豪,凡为此故也。山东、陕西、山西等处,皆有其屯垦之迹。观其意,殆欲于此作发展计。汉末田子泰(或作田子春,名畴),躬耕徐无山(今河北玉田县),百姓归之者五千余家,子泰为定法律、制礼仪、兴学校,众皆便之。乌丸、鲜卑并遣译致贡。常忿乌丸贼杀冠盖,有欲讨之意,而曹操北征,子泰为向导,遂大斩获,追奔逐北。使当时无曹操,则子泰必亲自攘夷矣。亭林之意,殆亦犹是。船山反对王学,宗旨与横渠相近,曾为《正蒙》作注。盖当时王学猖狂,若以程朱之学矫之,反滋纠纷,惟横渠之重礼教乃足以惩之。船山之书,自说经外,只有抄本,得之者,什袭珍藏。故《黄书》流传甚广,而免于禁网也。船山论夷夏之防,较亭林更为透彻,以为六朝国势不如北魏远甚。中间又屡革命,而能支持三百年之久者,以南朝有其自立精神故也。南宋不及百六十年,未经革命,而亡于异族,即由无自立精神故也。此说最中肯綮,然有鉴于南宋之亡,而谓封建籓镇,可以抵抗外侮,此则稍为迂阔。特与六朝人主封建者异趣:六朝人偏重王室,其意不过封建亲戚以为籓屏而已;船山之主封建,乃从诸夏夷狄着想,不论同姓异姓,但以抵抗外侮为主,此其目光远大处也。要之,船山之学,以政治为主,其理学亦不过修己治人之术,谓之骈枝可也。
陆桴亭《思辨录》,亦无过修己治人之语,而气魄较小。其论农田水利,亦尚有用。顾足迹未出江苏一省,故其说但就江苏立论,恐不足以致远。
北方之学者,颜(习斋)、李(刚主)、王(昆绳)、刘(继庄)并称,而李行辈略后,习斋之意,以为程、朱、陆、王都无甚用处,于是首举《周礼》乡三物以为教。谓《大学》格物之物,即乡三物之物。其学颇见切实。盖亭林、船山但论社会政治,却未及个人体育。不讲体育,不能自理其身,虽有经世之学,亦无可施。习斋有见于此,于礼、乐、射、御、书、数中,特重射、御,身能盘马弯弓,抽矢命中,虽无反抗清室之语,而微意则可见也。昆绳、刚主,亦是习斋一流,惟主张井田,未免迂腐。继庄精舆地之学。《读史方舆纪要》之作,继庄周游四方,观察形势;顾景范考索典籍,援古证今,二人联作,乃能成此巨著。此后徐乾学修《一统志》,开馆洞庭山,招继庄纂修。继庄首言郡县宜记经纬度,故《一统志》每府必记北极测地若干度。此事今虽习见,在当时实为创获。
大概亭林、船山,才兼文武。桴亭近文,习斋近武,桴亭可使为地方官,如省长之属;习斋可使为卫戍司令。二人之才不同,各有偏至。要皆专务修己治人,无明心见性之谈也。
东原不甘以上列诸儒为限,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其大旨有二:一者,以为程、朱、陆、王均近禅,与儒异趣;一者,以为宋儒以理杀人,甚于以法杀人。盖雍乾间,文字之狱,牵累无辜,于法无可杀之道,则假借理学以杀之。东原有感于此,而不敢正言,故发愤为此说耳。至其目程、朱、陆、王均近禅,未免太过。象山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乃扫除文字障之谓,不只谓之近禅。至其驳斥以意见为理,及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之说,只可以攻宋儒,不足以攻明儒。阳明谓理不在心外,则非如有物焉,凑拍附着于气之谓也。罗整庵(钦顺)作《困知记》,与阳明力争理气之说,谓宋人以为理之外有气,理善,气有善有不善。夫天生物,惟气而已,人心亦气耳。以谓理者,气之流行而有秩序者也,非气之外更有理也。理与气不能对立。东原之说,盖有取于整庵。然天理、人欲,语见《乐记》。《乐记》本谓穷人欲则天理灭,不言人欲背于天理也。而宋儒则谓理与欲不能并立。于是东原谓天理即人欲之有节文者,无欲则亦无理,此言良是,亦与整庵相近。惟谓理在事物而不在心,则矫枉太过,易生流弊。夫能分析事物之理者,非心而何?安得谓理在事物哉?依东原之说,则人心当受物之支配,丧其所以为我,此大谬矣。至孟子性善之说,宋儒实未全用其旨。程伊川、张横渠皆谓人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义理之性善,气质之性不善。东原不取此论,谓孟子亦以气质之性为善,以人与禽兽相较而知人之性善,禽兽之性不善(孟子有“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语)。余谓此实东原之误。古人论性,未必以人与禽兽比较。详玩《孟子》之文,但以五官与心对待立论。孟子云:“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人而已矣。心之官则思,不思则不得也。”其意殆谓耳目之官不纯善,心则纯善。心纵耳目之欲,是养其小体也;耳目之欲受制于心,是养其大体也。今依生理学言之,有中枢神经,有五官神经。五官不能谓之无知,然仅有欲而不知义理,惟中枢神经能制五官之欲,斯所以为善耳。孟子又云:“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性也。有命焉,群子不谓性也。”是五官之欲固可谓之性。以五官为之主宰,故不以五官之欲为性,而以心为性耳。由此可知,孟子亦不谓性为纯善,唯心乃纯善。东原于此不甚明白。故不取伊川、横渠之言,而亦无以解孟子之义。由今观之,孟、荀、扬三家论性虽各不同,其实可通。孟子不以五官之欲为性,此乃不得已之论。如合五官之欲与心而为真,补犹扬子所云善恶混矣。孟子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性所具有。荀子则谓人生而有好利焉,顺是则争夺生而辞让亡矣。是荀子以辞让之心非性所本有,故人性虽具恻隐、羞恶、是非三端,不失其为恶。然即此可知荀子但云性不具辞让之心,而不能谓性不具恻隐、羞恶、是非之心。是其论亦同于善恶混也。且荀子云:“途之人皆可以为禹。”孟子云:“人皆可以为尧舜。”是性恶、性善之说,殊途同归也。荀子云:“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孟子云:“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此其语趣尤相合。(孟子性善之说,似亦略有变迁。可以为善曰性善,则与本来性善不同矣。)虽然,孟子曰:“仁、义、礼、知,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荀子则谓礼义法度,圣人所生,必待圣人之教,而后能化性起伪。此即外铄之义,所不同者在此。
韩退之《原性》有上中下三品说。前此,王仲任《论衡》记周人世硕之言,谓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举人之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故作《养书》一篇。又言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又孔子已有“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困而学之又其次,困而不学民斯为下”语。如以性三品说衡荀子之说,则谓人性皆恶可也。不然,荀子既称人性皆恶,则所称圣人者,必如宗教家所称之圣人,然后能化性起伪尔。是故,荀子虽云性恶,当兼有三品之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