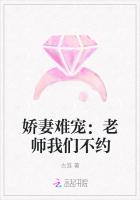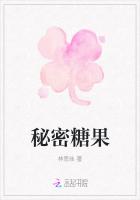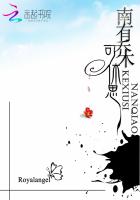《论文八首》与《论诗十二绝句》,创作时间虽相差仅一年,但对诗歌理论的阐述,却有着明显的提高,后者较前者更为具体而深刻,从中可以看出其诗论是不断发展的。如“胸中成见尽消除,一气如云自卷舒”。“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凭空何处造情文,还仗灵光助几分。奇句忽来魂魄动,真如天上落将军”诸句中的“情”、“真”等字眼,指的是诗人内在的真情、真意,是诗人对审美对象进行观照时,由审美对象所激发的主观审美体验的自然流露、真实抒发。张问陶把诗人的真性情作为诗歌创作的内心基础和创作前提,表明他已认识到诗人的真实思想感情是诗歌艺术的重要美学内容,认识到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和诗歌艺术的本质特征。诗中的“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及“文场酸涩可怜伤,训诂艰难考订忙”等句,可以明显地看出,与袁枚的“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及赵翼的“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的诗歌理论,是一脉相承又自具面貌的。可以说,《论诗十二绝句》是张问陶诗歌理论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题屠琴隖论诗图》十首31
妙灵何处说心声,粉碎虚空自浑成。
如向先天开一画,教他钦宝不知名。
仙经佛颂养灵胎,七宝庄严启辩才。
提笔便存天外想,神龙鳞爪破空来。
规唐摹宋苦支持,也似残花放几枝。
郑婢萧奴门户好,出人头地恐无时。
土饭尘羹忽斩新,犹人字字不犹人。
要从元始传丹诀,万化无非一味真。
来先无谓去无端,口吐人言亦大难,
是呓是痁都不解,回头鹦鹉在阑干。
下笔先嫌趣不真,诗人原是有情人,
生来将肘无风骨,且请搏沙待转轮。
妃红俪白想千年,祸枣灾梨亦惘然,
辛苦噉名皆劣伯,仙才何暇计流传。
也能严重能轻清,九转丹金铸始成。
一片神光动魂魄,空灵不是小聪明。
敢云老马竟知途,看尽寻常大小巫。
珍重《华严》留墨海,诗中一样有衣珠。
公事公言醉不辞,无邪诗教本无私。
一编也自留天壤,那望人知胜我知。
《题屠琴隖论诗图》组诗作于嘉庆十七年壬申(1812)冬。时年49岁的张问陶辞官侨寓吴门,时有闲暇,与江南的新老诗友赵翼、孙原湘、孙星衍、吴锡麒、梁同书及澄谷和尚等频频唱酬。屠琴隖(公元1781——1828年),名倬,字孟昭,号琴隖,晚号潜园、耶溪渔隐。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庆戊辰(公元1808年)进士,官至九江知府。倬夙智早成,质行独绝,诗才伉爽,与郭鏖、查揆齐名;乡举后,读书清平山中,与一时名流以诗文相砥砺。又工画山水,长书法,见重于时。著有《是程堂诗文集》。屠琴隖论诗有独到之处,如其《菽原堂集序》记查揆论诗,32尝谓:“沧浪香象渡河,羚羊挂角,只是形容消纳二字之妙。世人不知,以为野狐禅。金元以降冗弱之病,正坐不能消纳耳。《唐书·元载传》:胡椒八百斛,他物称是。举小包大,立竿表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以“消纳”二字概括查揆论诗大旨颇为精妙。钱钟书先生誉为“真解人语。”33船山在京师时就与屠倬有交往,曾作有《题屠孟昭双藤书屋图》诗相赠。故友重逢,船山作《题屠琴隖论诗图》十首,对自己的诗论主张又作了一次精辟、深刻、鲜明的阐述。34
妙灵何处说心声,粉碎虚空自浑成。如向先天开一画,教他钦宝不知名。
《易经》认为,太极乃万物本源,先天所在。古有传说,伏羲氏始画八卦,一画开天显无极。“先天开一画”本指开辟浑噩之玄沌,此处喻首创、出新。张问陶强调不虚伪妄作,不因袭古人。要立足于自我的阅历性情,吐露出内心真实的声音,粉粹无边际之虚空,如同“先天开一画”,使诗作有如钦宝,而浑然自成。这首诗的主旨申明了诗歌创作必须创新,对乾嘉诗坛偏重考据以及规唐模宋的诗风,是有力的反击。
仙经佛颂养灵胎,七宝庄严启辩才。提笔便存天外想,神龙鳞爪破空来。
“仙经”乃道家成仙了道的典籍;“佛颂”指佛家修身养性之偈语。“灵胎”是贯注于性灵的生命,借指由性灵而生出的诗歌。“七宝”乃佛教名词,即砗磲、玛瑙、水晶、珊瑚、琥珀、珍珠、檀香七种宝物。这首诗是以禅喻诗。前两句类似于陆机《文赋》中的“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指出读书学习,能开拓视野,加强文学修养。但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只靠“仙经佛颂”来培养自己在诗歌创作上的“灵胎”是远远不够的。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后,还要广启思维,运用丰富的想象和联想——“提笔便存天外想”,即陆机《文赋》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于是诗思如神龙鳞爪,35破空而来,创造出最有神彩韵致、缥缈淡远、空灵含蓄的意境。张船山逻辑严密地论述了读书、思维与创作的重要关系。
规唐摹宋苦支持,也似残花放几枝。郑婢萧奴门户好,出人头地恐无时。
清代乾嘉诗坛拟古者缺乏个性、因袭他人之作,是张问陶着力批判的“诗中无我”的典型。他先在《论文八首》之七中讥刺:“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次年写就的《论诗十二绝句》之十又讥评:“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本首诗更将矛头直接指向沈德潜、厉鹗这些规唐模宋者。诗人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指出:“规唐模宋”者成就再大,也似郑婢萧奴,36永无“出人头地”之日。他们的作品,只能有如残花败蕊,生气尽丧。张问陶《和少仙》诗中有“甘心豢养非天马,尘劳容易误神仙”一句,更鲜明地表达了要绝去依傍、门户独开的论诗主张,此亦表现出张问陶高傲清狂的个性。
土饭尘羹忽斩新,犹人字字不犹人。要从元始传丹诀,万化无非一味真。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尘饭涂羹可以戏而不可以食也”。以尘沙作羹、泥土当饭本是儿童的一种游戏。作者在此用来比喻创作,谓在诗歌创作上,既要有真实的思想感情,又要富有新意。所谓“新”,即是将“本”与“化”融为一体,也就是诗人所说的“犹人字字不犹人”。而“真”,则是不管事物如何“千变万化”,但总不失其本色,也不管感情如何“千变万化”,总不失其本心。即便号称“元始天王”的盘古真人的炼丹方法,无论如何变化,其“本真”是始终如一的。创新不排斥向他人学习,但是,学习不是机械模仿,动笔写作时要“字字犹人”而异于人,要自出新意,学习的目的在于师心。
来先无谓去无端,口吐人言亦大难。是呓是痁都不解,回头鹦鹉在阑干。
张问陶的《论诗十二绝句》之五云:“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功纯始自然”,说明提炼语言的重要性。这里又说“来先无谓去无端,口吐人言亦大难”。指出借用他人的话,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语言的使用有一定的语境,只有理解作品,理解他人的思想,才可能真正吸取营养,人为我用。写诗不能依人讨乞,倘若只知照抄他人的原话,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甚至连梦话、痴话都不去分辨,殆与鹦鹉学舌无异。杜甫写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不朽篇章,是与他“转益多师是我师”有直接关系。诗人要借他人口中之言,转化为我的胸中之言,再从我口说出。要字字古有,句句古无。这里进一步强调了继承中的发展与创造。
下笔先嫌趣不真,诗人原是有情人。生来将肘无风骨,且请搏沙待转轮。
张问陶在此对诗写真性情又作了进一步的肯定与阐述。诗人的下笔成诗,必须首先有诗的真情趣,要有真情实感。“真”是诗的灵魂,诗的价值所在。然后再结合诗中刚健质朴、优美形象的语言及骏爽直率豪荡的意气,方可形成富有气势的情韵及独具艺术感染力的风骨。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里说:“怡长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故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如果诗无真情趣,无真性情,即使具有绮靡浮艳的语言,亦不是具有风骨的好诗。从张问陶的诗歌创作看,他偏重风骨之作。
妃红俪白想千年,祸枣灾梨亦惘然。辛苦啖名皆劣伯,仙才何暇计流传。
诗歌如果没有真情实感,只徒具“妃红俪白”的华丽外表,难以流芳百世。而创作主体的贪求虚名,有碍真性情的自然直露,则会堕入“劣伯”的泥沼。举凡诗之仙才如李白、杜甫者,他们并未考虑自己的诗歌能流传后世,但由于他们对现实生活有深刻的感受,然后再结合其高度的艺术素养与文学造诣,直抒性灵,写出自己生活中的真实感情,创作出了“李杜诗篇万口传”的千古传颂的诗篇。此直抒性情、为情而诗者,自然会流芳百世。
也能严重能轻清,九转丹金铸始成。一片神光动魂魄,空灵不是小聪明。
张问陶反对饤饾为诗,但不排斥诗歌形式上的锤炼。一首好的诗歌,要象九转铸金丹一般,经过反复多次的锤炼,既可沉雄凝重,也可轻柔明丽,实现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后两句指出在诗歌创作中,要达到“空灵”动人的艺术效果,必须要具有“九转金丹”的刻苦努力过程。动人魂魄的诗歌,不是仅仅任性而发,也不是靠“小聪明”的创作态度及创作方法所能攀越的。船山所言实际上是自己的创作体会,其诗作不仅各体兼擅,而且既能作典雅端丽、秀美隽妙的“秀语”,如《阳湖道中》、《晚泊镇江京口驿》、《即目》;又能铸伟美刚劲、激情澎湃的“雄辞”,如《宝鸡县题壁十八首》、《芦沟》,兼阳刚与阴柔之美。
敢云老马竟知途,看尽寻常大小巫。珍重《华严》留墨海,诗中一样有衣珠。
任何艺术家创作的基础和源泉都离不开客观的现实生活。黄庭坚的《题子瞻〈枯木〉》诗中称:“折冲儒墨阵堂堂,书入颜杨鸿雁行。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就是指艺术家必须有多方面的积累和修养,融会贯通,厚积薄发,才能最后取得突出的成就。张问陶根据自己多年来在诗歌创作上的深刻体会,认为社会生活的积累和人生识力对写诗是十分重要的。“小儒未闻道”,无资格“摇臂称诗人”。“胸中有天地,触物皆经纶。以此事章句,譬诸龙一鳞。”37看遍了各种世俗人情,体验了百味人生,诗人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体验,将满腹感怀与切身之情蕴藏于诗的内容里,如“衣之有珠”,使得诗歌饱含着极有价值的思想内容。
公事公言醉不辞,无邪诗教本无私。一编也自留天壤,那望人知胜我知。
此诗旨在照应和总束全组诗歌。表明诗歌创作只是用来传真情、达真意、写性灵而已。诗人抒发出自己的真实感情,吐露出心底的声音。兴之所至,笔亦随之,不虚伪,不造作。留诗于天地之间,不依傍门户,不模拟古人,惟求达到真、善、美而已。不计流传,无所谓他人是否知晓与理解。读其组诗,如睹其人,亦如闻其声。张问陶无视他人的评头品足,“我自知我”的率真形象跃然纸上。
张问陶写这首诗时,已经四十九岁。这一组诗歌是他最后一次系统论诗。不足两年,即卒于苏州。比较《题屠琴隖论诗图》十首与《论文八首》、《论诗十二绝句》,我们可以看出,张问陶晚年诗论的内容更务实,更深刻,更全面,是对自己以前诗论的总结,更是对自己以往诗论的发展。他执着地坚持:诗歌创作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性显现;提倡以性情论诗,又以禅喻诗,从美学高度论诗;反对模唐规宋,又提倡“转益多师”,向他人学习;反对以笺注、考据入诗,也反对雕文镂彩,强调写真景、传真情、达真意、得真趣;崇尚“仙才”(天才),又看重创作主体的修、养、炼;突出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和灵感的重要性,又坚持必须有坚实的生活基础。这一组诗是张问陶晚年对自己的诗论主张的精辟的概述和总结,通过这组诗可对其诗歌理论得到一个总体认识。
绘画是视觉艺术,诗歌则是听觉艺术。两者媒介不同,题材不同,感受的途径也不同。但诗与画虽各具特点,却也有相通之处。作为造型艺术的绘画与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两者外部形态差异很大,但其本质都在于作者心声的表达,即“诗为心声,画为心印。”而且在创作规律和鉴赏标准上,诗与画也有不少内在相通的东西:两者都运用形象思维进行艺术构思,都通过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都特别讲究气韵生动、意境深邃和言(象)外之意等等。正如清沈宗骞所说:“画与诗,皆士人陶写性情之事;故凡可以入诗者,均可以入画。”38也如苏轼所言“诗画本一律。”39古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ofCeos)早就说过:“画为不语诗,诗是能言画”。邵雍亦言:“画笔善状物,长于运丹青;丹青入巧思,万物无遁形。诗笔善状物,长于运丹青;丹青入秀句,万物无遁形。”40故诗画一体的题画诗更为赏诗爱画者喜爱。
题画诗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专指题在画面上的诗,后者还包括不直接题在画面上的吟画、题画、论画以及题扇画、题壁画、题屏风画的诗歌。题画诗的产生原因之一是古代不少书画家和诗人,在长期的艺术创造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创作经验,也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美学观念和艺术见解,遗憾的是并非每个人都能留下有关论著加以专门系统地阐述,而是选取题画诗、题诗诗、题书诗、序跋等灵活而特殊的平台,借以交流创作经验,表达自己的美学观、艺术观。因此,它们就常常具有画论兼诗论、书论以及文论的性质。从现有资料看,广义的题画诗在六朝时已经产生了。特别是由梁至北周的杰出诗人庾信,在梁朝时,曾作《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生动地描绘了屏风上的各种优美画面,在题画诗创作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诗人的题画诗,对后世画上题诗产生了极大影响。李白、杜甫、白居易、罗隐、韦庄等都有题画之作,其中,杜甫的题画诗数量之多、影响之大,终唐之世未有出其右者。但真正把诗题在画上,始于宋代文人画的崛起之时。真正意义上的题画诗自此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文化泰斗苏轼,不仅为题画诗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是身体力行的艺术实践者。他在评论同样能诗善画的王维时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41。“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经典性的命题,遂成为中国一条重要的品诗论画的美学原则,对后世影响极大。苏轼备受人推崇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正是为僧人惠崇的春江鸭戏图而作的题画诗。元明之际,中国文人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元代的赵子昂、黄公望、倪云林、王冕,明代的刘伯温、沈石田、文征明、唐寅、徐渭、董其昌等,都以自己的艺术实践,推动了题画诗的发展,并使之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之一。到了清代,文人画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艺术大师八大山人42和石涛,清初“四王”43、“扬州八怪”等,都把题画诗推向了艺术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