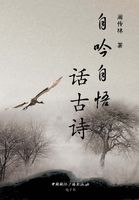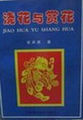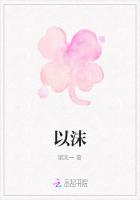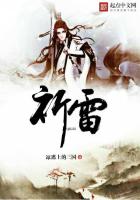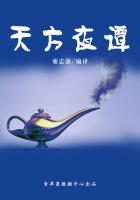一、关于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
“文以载道”是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学观念。一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几乎可以相当于一部“文以载道”观念的发展史。最早儒家的“兴、观、群、怨”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说”,便是这种思想的滥觞。以后,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原道”、“征圣”、“宗经”等篇,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的名言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提炼。唐时的韩愈、柳宗元更在此基础上针对“前人纤巧堆朵之习”提出了著名的“文以明道”说。但“文以载道”一词的出现是在北宋时,周敦颐的《通书·文辞》曰:“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此后,“文以载道”作为历代正统的文学观念,牢固地占据了国人的心灵。
“道”者何也?今人泛指思想体系、规律目的等。而古人之言“道”,各家言其之内涵并不相同。大多指儒家之道,也有指道家之道,还有指儒、道、释混合之道,甚至指经国之方略大道,但无论其说的是哪种道,历史上每次载道理论的提出,往往都带有反形式主义、维护政治统治等色彩。而且就史实看,刘勰之前的理论批评,尚能辩证地看待文与道之关系,唐以后,逐渐向“载道”倾斜。故客观地审视传统观念,其利其弊都相当明显。一方面,古人反对为文而文,反对言之无物,讲求内容与形式、人品与文品、道德与文章的完美结合,要求文学家有责任感、道义心。这方面,也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在反形式主义的同时,人们往往矫枉过正,不适当地抬高了文学的地位,夸大了其功利作用。“文非有关世道不作”;文章当“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诗“必尊人伦日用”;“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当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可“经纬天地”、“救治人弊”等,都是中国文人烂熟于心的古训。
不能说古人之言毫无道理。文学作为作家精神的产物,审美愉悦、消遣娱乐、熏染性情、拓宽视野是其重要的功能,但教育引导之功利作用也不可否认。而对于身处社会剧烈变革时的作家和一部分创作个性上偏重于道义审美的作家来说,可能会更为注重后者。令人不满的是,古人委实过分抬举了文学,且在有关文学本质的阐述上,对于文学的功利作用又加以了“执其一端、不及其余”的强调,以至于“在正统的古代文论中,政治功用就是文学的本质”。这就未免过于失当了。
自命中庸的中国文人在文学本质问题上,为何竟会显得如此极端、片面呢?这并非思想方法失当,而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制约下,知识分子的生存条件及随之滋生的依附意识使然。
亘古以来,中国为王权统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身为臣子的知识分子即使职位再高也是帝王的子民。隋朝以降,科举考试就成为知识分子谋求出路的唯一途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利禄,功名利禄也造就了知识分子的依附意识。这种在王权政治、科举制度下滋生的依附意识,使历代文人大都心甘情愿地“食君之禄,为君分忧”,并在思想文化方面责无旁贷地为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政治统治服务。在文学方面,则表现为夸大文学的作用,强调文学以载道为目的。
历代文人之所以如此夸大文学的作用,与当时落后的农业经济也有关系。因为,假如是在商业、航海业、农业并举的实行民主制的古希腊城邦社会,或者是在商品经济和各种传播媒介比较发达的今日中国,人们虽不会忽视文学、贬低文学,但也会以比较客观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可是在过去报纸、电台、电视等媒介尚未出现的封闭的小农经济社会里,人们赖以传道的工具只有“文”(包括文章、诗歌、戏曲),于是,中国历代文人近乎失衡地重视文学,夸大文学的作用尤其是其功利作用,也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了。
然而,这样一来,其弊端就更加明显了。人们在抬高文学的同时,实际上却贬低了文学。“统治者视文学为政治附庸,文学家自己也大多倾心于文学为政治工具。”文学应有的独立品格被削弱。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明太祖创设的科举考试时所作的八股文,专从儒家经典《四书》中出题,参试者“写体会而代古圣贤立言”,更使这种载道思想变本加厉,“文学必包含圣贤之大道……不包含道义的,便不能算是文学”。正是在漫长岁月的发展中,这种思想也就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沉淀下来,成为一种潜藏于中国文人意识深层的思维模式。而这种背离文学独立品格,充当载道工具的思想和“文学为……”的思维模式,正是传统“文以载道”观念的要害所在。
二、胡适等先驱者对“载道”观念的反叛
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变革始于近代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现状,激发了一批又一批有志之士奋起挽救中华。在救亡图存的实践中,人们首先利用的武器是文学,于是,文学观念的演变也随之开始。虽然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理论家,还不可能对强大的正统文学观念作出整体的审视,但西方进化论和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以及更主要的,出于维新改良运动的迫切需要已促使其发生新变。要求文学贴近现实生活,以“今社会”为文学之本源,而不是“代古圣贤立言”;发挥文学的政治功利作用,为改良运动服务,而不是“事父”、“事君”,等等,与千百年来代代相沿的以载道、维护封建道德为主的传统文学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代表这一时期的最高成就者,除了梁启超先生,还有王国维先生。王氏《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虽无一字明确指向“文以载道”,但对数千年来不容置疑的传统文学观的“载道”实质已产生怀疑:“‘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唐虞。’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矣……所谓‘诗外尚有事在’……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字里行间,对古代文人的依附意识,充当工具的思想观念,表示了极其强烈的反感。只可惜“在当时是空谷灵音,孤声绝响。不但无人共鸣,也无人了解”。
对以“文以载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学观念的明确否定,发生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可以说,当时对传统的文学观念,从“文以载道”的文学本质观,到“贵族文学”的服务对象观,直至“大团圆结局”的文学欣赏观……无一例外地发起了冲击。尤其是对“文以载道”的批判,更是当时先驱者们“不谋而合”的举措。其首举义旗者便是胡适。
1917年1月,当文学革命还未启幕,胡适针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种种弊病,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首当其冲者,便是传统的“文以载道”。其第一项“须言之有物”曰:“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一)情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二)思想……吾所谓‘思想’,兼盖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紧跟着,陈独秀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动者、胡适的声援人,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对“文以载道”也予以明确的否定。新文学运动就这样在否定“文以载道”的讨伐声中掀开了序幕。
然而,在众多著作中,每当论及这一问题,我们却几乎看不到对于胡适应有的评价。人们往往将包括反“载道”说在内的关于文学观念、文学内容变革的成果归功于陈独秀,而对于相对偏重于形式变革的胡适在这方面的建树则漠然视之。这实在是一个不应出现的现象。
诚然,对于“载道”观念的“大张挞伐”,是“五四”先驱者们“不谋而合”的举措;反“载道”中姿态最勇猛者,公论也不推胡适。然而,从现有资料看,胡适却是明确否定“载道”说的第一人。在此之前,蔡元培编《文变》集并作序,论及“文以载道”时仍无否定意见;王国维虽发出了对文人依附意识的强烈反感,其见解也极其深刻,却无一字直指“文以载道”。因此,假如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科学地尊重史籍的记载,那么,说胡适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有文字可稽的明确否定“文以载道”文学观的第一人,应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三、胡适反“载道”的思想成果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要想准确评价胡适当年的贡献,我们首先要对胡适同时代人反“载道”的成绩有个大概的了解。
海内外较早对“五四”的反“载道”予以郑重评价的是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先生。其三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史》的“导言”中有一节以“反载道始,以载道终”为题专论新文学史上先驱者们反“载道”的壮举。文章的一些观点及分析,笔者不敢苟同,但文章提到“自文学革命开始……那些披荆斩棘的先驱作家们,都一致反对‘文以载道’的古文传统。这本来非常正确”,可是,“对于‘文以载道’这件事了解不深透。他们只直觉的反对旧文学载孔孟之道”。其中,“对于‘文以载道’这件事了解不深透”,“只直觉的反对旧文学载孔孟之道”之语,的确是见解高明,非常客观地道出了文学革命初期先驱者们对“文以载道”这一传统观念的认识水平及当时反“载道”斗争的大概情形。
以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言论来说,陈独秀反“载道”的姿态大概再激烈不过。他先是在1917年初的《文学革命论》中批评韩愈“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不久,在两篇“通信”中,他又再三指出:“旧文学与旧伦理,本是一个家庭,固不得去此失彼。”他还在《答曾毅书》中指出:“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道’实谓天经地义神圣不可非议之孔道,故文章家必依附天经以自矜重。”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对旧文学、旧伦理、旧政治之间的关系认识非常深刻,在当时再无第二人可以比肩,但他只是从反旧文学载旧伦理、旧道德的角度去抨击“文以载道”。
到了1918年年底,周作人作《平民文学》。这时的周作人,已无须像文学革命初期的陈独秀那样通过抨击旧文学与旧伦理、旧政治的关系来讲明文学革命的必要性。他所面对的,是反掉了“载道”的旧文学后,应创立什么样的新文学。在这一方面,他为新文学的内容提出了几个标准:
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
我们不必记偏重一面的畸形道德……所谓愚忠愚教——殉节守贞,全不合理。
其反对“文以载道”自不言而喻。但也只是从新旧文学内容转换的需要,“反对作为内容的‘道’”,对“文以载道”的认识并未深入一步。
直到1921-1922年,沈雁冰、郑振铎在提倡为人生的文学时,对“文以载道”的了解才稍稍有所深入。沈雁冰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说:
中国旧有的文学观念不外乎(一)文以载道。(二)游戏态度两种。
道义的文学界限,说得太狭隘了,他的弊病尤在把真实的文学弃去,而把含有重义的非纯文学当作文学作品;因此以前的文人往往把经史子集,都看作文学……
郑振铎也提出:
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学观,却是谬误的……一派是主张“文以载道”的,他们以为文非有关世道不作……传道派的文学观,则是使文学干枯失泽,使文学陷于教训的桎梏中,使文学之树不能充分长成的重要原因。
与初期陈、周不同的是,沈、郑两人已注意到“文以载道”的种种弊病:
(1)“太狭隘”,把文学拘在道义的界限里,无法表现生活的丰富性。
(2)把真正的文学丢弃,把“载道”的非纯文学当文学。
(3)影响了文学的发展。
这些意见都是从艺术本体的角度来认识“文以载道”的。与初期相比,已有所突破,然而这时已是胡、陈初倡反“载道”的五年之后了。
总之,就传统文学观念向近现代演变的发展轨迹看,“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能义无反顾地高擎起反“载道”的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文以载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学观念的整体否定,的确比近代时期的梁启超、王国维迈出了一大步,而且是极具历史转折意义的关键一步。此外,在某些方面,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分析批判也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这一切都为我们今天的反“载道”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从总体情况看,“五四”时期的反“载道”,成绩还是有限的。先驱者们对于“文以载道”说形成的历史、原因及其违背文学的独立品格、充当工具的思想实质的认识,不能说混沌一片、毫无意识,但的确还少有人论及。因此,大致来说,初期基本停留在“只反旧文学载孔孟之道”的思想水平,发展期有所突破,对“载道”观念削弱文学独立价值的弊病有所认识,但总体来说,对于“文以载道”这件事,了解还是“不深透”的。
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中,胡适也就难以超越当时的历史局限。当他提出“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认为“宜以……情与思二者”代之时,其关注的重点,是文学所言之“物”,即文学的内容应以情与思代替孔孟之道,而不是“文以载道”观削弱文学独立价值的实质。
从学衡派学者吴芳吉《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一文也可看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是要“反旧文学载孔孟之道”。否则吴氏就没有必要大谈特谈“夫吾国文学,以受孔孟之道影响为最深厚,后世文人之所谓道,固亦孔孟之所为道。孔孟之所为道者,曰忠恕之道,曰仁义之道,曰孝悌之道……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之道……凡此种种,皆文以载道之所为道也”。
可见,胡适的反“载道”,其实并未超出五四初期先驱者们“反旧文学载孔孟之道”的整体思想水平。但比之同时代人,胡适却又有着独特的建树。
首先,他敢于率先否定传统的文学观念,又能够独具慧眼地肯定与这一核心观念有关的一些优良传统,如坚持“言之有物”,坚持“文学关乎世道人心”等。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五四”初期他的一些言论中。
比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他说:
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夐绝千古也。
在《留学日记》中,他写道:
文学不当与人事全无关系。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
我们以为文学是社会的生活的表示,故那些“与社会无甚关系”的人,绝对的没有造作文学的资格。
可见,对于自古以来中国文人所看重的文学关乎世道人心的功用特点,胡适是深以为然的。
在这一点上,胡适与学衡派学者吴芳吉的见解似比较接近。吴芳吉认为:“文学作品譬如园中之花,道德譬如花下之土,彼游园者固意在赏花而非以赏土,然使无膏土,则不足以滋养名花。土虽不足供赏,而花所托根,在于土也。”尽管二人对“文以载道”的见解相悖,但在文学与思想的关系上,却有一定的共同之处。
其次,胡适对古人过分强调“文非有关世道人心不作”的片面性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在《留学日记》中,他曾对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发”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文学之优劣,果在其能“济用”与否乎?作为文词者,果必有所讽乎?
老杜之《石壕》、《羌村》诸作,美感具矣,而又能济用。其律诗如“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则美感而己。
作诗文者,能兼两类,上也。
白香山抹倒一切无所讽谕之诗,殊失之隘。
由上可见,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胡适还无法对“文以载道”作出进一步的分析,但他对于文学的功用特点和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的阐述,以及从中表现出来的他对传统文学观的某些合理内核的深刻领悟,却能给我们以启迪,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传统的文学观念。
相比之下,同为先驱者的陈独秀在这一点上就不如胡适。他虽能一针见血地指出“载道”的本质离“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者也不远”,对于“载道”使文学“独立存在之价值”被“破坏无余”的现象也有着类似王国维先生的深刻认识,但在反“载道”时,却连“言之有物”的传统也不赞成,认为“言之有物”易“失文学本义”,有重蹈“言陈腐之物”陋习之可能,其理由是:“载道与否,有物与否,亦非文学根本作用存在与否之理由。”陈氏之言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为反文学载孔孟之道,竟连“言之有物”的传统也视为与“文学本义”格格不入的对立物,这种对传统的认识就缺乏全面的、辩证的眼光。
有必要言明的是,笔者之所以注意到胡适在这方面的建树,不单是由于他在同时代人中的特别表现,更主要的是因为海内外现代文学研究的某些偏颇。因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当代的一些研究者反而远逊于80多年前的胡适。比如说,有的研究者一说起反“载道”,就将与“文以载道”有关的一切,如文学的功利作用、作家与社会人生的关系、作家的责任感、作家的道义心等统统否定,其理由是文学“不应与任何功利打算混为一谈”。于是在他们的议论中,用文艺“改良社会”的鲁迅和“为人生的文学”都有了“载道”的嫌疑。还有的研究者虽不否定文学的功利作用,但在分析20世纪文学功利观的发生时,也不能从文学的本质去把握传统功利观中蕴涵着合理的内核,只是单纯地从传统的思维模式寻找根源。
当然,对于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及文学充当工具的实质、“文学为……”的思维模式,我们是应当时刻警觉的,惟其如此,文学才不会成为政治的附庸,才能繁荣我们的文学事业。因此,反“载道”仍任重而道远。
与此同时,我们对自己民族的传统也应持有基本的态度:我们反“文以载道”,不等于要将与这一核心观念有关的一切统统都否定。周作人曾说过一句精彩的话:“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其不可轻侮,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为关键的,是因为传统本身还有着许多符合民族审美要求、符合艺术本体规律和体现文学本体特征的合理的成分。
从这一角度讲,胡适当年的反“载道”就有自己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