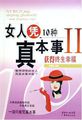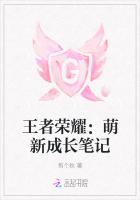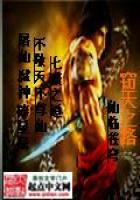振根振根,快吃茶。舅公接过阿娘(奶奶)泡来的新茶,撮圆嘴唇吸了一小口,咂咂嘴品味一会儿,脸上舒展出一朵花说,阿姊阿姊,这水真甜啊,上海吃不到这样好的水,这是天水吗?阿娘说是的,是天水,上海黄浦江的水哪有老家的水好吃。
“天水”是每家每户水缸储存的饮用水。下雨天,雨水顺着屋檐下的水槽落进下面的水缸,雨水带下来屋顶瓦片上的灰土、草梗等,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杂质沉到缸底,水就很清澈了。用小水桶把水舀到放置在厨房的另一个水缸,这缸清水就是全家的饮用水,做饭、烧水都用它。外面院子里的那缸水,一般供日常洗漱。用上自来水之前,靠天吃水,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储水。
有一段时间没下雨,厨房内、院子里的水都用完了,就要到吃水池挑水喝。吃水池在外钟路“树行”旁边,与芦江河一路相隔,“树行”是供销社的木材商店,仓库、院子堆满木料。吃水池的池壁垒起齐整的石块,四周围着水泥护栏,有一个入口,砌着台阶通到池底。天刚蒙蒙亮人们就出来挑水,池边常常排起长队。精壮汉子挑起满满一担水,神态自若,健步如飞,滴水不洒。有姊妹俩来抬水,大人帮她们在台阶下面打满了水提上来,她们一前一后抬起水桶回家,虽然有点脸红耳赤,走得倒也平稳。有一种水车,是手拉车改制的,车厢类似长方体形状,能够装几十桶水,但很会漏水,因此拉水的走得很快,近乎小跑。水车一般是饭店、饮食店、二食堂等用水大户的,因为用量大,他们每天必要拉水。
我们从小就被告诫不能往吃水池扔东西,不能弄脏水。偶尔我们调皮往里扔个石子,要被大人呵斥。附近有对婆媳吵架,媳妇扬言要跳河寻死,拉拉扯扯出来,跌跌撞撞奔到吃水池边,挣扎着做张做势,终于没有跳下去,而是绕池一周,舍近求远,冲到河边,往埠头边一跳,水只及腿肚子,倒是水底的污物泛起一大摊。由此可见,镇上人们保护水池的观念深入人心。吃水池也因此很清很清,能够一眼看到水底,水中的鱼一动不动,像是立在池里。夏天,我经常趴在台阶玩小鱼,一趴就是半天,有两次滑进了池里,灌了几大口水,幸运的是正好有大人路过把我捞起,我湿漉漉地回到家,遭阿娘数落。
吃水池毗邻芦江河,犹如儿子依恋母亲,这是当初挖池人刻意设计好的。地下,河水透过一条路的间隔源源不断渗到吃水池,池水面永远与河水面持平。遇到大旱,芦江河露出河底,吃水池也干涸了。这时,居民吃水就要靠分布在全镇的十几口水井了。
打水人站立在井口,一手攥紧长绳的末梢,这长绳一头系牢在打水桶上,另一手松开打水桶,任其自由落体。地下传来沉闷的一声“砰”,是水桶落到水面了。打水人上下提了提长绳,凭手感觉到水桶盛满了水,就双手交替攥牢长绳一鼓作气提水,直到水桶放在井沿才松口气。井水冬暖夏凉,但味道不是很好。打水的过程中,不留神手一滑,长绳没攥牢,水桶就落进井里。捞水桶要用长长的晾衣竹竿,竹竿一头绑紧一个铁钩,因为井下是黑漆漆的,还需有人帮忙打手电筒往深处照,这样才能找到水桶的提环,用铁钩钩住,捞上来。由于水桶落井的情况经常发生,井旁也就矗立着一根这样的带铁钩的晾衣竿,随时备用。
镇上终于通自来水了,水厂建在新曹村附近芦江河上游一个河湾边。我工作后曾有事去过几次水厂,花草繁茂、树荫匝地的厂区里,偌大的水池处理着取自芦江河的水,“哗哗”的水声响彻一片。虽然水质是达标的,说实话,自来水不好喝,有股浓浓的氯气味,特别是水烧开了气味更浓。记得有一年夏天严重干旱,河面水位低于海平面,穿山碶外的咸潮倒灌进来,自来水有点咸。那个漫长的苦夏,人们对水的情绪既复杂又无奈,祖祖辈辈守着芦江河,吃着芦江河水,有什么办法呢?
“谁料想,铁树开花枯枝发芽,竟在今天……”那是2008年清明前夕,白溪水库的水刚刚接入柴桥自来水管网,那天我去阿娘住过的外钟路那边,看望来扫太外公墓的舅公。院子里坐着一位隔壁老阿叔,他捧着摩拭得油光发亮的紫砂壶,小口小口地呷茶,脸色特别的神清气朗。突然他唱响了这句曾经很流行的京剧唱段,接着是一阵哈哈大笑。老阿叔年轻时是个文艺积极分子,吹拉弹唱样样在行。
舅公那天也正好在品茶,他乐得合不拢嘴,眼睛眯成一条缝。舅公八十多了,眼不花耳不聋,只是有点“背”。我对舅公说,舅公,报纸登过了,这水可以生吃的。舅公连连说,可惜阿姊没有吃上这么好的水,可惜阿姊没有吃上这么好的水。
现在我有时还会去外钟路以前住过的地方,后院的水缸还在,水还是那么的清,一眼望得到底,只是缸盖不知去向,水面浮了些细沫。我发现缸肚子里有两个马钉,勉强还能分辨得出,这一定是以前阿爷叫来补缸师傅打上的。小时候,我经常看到补缸师傅夹着布包,走街串巷,吆喝着“补缸——补甏——,补缸——补甏——”
讲司马光砸缸故事时,我带女儿来看过这个水缸。至于吃水池和水井,早已填塞,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