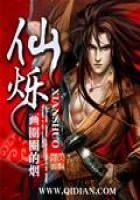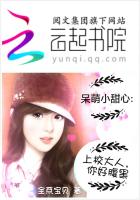紫石河发源自双石人山,山上流淌下来的千百条小溪在山岙间汇聚、融合,启程向东,一路弯弯曲曲,两岸串联起星罗棋布的村庄,自上游而下,依次是下龙泉、甘溪、大溟、里隘、东六房、高村、前郑、后郑、陈胜。流过陈胜桥后,紫石河汇入了芦江河,最终经穿山碶,东归大海。穿山碶只是在雨季芦江河水溢满的时候才开闸,这时的紫石河会湍急疾奔,途径狭窄的河床,更会汹涌起铁黑色的洄流。在平常,紫石河总是静静的,波澜不惊。
紫石河的河床比较浅,大部分河道更像是沟渎,特别是紫石滩那一段。紫石滩位于东六房与高村之间,水面波光粼粼,水质清澈,水域比较开阔,从东六房此岸到高村彼岸,目测距离应该有两百多米。临近高村那边,河面隆起一块洲沚,上面花木扶疏,绿荫婆娑。紫石滩是我们少年时代的水上乐园。如果夏天持续干旱,紫石河的水位就会下降,紫石滩中央的紫水墩就露出水面,面积大概有六七十平方米左右,我们从这边的河岸下河,可以趟到紫水墩上。在紫水墩打水仗很过瘾,弯腰捧起泥浆恣意互掷,水花漫天,泥点乱飞,光溜溜的少年人影幢幢,这天然真趣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有几年夏天台风频频光顾,几阵暴雨过后,紫石河水满满的,我们游泳游到紫水墩,站在墩上,水位也只及颈部或者胸部。
过紫水滩,就是两个莲叶墩。小莲叶墩上曾经有紫荆庙。早年,柴桥的三户开埠大姓曹氏、胡氏、郑氏为感念王安石疏浚芦江河、兴建穿山碶的政绩,联合建造了紫荆庙,里面供奉王安石塑像。后来塑像被毁,红墙飞檐颓倚,庙宇则改成粮库。每逢农忙季节,四面八方的农民肩挑背拉,把刚刚收割的稻谷运到粮站。开秤、过磅、晒谷……每天总是从天刚蒙蒙亮,忙到繁星密布。现在粮站解散了,古老的建筑里又搬进很多私人小企业,还有的房间用作仓库,那里又是另一番机器轰鸣的忙碌景象。
莲叶墩附近河岸曲折,水色浑浊,水势有点复杂,小时候长辈嘱咐我们不要到那里去游泳。近河岸水中长满芦苇,风吹过,细长低垂的芦叶沙沙作响,十分动听。乡贤虞景璜先生是清光绪年间举人,著有多种诗文集,一组《芦江十景》选取芦江河从源头到入海的十个值得称道的景点,其中的第六景《紫石回澜》描写的就是莲叶墩那里的景色:“长桥高障水横喷,莲叶墩前色半浑。两岸峰回收水势,浪化足就碧芦根。”长桥,一头连着河岸,一头连着小莲叶墩。大莲叶墩以前孤立河中,有牵渡,上面建有我们的郑氏宗祠,后来祠堂被改成厂房,疏水阀厂、衬衫厂等当时紫石乡一些效益比较好的乡镇企业都在那里。
紫色,高贵的颜色;紫石,附近山上确有紫色的石块;“紫石”这个地名,意寓祥瑞、福祉,我喜爱这个地名。
有一年夏天早晨,我跟随邻居一位同宗兄弟,从紫水滩出发,沿河岸作一次溯源。他一路紧盯着脚下的河滩,不时弯腰捡拾蛳螺、河蚌、河蛏子等,而我东张西望,这里拾起一片青花瓷,那里捡起一块卵石,遇到河边一个凉亭,还进去仔细看了很久。那一次我们走了很远,直到人迹罕至处才折回。中午到家,他的小木桶里河鲜满满的,应有尽有,我的却很少,干脆把我的全倒给了他。他马上分拣清理,去镇上摆摊卖掉。他家世代务农,从小他就会很多农活,直到现在他还是以勤劳、孝顺出名。
老家离紫石河不远,老家的房子很旧很旧了,在周围一排排新盖起的楼房包围下,显得十分局促。由于牵涉很多手续上的问题,老屋至今还没有翻新,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翻新。老屋在,根就在,我们像燕子归巢定期回去看看。有时候我也带女儿到紫水滩一带走走,夏天玩水,秋天捞河上漂着的野生刺菱。现在的紫石河沿岸是水泥块铺砌成的游步道,一个个新建的钓鱼台伸向河面。漫步在河边,极目远眺,远方的双石人山峰在云雾中隐约可辨,青黑色的山体苍苍茫茫;低头俯视,只见花木倒影在水面,清漪潋滟,十分令人赏心悦目。
紫石河,我们的母亲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