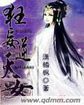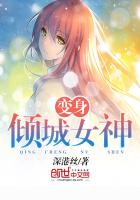我们抵达肇兴侗寨,已经迎候在寨门外的村民马上用长板凳、纺车挡道,他们排成一行拦住我们。他们个个穿戴艳丽的民族服饰,小伙子吹响手中的芦笙,女孩子唱起热情悦耳的歌曲。一曲既罢,她们斟满酒杯,一定要请我们喝下,又在我们每人的脖子挂上精美的长长的绶带,这才让我们进寨。拦路是侗族隆重的迎宾礼仪,来宾如果无法对唱拦路歌,得喝下罚酒。
肇兴侗寨坐落在山谷盆地,四面绿树环绕,满眼绿意葱茏,一条溪流穿寨而过。这里是黔东南侗族地区最大的侗族村寨,一家一户的吊脚楼簇拥在两岸,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吊脚楼用杉木建造,上覆青瓦,大都二层或三层,几座新盖的吊脚楼还散发出好闻的原木清香。临河架起长廊式木桥,桥两侧栏杆绘有日常生活场景和花木人物。桥上盖有顶棚,能遮风挡雨,因此也叫风雨桥。孩子们在桥上玩耍,几位姑娘在桥下低身漂洗头发,长长的秀发像一面黑色的旗帜在水中翻舞,灵动而柔情。过了桥,迎面便是高高耸立的鼓楼。鼓楼下部呈方形,上部有十多层重檐,八角攒尖顶,外形看起来像宝塔。几位长者坐在鼓楼,神态从容。我们在寨中漫步,不时看到白发苍苍的老祖母在石板上捶打靛青色的侗布,一下接着一下,“嘭、嘭”,捶击声低沉而结实。侗乡处处呈现安谧、和谐的原生态美。
晚上我们在一家侗家餐馆就餐。主人摆起长桌饭,原汁原味的侗家土菜,自酿的米酒,热烈的言谈,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啊。席间,一位年轻的村干部乘兴唱起了“琵琶歌”,歌声时而高亢,时而低回,别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意境,令人遐思联翩。他告诉我,侗家有“饭养身,歌养心”的说法,歌是侗族人民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侗家人用歌来承传民族历史传说,赞美先祖功绩,表达美好情感。他们从小就接受年长歌师的严格训练。歌师牢记着众多的歌词和曲调,还能即兴编歌,享有很高的名望。村里有位八十多高龄的歌师,曾多年被中国音乐学院聘为教师,前不久刚刚返乡。20世纪80年代,村里的歌手远赴巴黎,在夏乐宫国家剧院演出,侗族大歌那纯正、雅致、朴素的“东方美”,深深陶醉了欧洲听众,从此侗歌被公认为世界一流的艺术,他本人就多次带队赴欧洲、香港等地演出。
入夜,一弯弦月斜挂在深蓝色的夜幕中,鼓楼旁边的戏台亮起了大灯,游客们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坐在台下的长凳,欣赏村里年轻人表演歌舞。舞蹈表现日常生活、劳动、恋爱等,年轻人个个身材匀称,动作整齐划一,举手投足间,小伙子表现出刚强、果敢而不粗野的气概,姑娘们则呈现了温和、清雅而又不柔弱的性情。美妙的侗族大歌一曲接一曲,有一位姑娘是领唱,众姑娘合唱加入地非常自然贴切,不知不觉间她们分成低声部和高声部,低声部唱主旋律,高声部唱复调,低声部还派生出拖腔声部,不时穿插模仿鸟鸣、流水声。我们屏息凝神细听,神思被天籁美音牵引着,一时间忘记了身处何方。
在干栏式木建筑风格的肇兴宾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到建在山顶的堂安侗寨参观。站在村口俯瞰,梯田从山顶往山下绵延,一直望不到头,层层梯田边缘的曲线沿大山的褶皱起伏波动,非常优美。正值秋收时节,金灿灿的梯田像一块块、一条条厚实的织锦,蔚为壮观。堂安村古朴安静,青石铺成的小径四通八达,上下穿梭,吊脚楼、鼓楼、戏台、歌坪,以及水碾、石椎等,浑然一体。村头有一股清泉,“哗哗”从石壁喷出,流泻到石槽,石槽两端有壶嘴,槽中的水满溢出壶嘴,落到沟渠,流到下面一个圆形水池。村民喝水从壶嘴中接水,圆形水池里的水用来淘米洗菜。往下还有一个方形水池,用于日常刷洗,村民洗衣服都不用洗涤用品。再下面是个大消防池,用来养鱼。灌溉层层梯田的农业用水,就从大消防池流出。堂安人与环境如此和谐的紧密交融,可谓典范,中国与挪威合作建设的唯一一座侗族生态博物馆就建在村外。
离开堂安,我们又经过几个小时的辗转盘旋,来到掩蔽在群山深处的黎平县德顺乡平浦村。平时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少有访客,我们的到访好像在村中兴起了一股旋风。远远的,我们就听见欢快的芦笙曲和拦路歌。不等走近村口,村民们就迎上来,斟满手中的大酒杯,一定要我们喝下。他们待客是如此的真诚,晶莹的眼眸散发出仁爱的光辉,瞬间感染了我们,他们发自内心的热情,迅速消解了我们因长途跋涉引起的倦意。我们参观了村图书室、活动室和村民学校。听村干部介绍,半浦村是黎平县的先进村,各方面工作都很好,尤其是计划生育,全村没有超生户。中午,一位村民在盖起还不是很久的家里摆开很多桌酒席,村里有威望的长者、村干部都出席了。他们一次次举杯,一遍遍真诚感谢我们从远在东海之滨的北仑港畔来到西南高原看望他们。他们还说起,台江县有一条路被命名“宁波街”,就是为答谢宁波人民对黔东南的无私援助。说到动情处,他们又一次举杯致谢。侗家的米酒清冽、甘甜,我们都略有微醺。乘着席间空隙,征得主人同意,我上楼参观吊脚楼。二楼中间是客厅,两厢各有一间套房式卧室,朝西的卧室墙上挂着一对新人的结婚照,室内平板电视、音响等俱全。三楼有三间仓房,堆放着稻谷、花生等农作物,再上层就是阁楼和屋顶。我真想在这吊脚楼里住上几天,细细体验侗家生活。
临别,我们在村口的鼓楼小憩片刻,村里的歌队围坐在我们旁边,她们放声唱起了一首又一首大歌。歌声在山谷间久久回响,那发自肺腑的热情,天然直率的表达,再次深深感动我们,使我们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