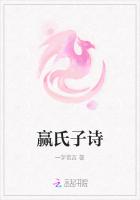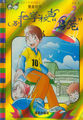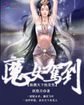七月初盛夏时节,正是看海的好季节,我们终于成行了期盼已久的东极之旅。
去东极先得在沈家门住一晚,否则第二天赶不上船。到了沈家门,当然不能不去著名的夜排档,因渔港拓宽改建,沈家门夜排档搬到了朱家尖大桥左侧的防浪堤上。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绵延数里的夜排档人声鼎沸,流光溢彩。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刚刚腾空出来的排档,一桌人坐定,迎面吹来的海风,脚下层层叠叠的浪涛,此情此景,使人心旷神怡。与老板娘一番讨价还价后,稍候片刻,鱼虾蛤螺就一一上桌,蒸煮烤炒,样样鲜美,杨梅酒红酒,饮料啤酒,我们在尽情品尝、干杯之后,个个稍带微醺。
离席,看到海堤上搭起了小舞台,有个乐队正在演唱。乐队三个人,一个主唱,两个演奏乐器,看年纪都在三十五岁以上,唱的都是老歌,歌声低回沧桑,听着有些沉重。
第二天我们登上了“东极”轮。去东极的游客很多,船舱很闷,座位又小,大家都挤到甲板上吹海风看海景。船驶过普陀山,海水就很清澈了,就像淡水一样。越往东,海上的船越少,不时有孤单的海鸥在船边追逐。环顾四周,波涛起伏,像一匹无穷无尽的蓝绸缎,使人产生几许孤独感。极目远眺,云淡风轻,海天交接处隐隐烟波浩渺,海面上偶尔点缀着无人居住的岛屿和礁石。三个小时的航程结束,前方终于出现一个大岛屿,这就是东极的庙子湖岛。
我们在下榻的旅馆吃罢午饭,就随处在码头附近逛。屋前屋后的墙上,随处可见风格独特的东极渔民画,画面有渔民的生活生产场景,也有海岛风光,色彩艳丽,技法夸张。
下午的项目是海钓,十多位游客来自宁波、杭州,快艇送我们到青浜岛。青浜岛有海上“布达拉宫”的别称,这是因为从海上看过去,青浜岛上依山而建的石屋高低不同错落有致,很像西藏的布达拉宫。东极的房子都是大石块砌成,方方正正很坚固,足以抵御台风。我们中有两位真正的海钓高手,他们全副武装,装备齐全,快艇送他们到一块孤立的礁石上,而我们大家则继续往前。经过一个个岛屿,不时看见采割淡菜的渔民在礁石上艰难地寻找淡菜。到了青浜岛,我们三三两两散开,各自找到合适的礁石,拉开租来的钓竿,下洱垂钓。我们所谓垂钓,不过是体验一下而已。有人钓上一条小虎头鱼,立即大呼小叫,引来其他人羡慕的目光。
海面上不时有海蜇载沉载浮,海蜇大约脸盆一样大小,很好看,透明的伞盖状腔体,里面的内脏是淡黄色,海蜇头是褐红色,有很多触须。其中有一只海蜇被海浪卷到我们脚边,缠住了钓鱼线。一个浪头涌来,钓者顺势把海蜇提到礁石上,但头和腔体已经被割离,腔体已打开,淡黄色的内脏裸露在阳光下。又一个浪头打来,腔体被卷走,只剩下海蜇头抛在礁石上。有人好奇地用手去触摸,立即有被蜇麻的感觉,赶紧在海水里刷洗。一下午,总共钓到了七条小虎头鱼,我们中有很多人一条都没钓到。
晚餐桌上,这七条小鱼一人一条都不够,大家只象征性地品尝一下,算是体验一下成就感。两位海钓高手收获颇丰,大家吃着他们钓上来的大鱼,听着他们讲述海钓经历,颇有感慨。
太阳一下山,渔民们就在码头边摆开了桌椅。东极的夜排档也很有情趣,每一个摊位同样都挤满了游客。远离喧嚣,在沿山而筑的石街上随意漫步,昏黄的街灯下,只有自己的足音轻轻叩响街面,却能体会到另一种世外清净。
我们住的旅馆就在码头边。站在窗边,看沉沉夜色中的海面,微如豆灯的信号灯一明一灭,宁静的海在浅吟低唱,忽然想起曾经背诵过的雨果的诗句《夜听海涛》:“这是什么低沉的声音?请你向海水那边谛听,这声音无比的深,它永远在呜咽,而又永远在咆哮,即使一种更嘹亮的音波,有时把它冲破……——狂暴的海风,吹着它的喇叭。”不论古今,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
凌晨三点,天已微露曦明,四点半,太阳已经出来了。这就是东极,祖国的最东端,东经122.4°北纬30.1°,这里的人们最早看到阳光。再往东一点点,就是公海了。有一首歌《战士的第二故乡》,据介绍,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就是在东极岛的军营里体验生活后创作的,以前经常在舟山电台听到有士兵点播这首歌。“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人都说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哨……”耳畔仿佛又响起那悦耳的旋律,感觉特别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