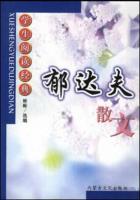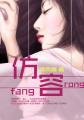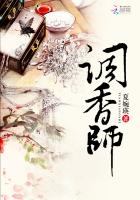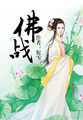这次,我想学着余先生也来切一刀,不过我切的是他前面不要的那个“1684”年。我的做法是,先考定张岱的生年:
张岱在《陶庵梦忆》卷三“南镇祈梦”中说:“万历壬子(1612),余年十六。”
古人计算年龄都用虚岁,出生为1岁,过1年为2岁,过15年即为16岁。从1612年往上推15年,可知张岱生于公元1597年。
再考张岱的卒年:
据清温睿临《南疆逸史》说:“山阴张岱,字宗子……长于史学,丙戌(1646;即清顺治三年)后屏居卧龙山之仙室,短檐颓壁,终日兀坐,辑有明一代纪传,既成,名曰《石匮藏书》……岱衣冠揖让,犹见前辈风范。年八十八卒。”
张岱既然活了88岁,那么将其生年1597年往下推87年,即可知他去世之年为公元1684年了。
当然,我不是研究明清史的专家,我的说法只是一家之言,未必能当作定论。但我毕竟经过了自己认真的搜集和查检,引用了可靠的史料,推理、考证也符合逻辑和规范。可余先生切下的蛋糕呢?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除了摸不清底细的读者会把它当作美味吞食下去,凡是严肃的学者是绝不会认可这种无根之说的。
㈣朱权被封于南昌,是在朱耷出生前223年吗?
余先生在《文化苦旅·青云谱随想》中写道;
他叫朱耷,又叫八大山人,雪个等,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后代。在朱耷出生前223年,朱权被封于南昌……
看来余先生是非常喜欢玩这种中外古今历史人物生卒年之间的推算游戏的。前面玩了张岱和狄德罗,现在又来玩朱权和朱耷了。殊不知这种推算有个前提,即被推算者的生卒年份必须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有哪一个无法考定,游戏也就要玩豁边了。
先看朱权被封于南昌的年份:
《明史·宁献王权传》载:“宁献王权,太祖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封。……永乐元年(1403)二月改封南昌。”
由此可知,朱权是在公元1403年被封于南昌的。
根据余先生的提示,我们将公元1403年下推223年,得出的结果为公元1626年。那么八大山人朱耷是否这一年出生的呢?先看一下几部权威工具书的注释:
1999年修订版《辞海》(1624或1626—1705)
1988年修订版《辞源》(缩印本)(公元1624—1705年)
《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1626—约1705)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约1626—约1705)
《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1626?—1705?)
在以上五部工具书中,有三部对朱耷的生年是用约数或存疑来表示的,如“1624或1626”、“约1626”、“1626?”只有两部用了肯定的口气,但确定的年份却各不相同,《辞源》作“公元1624”年,而《中国人名大词典》则作“1626”年,其间差了两年。余先生取了后者“1626”年,正好与“223年”吻合。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跟《中国人名大词典》属于同一个上海辞书社最新版的《辞海》,却注了个模棱两可的“1624或1626”。这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其实也难怪那些工具书的编纂者们,因为根据目前传世的文献资料,朱耷的生年和卒年都是无法考定的。我现在已经搜集并仔细读过的就有近二十种,即使以清邵长蘅(1637—1704)所作的记事较详的《八大山人传》来说,对于朱耷的生卒年份也没有片言只语的交代。因此,存疑是唯一可取的办法,任何没有根据的一刀切出来的年份,都是不会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的。
余秋雨散文月日记时差错举例
我国古代作者在以年、月、日来记述人们的出生、死亡或其他经历时,用的都是旧历(也称农历或阴历)。如:
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子厚以[宪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
宋文天祥《后序》:“[恭帝]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
这两例中的“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和“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用的就是千百年来传统的旧历。
到现当代,人们对于年、月、日等时间概念的表述有了一些变化,一般使用两种形式:
仍然用传统的旧历,但根据历表折算,在其年、月、日后面括注相应的公历(一般也称阳历)年、月、日。如:
唐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公元819年11月28日)
宋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公元1276年3月5日)
不出旧历的年、月、日,根据历表折算后,全部用公历来表示。如:
公元819年11月28日
公元1276年3月5日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
其一,一个用帝王年号记述的旧历年份,折算成公历时会有两个年份。因为阳历一般要比阴历多出一个多月(有时接近一个月,有时超过两个月),所以阴历在年末的月、日,折成阳历会超过12月,变为次年的1月。这样,公历便出现了两个年份。如:
唐元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公元819年10月10日)
唐元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820年1月14日)
其二,如果要用公历来表示,必须把旧历的年、月、日全部折算成公历的年、月、日,不能只改年份而不改月、日。如“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应当改成:
1276年3月5日
不能改成:
1276年2月19日(年份改公历,而月、日仍用阴历)
以上介绍的将旧历记时折算成公历记时的原则和方法,是现代从事史学研究或历史文学创作的人所必须掌握的常识。如果对于这些常识不甚了了乃至一无所知,那么,差错的发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现在,让我们转入正题,看一看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这两部历史散文中,是怎样来表述人物活动的时间的。下面先举两例:
《文化苦旅·道士塔》:“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余先生在这里用小说笔法为我们描述的内容,就是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时任敦煌千佛洞住持的道士王圆箓(一作“禄”)发现莫高窟藏经洞的经过。
根据姜亮夫先生《莫高窟年表》一书所收《王道士荐疏》的记述,王圆箓在这篇上报天恩佛祖的疏文中,具体陈述了自己发现藏经洞的确切时间,是在光绪“贰拾陆年伍月贰拾陆日清晨”。当时的中国处在清朝末年,还没有使用公历,这里所写的年月日,毫无疑问是用的旧历。余先生把“光绪二十六年”折算成公历1900年,毫无问题,但他显然没有想到,跟在光绪年号后面的“五月二十六日”也是阴历。阴历的日期不经折算,怎么能原封不动地搬到公历“1900年”后面去呢?这种阴阳混杂、不伦不类的写法,说明余先生完全缺乏两种历日必须折算的知识。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如果要用公历来表示,按照历表的推算,应当是1900年6月22日。
《山居笔记·苏东坡突围》:“一○七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