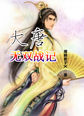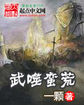余先生这段文字,写的是苏东坡在“乌台诗案”事发后,朝廷派人来湖州逮捕他的情景。据孔凡礼《苏轼年谱》记载,当时东坡正在湖州知州任上,逮捕他的时间是“宋神宗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这个日期,不言而喻是旧历(阴历),但余先生在改用公历来表述时,也只将“元丰二年”改为1079年,而把阴历的月、日原封不动地照抄了过来。其实后者应当折算成阳历8月27日。其错误性质,与上例完全相同。
下面再举一个更典型的例子:
《山居笔记·天涯故事》:“先说李纲。宋高宗时做宰相,后来宋高宗自己改变了主意,也就把他流放到海南岛万安(今万宁)来了。一一二八年十一月李纲和儿子渡海到琼州,向人打听万安的去处,人家说,万安离这里还有五百里路程,僻陋之地,去了根本找不到生活用品。走山路过去难免遭到抢劫,一般人总是先到文昌搭海船过去,如果运气好遇到顺风,三天可以到达那里。李纲一听,大吃一惊,已经到了琼州竟然还有那么多艰难的路程要走!他摇摇头长叹一声,先找一个地方住下来准备上路,没想才三天,大陆方面来人急急通报,他已经被赦免了。那是求之不得的大喜事。涕泪交加地高兴了好几天,选了一个吉日,于十二月十六日渡海回去,在海南岛共逗留了三十来天,像一次短期旅游。”
余先生在这一大段文字中,写了李纲从拜相到被贬,流放海南,与儿子一起渡海踏上琼州,又喜获赦免,再渡海返回大陆的整个过程。读起来情节连贯,让人感到这些仿佛都发生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这个过程前后长达三年,即从宋高宗建炎元年到建炎三年。现在,我把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和《梁溪集》所附李纲年谱、行状中的有关史料,向读者作一个概括的介绍,看看余先生这段从古书中演绎出来的情节有些什么纰漏。
李纲是在宋高宗建炎元年五月甲午(五日)被任命为宰相的,六月己未朔(一日)入朝执政,到八月乙亥(十八日)免官。他在这个职位上实际只干了70多天。罢相以后失去了权力,但他并没有随即被流放到海南,而是蒙恩“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这是宋朝对落职宰相的一种安置,只领俸禄而无实务,仍然居住在临安(当时称为“行在”,意思是临时都城,即今浙江杭州)。十月八日,受殿中侍御史张浚弹劾,革去“观文殿大学士”头衔,但仍然保留“提举洞霄宫”之职。他的家基本上在临安,有时也去常州、无锡等地暂住。由于张浚劾奏他在常州名声极大,无锡知县郗渐甚至到郊外迎候,设宴慰劳,怕他蛊惑人心,影响社会安定,提出当“置之岭海”(即贬斥到岭南或海南)。十二月二日,朝廷的命令下达,也只是将其遣往“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居住”。(以上史料见《要录》卷五、卷八、卷十)
建炎二年十月以前,李纲以“银青光禄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之职,居住在鄂州。当时,原侍御史范宗尹也贬在鄂州。朝廷有旨:左降官(贬斥的官员)不得居同郡,于是在十月间将李纲移往澧州(治今湖南常德市澧县)居住。可能过去李纲在鄂州时经常离家去东南故居同旧友交往,这次又没有及时迁居澧州,所以御史中丞王绹上章弹劾李纲“经年不赴贬所”,又重提他过去执政时的三大罪状,请宋高宗“投之岭海”。十一月四日,朝廷终于下令将李纲“责授单州(今山东单县)团练副使、万安军(今海南省万宁市北)安置”。(以上史料见《要录》卷十八、李纲“年谱”)
即使在这道朝令下达以后,李纲也没有立即前往万安,而是一再拖延,迟迟不想动身。他的行踪不得而知。根据历史文献的简略记载,我们只知道建炎三年六月一日在其长房长孙李震出生的那天,他还逗留在海峡北面的雷州(今广东省雷州市)。直到十一月下旬,他才乘潮南渡,踏上了琼州的土地。在《梁溪集》卷一三三里,收有李纲所作的《武威庙碑阴记》,详细记载了他这次海南之行的经过和日程。这篇碑记,可以肯定是前面所引余先生那段文字的蓝本。兹将原文迻录如下:
故翰林学士承旨苏公谪儋耳(今海南省儋州市),既北归,作《汉伏波将军庙碑》,言两伏波(指西汉路博德、东汉马援,均封伏波将军)皆有功于岭表,庙食海上,为往来济者指南。辞意瑰伟。自作碑造今,凡三十年未克建立,盖阙典也。余以罪谪万安,行次海滨,疾作,不果谒祠下,遣子宗之摄祭。病卧馆中,默祷于神,异时傥得生还,往反无虞,当书苏公所作碑,刻石庙中,使人有所观考,以答神贶。时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有五日。既得吉卜,夜半乘潮南渡,诘旦(二十六日早晨)次琼管(即琼州),恬无惊忧.后三日(二十九日),祗奉德音(圣旨),特恩听还。疾良愈,躬祷行宫,卜以十二月五日己卯北渡,不吉;再卜六日庚辰,吉。己卯之昼,风霾大作,庚辰乃息。日中潮来,风便波平,举帆行船,安如枕席,海色天容,轩豁呈露,不一时已达北岸,乃知神之威灵,肸蠁昭著若此。苏公之言,信不诬也……故并记于此,岁次己酉(建炎三年)季冬十二日,武阳李某记。
通过前面所引《要录》、“年谱”等历史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李纲的罢相,是在建炎元年八月十八日;而下达将他责授单州团练副使、万安军安置的命令,是在建炎二年十一月四日;至于他在儿子宗之的伴同下乘潮渡海到达琼州,则在更后的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这前后三年里断续发生的事情,都被余先生稀里糊涂地一锅煮了!
现在再着重谈谈阴阳历日混杂的问题,看看余先生是怎样用公历来记载李纲的琼州之行的。李纲的《武威庙碑阴记》所用历日肯定是旧历。他说自己是在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半乘潮南渡,二十六日早晨到达琼州的。这两天折算成公历,应当是1130年1月6日和7日。余先生怎么会记作“一一二八年十一月”的呢?看来他犯了双重错误:
其一,他弄不清李纲罢相和万安军安置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年份,其间相距有一年多时间。他看到有些资料上说李纲于建炎二年十一月“责授单州团练副使.移万安军安置(见‘年谱’)”,就贸然地把两件事情混在一起,将“建炎二年”折成了“一一二八年”。
其二,他不知道古书上记载的月、日都是阴历,如果改用公历来表示,必须根据历表的规定来折算,绝对不能按原文照抄。对于阴历十一月来说,如果是月末,则折成公历肯定在12月甚至第二年的1月。余先生不问青红皂白,只顾照着古书一抄了事,哪能不出纰漏呢!
此外,按照《武威庙碑阴记》的记载,李纲择吉渡海北归大陆的日期,明明写着建炎三年十二月六日,你不去折算成阳历已经是个错误,怎么还要莫名其妙地把“六日”抄成“十六日”呢?这种错上加错的低级差错,即使是一个中学生也不容轻犯,现在都出现在备受莘莘学子青睐和崇敬的余先生笔下,怎么能说得过去!
像这样阴阳混杂、不伦不类的历日表述,在余先生的散文中是屡见不鲜的,限于篇幅,我不再一一列举了。总之,由于他完全不了解当代历史研究中这个普通的常识,所以只要作品中遇到此类问题,就必错无疑。我在本文开头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绍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就是专门为余先生写的。希望他无论如何能拨冗一阅,再向图书馆借一本《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社1987年版)备在案头,遇到问题随时翻检折算。我想,这样的差错,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