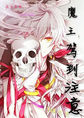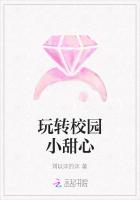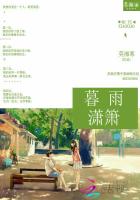写完了《唐代纪年为什么一度用“载”?》以后,感到意犹未尽,特补作馀话。
唐代纪年改“年”为“载”,从玄宗天宝三载(744)正月起,到肃宗至德三载(758)正月止,前后共14年又1个月。掌握了这一知识,对于辨识古籍和现代书刊中的有关错误,以及古器物的辨伪,都有一定的好处。试举数例:
一、《唐代墓志汇编》“天宝○三九”载《故和上(尚)法昌寺寺主身塔铭序》云:“〔圆济和上〕以天宝二载癸未岁冬十二月遘疾……至廿八日,泊如长逝。”
按:“天宝二载”应称“天宝二年”,当时尚未改“年”为“载”,怎么能称“载”呢?揣其文意,圆济和尚逝世于十二月廿八日,当时距离年终仅只二日,墓志作者撰写志文,特别是雕刻上碑时,肯定已在次年。而次年之正月一日,玄宗改“年”为“载”的诏书即已下达,撰文者不敢不遵行,只好将“年”字写作(或刻作)“载”字。这样就背离了史实,将改“年”为“载”的时间推前了一年,容易引起误解。
二、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云:“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别驾元持宅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开元五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
按:“开元”只称“五年”而不称“五载”,因其时唐玄宗尚未下诏改字。查杜诗主要版本,各家所录除“五”一作“三”外,“载”字均不作“年”。“载”与“年”字形迥异,不会因刊刻致讹,当是杜甫误记造成。此诗作于代宗大历二年(767),杜甫56岁。开元五年(717)时年仅6岁,前后相距整整50年,其间经过了14年改“年”为“载”的时代,杜甫以眼暗耳聋的衰病之身,回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可能将天宝三年(744)改“年”为“载”误记为开元初年之事,因而造成了这样的差错。此误历来很少人指出,唯南宋赵次公在注中将“载”改为“年”,当是心知其误而未明言之。
三、叶梦得《避暑录话》载:“长安李士衡观察家藏一端研,当时以为宝。下有刻字云:‘天宝八年冬。端州东溪石。刺史李元书。’刘原父(名敞,字原父)知长安,取视之,大笑曰:‘天宝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称载矣。且是时州皆称郡,刺史皆称太守,至德后始易。今安得独尔耶?’取《唐书》示之,无不惊叹。李氏研遂不敢复出。”
按:以宋代新砚冒充唐代端砚,作伪者手段并不高明,但如不知唐天宝改“年”为“载”等史实,自然难免上当。可见古器辨伪,除器物之质地、形制及镶刻工艺等知识外,掌握其款识中有关的典制史实,也是重要的门径。《旧唐书·地理志四》云:“〔端州〕天宝元年(742),为高要郡。乾元元年(758),复为端州。”《通典·职官典十五》云:“天宝元年,改州为郡,刺史为太守。”肃宗至德三载改元乾元,可证《避暑录话》“是时州皆称郡,刺史皆称太守,至德后始易”之说确凿无误。唯文中刘原父所云“天宝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称‘载’矣”一语略有疵病。因玄宗下达改“年”为“载”诏书在天宝三载正月一日,天宝元年、二年仍称“年”,并非“自改元即称‘载’”。
四、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地名语源词典》第44页“平山”条释文云:“汉蒲吾县地,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析置房山县……唐至德元年(756年)改为平山县……《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天宝十五载(756年)三月,‘改常山郡为平山郡……’”
按:释文引《旧唐书》称“天宝十五载”,符合史实。但将“载”回改为“年”是在肃宗至德三载(758)二月,则至德元载仍应称“载”而不当称“年”,释文中“至德元年”的写法是不妥当的。
余秋雨先生确实是一位文章高手。庄周先生在《齐人物论》一书中评价说:“作为当代一个重要的散文家,他的文笔和才情是不容置疑的。”此话我也有同感。但“文章高手”并不一定能保证其用语的准确和规范;散文家的“文笔和才情”也往往掩盖不住由于轻率粗疏而造成的词病。
责人的大师何以不严于律己?
余秋雨散文引书差错二十七例
先哲韩愈有言:“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宽以约。”(《原毁》)在人与人之间相处交往的问题上,这是一句可以传之久远的至理名言。
余秋雨先生待人如何,从他与别人起伏不断的笔墨官司中已可略知一二,且不去说他。这里,我只想从引用古书的小事上,谈谈他是用什么标准来律己的。
余先生在《山居笔记·遥远的绝响》中写道:
一天,他(阮籍)就这样信马由缰地来到了河南荥阳的广武山,他知道这是楚汉相争最激烈的地方……阮籍徘徊良久,叹一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他这声叹息,不知怎么被传到了世间……直到二十世纪,寂寞的鲁迅还引用过。毛泽东读鲁迅书时发现了,也写进了一封更有寂寞感的家信中。鲁迅凭记忆引用,记错了两个字,毛泽东也跟着错。
这里,余先生对他认为在引用古书时出了差错的鲁迅和毛泽东进行了婉转的批评。他的意见是否正确呢?
我的看法是:关于引用古书的问题,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需要作具体的分析。
余先生所引阮籍临广武而叹息的那句话,可以从现存的古籍中查到。其较早的版本,大致有以下两种:
《三国志·魏志·阮瑀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乃叹曰:‘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
《晋书·阮籍传》:“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裴松之注所引《魏氏春秋》,是东晋孙盛所著,而《晋书》乃唐初史臣奉诏纂修的,时代要比《魏氏春秋》晚得多。因此两书所载阮籍叹息的话,似当以前者为准。《魏氏春秋》上句中的“英才”,《晋书》改作“英雄”;《魏氏春秋》下句末有语气词“乎”,《晋书》则把它删去了。严格说来,后者似乎记错了两个字。但《晋书》的作者没有像裴松之那样明讲引自《魏氏春秋》,这种引书的方式叫“暗引”。“暗引”的事比较难说,也许它当时确实别有所据呢。所以,过去没有人认为《晋书》出了差错,最多说它是异文。余先生引用的文字,虽然不合于《魏氏春秋》,但却与《晋书》完全相同,加上他也是暗引,因而同样不能算错。
再看鲁迅和毛泽东的引法:
鲁迅《准风月谈·后记》:“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
毛泽东1966年8月7日致江青的信:“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经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