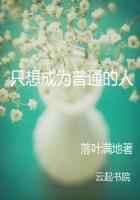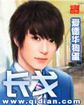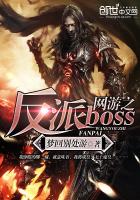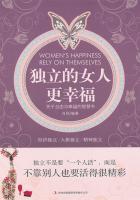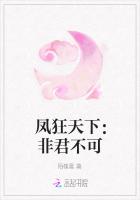慈济拓展至全球的慈善济世志业,是从花莲起家,由日省5毛钱(折合人民币不到一毛钱)的“竹筒岁月”走过来的,带动了各地善心人士承先启后,呼应慈济大爱于天下的善行,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跟着慈济在各地做善事,蔚为一股可敬可观的力量。
证严法师生于1937年,26岁落发出家;3年后,她从一个小小的愿心出发,带领着信众,开启了“慈济”救苦救难的善行大业。
26岁之前,她是王锦云;26岁之后,她是证严法师。两段迥异的人生,两段传奇的经历。
她是中国台湾台中清水人,幼年过继给叔父。养父经营多家戏院,业务繁忙;她是长女,20岁不到就得替父亲分劳,并料理家务。
15岁时,她的养母罹患胃穿孔,必须开刀治疗。她为了替母亲祈福消灾,开始持诵“观世音菩萨”名号,发愿以自己的12年阳寿来换回母亲的健康。
尔后她一连三天作了同样的梦,梦到一位慈祥的女子,赐药给她母亲;后来她母亲果真不药而愈,她从此开始吃素,但当时并未信佛,只是出于一片纯孝。
5年后,她父亲51岁时,因高血压病故。她悲伤之余,思索生命是怎么回事?一向健康的父亲,一口气咽下就再也不能呼吸了,为什么人生这么无常?死亡到底是什么?人死后又去了哪里?
从此,她信了佛;继而不顾家人反对,决意出家。1963年,她拜高僧印顺长老为师,获赐法名证严,字慧璋,受了32天比丘尼具足戒。
回花莲后,她住进许老居士在地藏殿后面盖的小木屋修行,每天礼拜《法华经》,以报答生养她的两对父母,和陪她修道法师及许老居士的恩情;每月写一部法华经,为众生回向。
后来她移单到慈善寺讲地藏经,结识许多佛门弟子。
1964年秋天,她带着几个弟子回地藏殿修行。她们不赶经忏、不作法会,也不化缘,完全自力更生。到工厂拿材料加工打毛衣,或把水泥袋改装成装饲料用的小型纸袋,后来又增加制作婴儿布鞋,以维持常住生活。
不多久,当地一名山地妇女小产,因无力缴付8000元(台币,下同)医药费,留下一摊血的故事,受这件事冲击,她惊觉钱财虽是身外之物,却也能救人性命。
问题是,尽管悲悯贫病苦痛苍生,怎奈需要帮助的人何其多!
有一天,三名天主教修女来访,她们赞同佛教的慈悲精神,但认为佛教徒较保守,不似西方宗教徒活跃。这使得证严法师暗暗立誓,独善其身是不够的,还应该实际为芸芸众生做点事。
适时印顺导师希望证严法师到他嘉义妙云兰若的道场,消息传出后,大家舍不得她离开,集合了30名信众挽留她。
这让证严法师想到“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这句话,把每个人的慈悲心都启发出来,组成一个500人的团体,不就等于菩萨的一千只眼睛和一千只手吗?那么阴暗角落苦难的众生,不就可获得救助了吗?
她因而向信众说,她可以不离开花莲,但要帮她具体做些实事,落实她“济贫救世”的心愿。
她的初步构想是,与5名同修弟子,每人每天增产一双婴儿鞋,每双可卖台币4元,6个人可多赚24元,一个月就有720元,一年可多出8640元。有了这笔钱,就可以拯救像那山地小产妇女的一条性命了!
她并呼吁30名信众,每人每天上市场买菜时,先在竹制的存钱筒内存进5角钱,30个人一个月可存450元,加上增产婴儿鞋的每月720元,一个月就有1170元的基金了,大家发挥聚沙成塔的力量,就可以“济贫救世”了!这个构想获得了认同与支持。
1966年2月19日开始,“家庭主妇出门前先丢五毛钱在竹筒里”的这件事,在花莲各菜市场很快就传开了,获得很大的回响,参与的人愈来愈多。
农历3月24日——证严法师每月诵药师经回向日,成立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所谓“克难”,亦即“一针一线”缝制婴儿鞋、“一角一毛”节省买菜钱来凑基金的意思;从那天起,慈济救助的工作无休无止地展开了!
那年她29岁,从此长住花莲,不言离去。
中国台湾花莲县新城乡康乐村的静思精舍,是盛名远播的“慈济”发源地。40多年来的济贫解困事迹,恩泽广被,使得这座建筑散发着耀眼的万丈光芒。
证严法师受戒之后,原本发愿一不作法师、二不作住持、三不收弟子,也不受在家人皈依;可是“功德会”的成立,会员深受证严法师牺牲无我的悲悯情怀感动,纷纷要求剃度或皈依,证严法师为了“功德会”的因缘,只好破例接受皈依,条件是皈依者,必须作“慈济功德会”的成员,并实际负起“慈济功德会”的社会救济工作。
一时之间,她的白衣弟子急速增加,“慈济功德会”的工作大幅成长。
“功德会”救济的对象包括长期与急难救助。只要发现需要救济的个案,就在每个月举行的委员联谊会中提报讨论;若是临时紧急个案,则由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决定。“慈济功德会”秉持“救人救到底”的原则,绝不半途而废、有始无终;这个原则沿袭至今。
1966年4月初,功德会的第一个长期救助个案对象,是一位从大陆来台、86岁孤苦无依、不能行动的林老太太,慈济每个月帮助她300元生活费外,请人帮她烧饭洗衣,照应她的生活起居,直到1970年2月往生为止。
第二个领受慈济恩泽的是那年5月的“急难送医”个案。慈济负担5000多元的旅费、伙食费及手术费,协助患青光眼的菜贩卢丹桂,到罗东五福医院开刀。
遗憾的是,半年后,卢女士因细故与先生口角后寻短见;慈济致送1200元慰问金及一床棉被,每个月发给白米二斗,安定苦主和5个女儿的生活;直到来年6月,其夫收入好转才中止。
由此经验,以后对于贫户个案,慈济每三个月复查一次,一方面给予精神上的安慰与关怀,另一方面视其生活状况,增减其补助。
推动慈济工作,是采“委员制”方式。出任慈济委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正知正见,无不良嗜好。
二、能拨出时间从事济贫教富的工作。
三、能有“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的深切体认,言行举止端庄合宜。
四、遵守诚正信实的工作精神,并担任见习委员及培训委员合达两年以上。
慈济委员的任务,必须协助推动会务,以及参与所属地区分会各项活动及会议,还有劝募善款,发挥慈悲喜舍予乐拔苦的精神;访查、复查低收入户;慰问急难灾户病患。
早期的委员大都属家庭主妇,识字不多,仅是凭着一股信念,以极浅显直接的言辞向人介绍:“有位师父要救济贫民,很伟大,没有人能这样做!”善款则是5元、10元的点滴累积。
这些委员靠的是两条腿,不辞辛苦地各处奔走。这期间,有鼓励、有温暖;也有挫折和误解的白眼。他们主动地去发掘需要救助的对象,适时施予援手;40多年来,领受过慈济德泽的贫户不知凡几,许多人即因心存这份感念,也自愿加入慈济的行列,再去帮助比他们更穷更苦的人。
慈济爱的力量,如海潮般的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而慈济的会员亦由原先的家庭主妇,到如今的社会贤达,每个人都深受证严法师无私无我精神的感召,全力奉献自己的心力。
“这一切,该感谢的是师父,她不仅是救贫,同时也教富,是她老人家的慈悲,才让我们这些人有福田可耕。”
“师父的担子这么重,所以,那怕是些微的力量,也都是慈济最需要的……”
就是这份共识,成就了远近驰名的慈善事业。
慈济功德会刚成立时,是在秀林乡佳民村警察派出所后面不到66平方米空间的地藏殿(即普明寺)里,除常住的出家人要在这里做加工品之外,功德会也经常需要利用这个地方处理一些事务;加上每月发放救济米,以及每月24日所举办的一次“药师法会”。
平时证严法师不为人家赶“经忏”或“请托诵经”,所以参加“药师法会”的人异常踊跃,狭小的空间实在不敷使用,解决功德会的场地问题,成了当务之急。
为此,证严法师向俗家的母亲提出了经济支持的请求,而她母亲也以慈爱、宽大、谅解的胸怀表示:“女儿出嫁要嫁妆,出家当然也需要护持。”为她解决了困难。
1967年的秋天,她贷款买下目前精舍所在地近1.5万平方米的土地,距普明寺约200米。自此,这些常住的出家人除生活费外,还要偿还银行的贷款与利息,负担加重了,工作也更为劳苦,除在原有的五分旱地种植花生之外,另种植了一甲半的水稻,并且多接了一些织棉纱手套等手工。
生活如此清苦,所募得的善款仍全数纳入“济贫基金”的专户;那一年7月20日创办的“慈济月刊”,除刊载有关会务报导之外,并刊载善款帐目。
1969年,慈济功德会的会员日益增加,普明寺已不敷使用,证严法师的俗家母亲又伸出了援手,资助功德会兴建静思精舍。从此慈济功德会才算有了自己的“家”,成为后来慈济志业发展的根基,并成为“慈济功德”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