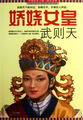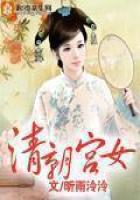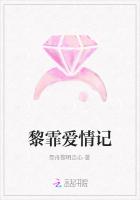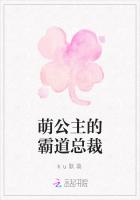苏东坡年二十中进士,可谓才气纵横。在仕途上,他一开始就遭遇挫折,但他能够耐心等待时机。在他担任凤翔府判官、杭州通判、徐州太守的任上,他领导群众抗旱抗洪,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并能为民请命,以减少人民的负担,体现了他爱民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尚品德。他不仅爱天下百姓,也爱自己的亲人,爱兄弟、妻子,爱那些出生卑贱之人,如歌女等,体现了他博大的爱心。他恪守为政之道,不搞朋党,对百姓宽厚仁慈,深得百姓的拥护与爱戴。同时,他在文化上努力进取,成为一代文坛盟主,并培养了大批优秀文化人才。但因为苏东坡为政刚直,实事求是,因此得罪了朝中推行新政的王安石一党,这成为他后半生的贬谪之旅的发端。
苏东坡进士及第后,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县)主簿,主簿是帮助知县处理文书,办理具体事务的九品官。按理说苏东坡也算是进入官场了,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苏东坡不这样认为,没有去上任。欧阳修十分奇怪,问他为什么不去赴任。苏东坡说:“伯父(苏涣)教导我们,做官就像作文一样,得到题目后,要考虑成熟后才能下笔,这样写出的文章才是好文章。现在授予我主簿的职位,官职小,事务杂,难度很大,觉得既无从下手,又难以施展,所以推辞。”听完苏东坡的解释,欧阳修赞叹道:“好,有志气。那我推荐你参加秘阁的制科考试如何?”苏东坡十分高兴,赶忙拜谢欧阳修,并保证一定不让他失望。
苏东坡果然争气,顺利地通过了秘阁考试。在仁宗皇帝御试时,他的一篇《御试制科策》又被列入三等(最高等次)。自宋王朝建国以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前朝宰相吴育和苏东坡两个人。
苏东坡应制科考试后不久,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大理评事是掌管刑狱的京官,签书判官是州府幕职,掌管文书,佐助州官。这是以京官身份去州府签判,比起前次所授的河南伊阳县主簿来,职位明显提升了,而且也更能展示他的才能,苏东坡感到很是满意。
很快就到了苏东坡携妻带子离开京城的日子。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偕同妻子在开封侍奉老父。行期那天,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为兄嫂赴任送行,苏辙与哥哥自小一起长大,从来没有分开过,兄弟二人感情特别的好,而今要第一次分开,自然非常舍不得。直到离开封四十里外地方,兄弟二人为平生第一次分手,各尽杯中之酒,然后苏辙回京,苏东坡打马上路。
苏东坡停马在土坡上,望着弟弟在雪地上胯骑瘦马,头在低陷的古道上隐现起伏,直到后来再不能望见,才赶程前进。苏东坡想到很久不能见到弟弟,异常的感伤,他到达凤翔寄给弟弟的第一首诗写的是: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扰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陇隔,惟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风雨对床”之思,在唐人寄弟诗中有之,此种想法成了兄弟二人团聚之乐的愿望,也是辞官退隐后的理想生活。后来有两次弟兄二人又在官场相遇,彼此提醒在诗中曾有此“风雨对床”之约。后来,苏氏兄弟去世,都埋葬在一起,真正是“风雨对床”了。
由京都到凤翔的函件,要走十天才到,兄弟二人每月经常互寄诗一首。由那些诗函之中可以看出,初登宦途时的苏东坡,对弟弟的思念之深,感人肺腑。
古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之训,同样的道理,一族不济,又何以济苍生?只有热爱自己的亲人,才能推己及人,兼爱天下大众。正因为苏东坡有这份难得的亲情爱心,推及到天下人,从而使他拥有一颗爱民的心,让他自己在为官的生涯中,时刻不忘为民多办事,办实事。也正是苏东坡以博爱之心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他才会有对国家的耿耿忠心、尽职尽责、冒死直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