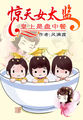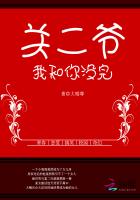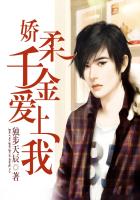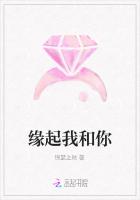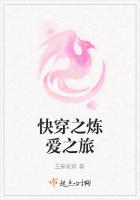有一句著名的格言:“真理诞生于100个问号之后。”这句格言本身,就是一条真理。人们都很尊敬发现真理的人。其实,真理常常就在你的身边,看你有没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有没有一个善于思索的头脑,有没有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
可惜的是,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中国人的看法十分明确,那些看起来十分奇怪的事情,只要看多了,发生“审美疲劳”了,就自然不会觉得奇怪了。既然如此,那些看起来本身就很平常的事情,就更不能引起中国人的求知欲了。
中国人的“审美疲劳”思维,是中国人创新的大敌,也是中国人突破常识对自己认知能力束缚的大敌。然而,一代代的中国人,正是在对司空见惯的事情不感兴趣的情况下,慢慢失去了发现真理的能力。
然而,那些对一切充满好奇心,不放过任何一件微小事件的人,则是成功的幸运儿。他们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没有受到“审美疲劳”思维的影响,而是让自己的思维一直处于保鲜状态。
就拿洗澡来说,可谓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洗完澡,把浴缸的塞子一拔,水哗哗地流走,谁也不会去注意它。然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的系主任谢皮罗教授,却敏锐地注意到:每次放洗澡水时,水的旋涡总是向左旋的,也就是逆时针的。谢皮罗紧紧抓住这个问号不放。他设计了一个碟形容器,里面灌满水,每当拔掉碟底的塞子,碟里的水也总是形成逆时针旋转的旋涡。这证明放洗澡水时旋涡朝左,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
1962年,谢皮罗发表论文,认为这旋涡与地球自转有关。如果地球停止自转的话,拔掉澡盆的塞子,水不会产生旋涡。由于地球是自西向东不停地旋转,而美国又处于北半球,所以洗澡水总是朝逆时针方向旋转。谢皮罗由此推导出,北半球的台风,同样是朝逆时针方向旋转的,其道理与洗澡水的旋涡是一样的。他断言,如果在南半球,则恰好相反,洗澡水将按顺时针形成旋涡;在赤道,则不会形成旋涡。
谢皮罗的论文发表之后,引起各国科学家的莫大兴趣,纷纷在各地进行试验,结果证明谢皮罗的论断完全正确。
一位名叫密卡尔逊的生物学家,调查蚯蚓在地球上的分布情况,发现美国东海岸有一种蚯蚓,欧洲西海岸同纬度地区也有同样的蚯蚓,但在美国西海岸却没有这种蚯蚓,他无法回答这究竟是为什么?密卡尔逊提出的这个问题,引起了德国地质学家魏格纳的注意。当时,魏格纳正在研究大陆和海洋的起源问题。他认为,那小小的蚯蚓,活动能量很有限,无法横跨大洋,它的这种分布情况揭示了这样一个秘密: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后来才裂开分为两个洲。他把蚯蚓的地理分布作为例证之一,写进了他的名著大陆和海洋的起源一书。魏格纳从蚯蚓的分布,推论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也正说明他的成功在于从日常的现象中寻求真理。
最为有趣的是,一位奥地利医生看到儿子睡觉时,忽然眼珠子转动起来。他感到奇怪,连忙叫醒了儿子,儿子说他刚才做了一个梦。于是这位医生想,眼珠子转动会不会与做梦有关呢?为了解开这个谜,他把儿子当成了“试验品”:每当儿子睡觉时,便守在旁边,一旦发现儿子眼珠子转动,就叫醒他。儿子总是说做了一个梦。后来,医生又细细观察了他的妻子和邻居,都发现同样的情况。于是,他写出了论文,指出当人们入睡时,如果眼珠子转动,一定是在做梦。他的论文引起了各国科学家的注意。如今,人们研究梦的生理学,使用眼珠子转动的次数、时间,来测量人做梦的次数和梦的长短。
在科学史上,这样的事例岂止3个?它说明科学并不神秘,只要你见微知著,那么,当你解答了日常生活的100个问号之后,必能发现真理。
有些时候,我们的“审美疲劳”思维,不但表现在我们对日常现象的漠视,更是表现在我们对某些特殊现象缺乏想象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人,才能挣脱“审美疲劳”的枷锁,放飞自己的思维。
1872年的一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酒店里,斯坦福与科恩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马奔跑时蹄子是否都着地?斯坦福认为,马奔跑时始终有一瞬间四蹄是腾空的;科恩却认为,马奔跑时始终有蹄着地。争执的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就采取了美国人常用的方式——打赌——来解决。他们请来一位驯马好手来作裁决,然而,这位裁判员也难以断定谁是谁非。这很正常,因为单凭人的眼睛确实难以看清快速奔跑的马蹄是如何运动的。然而,裁判的好友——英国摄影师麦布里奇知道了这件事后,表示可由他来试一试。他在跑道的一边安置了24架照相机,排成一行,相机镜头都对准跑道;跑道的另一边,他打了24个木桩,每根木桩上都系了一根细绳,这些细绳横穿跑道,分别系到对面每架照相机的快门。
当准备就绪之后,麦布里奇牵来了一匹骏马,让它从跑道一端飞奔到另一端。当跑马经过这一区域时,依次把24根引线绊断,24架照相机的快门也就依次被拉动而拍下了24张照片。麦布里奇把这些照片按先后顺序剪接起来。每相邻的两张照片动作差别很小,它们组成了一条连续的照片带。裁判根据这组照片,终于看出马在奔跑时总有一蹄着地,不会四蹄腾空,从而判定科恩赢了。
按理说,此事到此就应结束了,但这场打赌及其判定的奇特方法却引起了麦布里奇很大的兴趣。麦布里奇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出示那条录有奔马的照片带。一次,有人无意识地快速牵动那条照片带,结果眼前出了一幕奇异的景象:照片中那些静止的马叠成了一匹运动的马,它竟然“活”起来了。
生物学家马莱从这里得到启迪。他试图用照片来研究动物的动作形态。当然,首先得解决连续摄影的方法问题,因为麦布里奇的那种摄影方式太麻烦了,不够实用。马莱是个聪明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后,终于在1888年制造出一种轻便的的“固定底片连续摄影机”,这就是现代摄影机的鼻祖了。从此之后,很多发明家将眼光投向了电影摄影机的研制上。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大咖啡馆”第一次用自己发明的放映摄影兼用机放映了火车到站影片,标志电影的正式诞生。而斯坦福与科恩的打赌事件如同使这些科学技术糅合在一起发生巨变的催化剂,迅速导致了电影综合技术的出现和产生,使电影这门伟大的艺术叩响了20世纪的大门。
观看奔马照片的人很多,但是只有马莱从中悟出了连续摄影然后当作电影播放的道理,这并不是因为他聪明过人,而是因为他能够从一些现象中,产生别人所没有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就是对“审美疲劳”思维的克服。
无论是从日常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找到不平凡的因素,并且从中发掘出创新的因子,还是从那些比较奇特,但常人并不注意的事物中寻找到创新的源泉,都是十分难得的,尤其是对中国人而言,要克服旧有的对身边现象的“审美疲劳”,从小事开始观察,从你最有想象力、最有心得的地方入手观察,不失为一种高明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