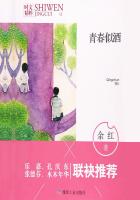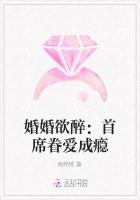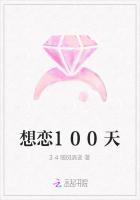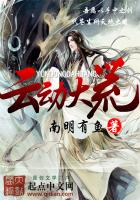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由教育界转入社科界,开始了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二个职业。因工作的关系,我开始接触区域历史文化。涉猎和研习炎帝、姜炎文化。我原是学文的。虽“文”“史”有联系,但毕竟是属于两个学科。起初,我对炎帝文化的涉猎。可以说只是看作为完成领导交给自己的一项工作。因炎帝、姜炎文化要涉及上古史的诸多方面,对我这个“门外汉”来说。自然谈不上什么研究。但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展开,通过参与《炎帝·姜炎文化》一书的编写,尤其是通过编纂《炎帝史料辑录》,对有关炎帝方面的史料也开始有所了解。接着,于1994年下半年,与另一位先生合作撰写了一本16万字的《炎帝传》。此书出版后,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为我继续在炎帝、姜炎文化研究道路上走下去增加了信心。从此。我对研究炎帝、姜炎文化以及黄帝文化产生了兴趣,而且这种兴趣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愈来愈浓厚。结果没有想到,一干就是近20年。先后或参与或主持召开了八九次有关炎帝、姜炎文化学术研讨会,也先后应邀到外地参加了10多次炎黄文化的学术研讨会。为了应付学术研讨会和有关刊物的约稿,也陆续撰写了几十篇论文。这些论文有些是对炎帝其人其事的考证,有的是对姜炎文化的探讨,而更多的是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思考炎黄文化的内涵、特征和意义。此外,还有一部分论文是对地域历史文化和旅游文化的思考。尽管这些论文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缺点、错误,但它毕竟浸润着我的半生心血,烙印着我的思想,所以也就没有了“丑媳妇怕见公婆”的顾虑。从去年开始,有了将这些散见于报刊或论文集中的论文集中起来,编辑成册的想法。于是,经过半年多的整理,今年初完成。没想到,拉拉杂杂竟也有五六十万字。今年正逢我甲子之年,是我人生道路的又一转折。喜也,悲也,实难道明矣。这本书也就算成了我对自己六十年的一个总结和交待。
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炎帝·姜炎文化”。这部分是近20年来陆续所写的研究炎帝、姜炎文化方面的文章。有关炎帝诸方面的问题基本上涉及到了。这些文章多为刊物已发表或在有关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并收入论文集。第二部分“区域历史文化”。为应邀参加全国学术研讨会所写的文章。内容相应来说要比较杂一些,但也未离开我所研究的范围。第三部分“旅游文化”。主要是为有关部门和单位召开的研讨会或座谈会所写文章。其中有些在当地报刊已发表。这三部分文字从表面看,似乎无多大的联系,实际上,除了个别篇目外,都是炎帝、姜炎文化研究的延伸和扩展。
这里还需要提及的,有关炎帝、姜炎文化的研究,因前后延续十几年。对有些问题的认识,随着研究的深入,可能有所变化。为了保持当时的面貌,这次结集时,未作改动,只在个别字句方面做了一些调整。再还需要说明的,当时是以单篇文章写的,现在收集在一起,个别篇目在文字上难免有雷同之处。但为了保持每篇文章内容的完整性,只好保存下来,敬请读者谅解。
我生于周文化发祥地扶风渭河岸边的一个村子。家里世代为农,父母也是以农为业,到我这一代才有了上学的人。我爱我的父母,也爱生我养我的这块古土。父母虽不能给我以学习上的辅导,但我从他们身上却学到了正直、刚强做人的品德和对工作、事业的敬业精神。回想我这40多年来所从事的工作,不管是干教育,还是搞研究,或是做其他事情,从不敢偷懒,不敢懈怠,可以说。这与父母对我的感染不无关系。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很感激、怀念我的父母。若说有什么成绩,是与他们对我的养育、教育分不开的。尤其我到了“耳顺”之年,就更思念父母对我的恩德了。尽管父母已离世多年,但他们对我的那份情、那份恩,却时刻萦绕在我心头,浓而不化,挥之不去。
写到这里,我不免又想起多年相识相交的学人师长和朋友,我所取得的这一点点成绩也是与他们的鼓励、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着名中国思想史家张岂之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学者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初结识后,至今还保持着联系。我们筹办的多次学术研讨会。都是遵照先生为我们拟定的题目做的。先生睿智的思想。大家风范,是我永远的良师益友。为此,在纪念先生八十华诞之际,应邀撰写了《大家风范良师益友——张岂之先生与宝鸡炎帝·姜炎文化研究侧记》一文,以表达对先生的仰慕、敬重之情。着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也是我最敬重的学者之一。我虽小于先生20多岁,但自结识的10多年里,先生从未以长者自居。始终以谦和的态度对待晚辈。我们每每邀请他参加研讨会,他都能不顾年事高迈,欣然应诺。他所写的几篇有关炎帝文化方面的文章,每次读起来,都给人以新的启示。在我的良师益友中,还有何光岳、陈连开、杨东晨等等诸位先生,我不仅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学者所应具备的真正学术良知,而且还从他们的大作宏论中吸收了有益的学术营养。在此,我还不会忘记邹衡和许启贤二位大师,虽他们不幸作古,但二位先生的名字却永远地留在了我心中。当然,在我的周围还有许许多多的同仁、好友以及有关领导,不管年长于我或年小于我,但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都程度不同地得到过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借此,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结集并不等于结束,只是一个阶段的总结。若身体允许,无其他干扰,自己还愿意将此项研究工作继续进行下去,以对自己人生有个比较满意的交待。
作者
2007年9月于苦耕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