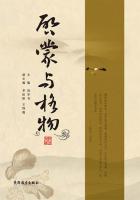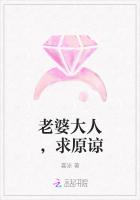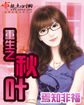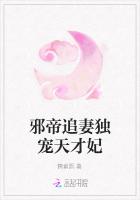所谓中华民族凝聚力是指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维系整个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与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有着血肉般的联系。它是由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结果。考察这些因素,包括有地理、经济、传统文化、共同心理状态、“大一统”思想及含有亲情、乡情、民族感情和国家感情的爱国主义思想等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使中华各族产生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从而凝结成为一个牢不可破、密不可分的整体。
但要历史地考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笔者认为,是植根于炎黄时代,起核心作用的乃是炎黄二帝。因为,炎黄二帝具有“共祖”象征作用、文化纽带象征作用和精神感召象征作用,所以,炎黄二帝及其创造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情感基础、思想基础和精神基础。
一、炎黄二帝具有“共祖”象征作用。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情感(心理)基础
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过程中,共同的心理状态即情感因素,始终起着一种牯合剂的重要作用。而这种共同心理的构成,固然有其共同地域、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但是,从历史上看,我们不能不承认,也与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文明的初曙时期起,在中华民族的宗教观念中,就明显地具有一种崇天敬祖的特点。而且,这种特点在夏商周时期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以食配天”的礼制。因而,炎帝、黄帝从很早时候起,就以“始祖”的名义受到华夏族的崇敬和祭祀。而这种崇敬和祭祀即“共祖”象征作用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
据史书记载,对黄帝祭祀最早始于有虞氏一系。《国语·鲁语上》记鲁大夫展禽的话: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韦昭注:“……有虞氏出自黄帝、颛顼之后,故禘黄帝而祖颛顼……”又注:“虞、夏俱黄帝、颛顼之后,故禘祖之礼同。”战国时有虞氏后裔的传世铜器“陈侯因脊敦”铭文有“昭(统)高祖黄帝”的文字,自称黄帝为高祖。因齐王尊黄帝,在“稷下之宫”亦形成“百家言黄帝”的局面。在商周时期,有祭祀五方天帝之礼,炎帝、黄帝等配食;秦国至灵公时,“作吴阳上畴,祭黄帝;作下畴,祭炎帝”。因鄜畴、吴阳上、下畴及密畤,位于雍城附近,称“雍四畴”,为国之大礼。秦统一后,仍重祭“雍四畴”之祀。秦末,刘邦“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刘邦入关后,以“天有五帝”而增立黑帝祠,由原“雍四畴”而变为“雍五畴”。其即帝位后多承秦制,行“雍五畴”之礼。后文帝又作渭阳五帝庙、长门五帝坛。武帝于都城长安东南郊作太(泰)一坛,坛旁祠黄帝;以后武帝又作甘泉太(泰)一坛,以“五帝环居其下”;于泰山下作明堂,以祠太一、五帝。武帝又于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北巡朔方……还,祭黄帝冢桥山”。至宣帝时,“又立龙山仙人祠及黄帝……凡四祠于肤施”。成帝时改于京都长安南郊行祭天之礼,罢各地诸祠,后又恢复旧制。哀帝时又先改后复旧。至平帝时,王莽摄政,“祭五帝于西郊”。后王莽篡位称帝,自谓黄帝之后,并立祖庙,“郊祀黄帝以配天”,天下初定“祭于明堂太庙”。东汉建都洛阳,于城南设圆坛以郊天,“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又“祀五帝于明堂”,“兆五郊于洛阳四方”并“宗祀五帝于孝武所作汶上(泰山下)明堂”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沿用汉制,各在其国都设祠坛郊天及祭祀五帝。
隋唐以后,仍行郊天及祭五帝之礼。唐玄宗敕示:“三皇五帝,创物垂范,永言龟镜,宜有钦崇。”并又诏示:“其三皇已前帝王宜于京城内共置一庙”,“以春秋二时享祭”。由此开启京都立庙祭祀黄帝等古帝王之先河。宋代因皇帝崇尚道教而有景灵宫之设。宋真宗以梦见黄帝言“是赵之始祖”为由,尊黄帝为圣祖,以筑景灵宫而奉之。并诏示:“崇饰诸州有黄帝祠庙”。宋徽宗时又于京城筑九成宫以置九鼎;并以铸鼎之地作宝成宫,“中置殿日神灵,以祠黄帝”。南宋时虽偏安临安(今杭州),仍仿旧而祭祀。元代统治者虽为异族,但为巩固其一统天下,很快接受了炎黄二帝以来的文化。元成宗继位之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并于大都(今北京)城内明照坊建造三皇庙,供奉伏羲、神农、黄帝及历代名医像。至顺帝至正十年(公元1356年),又“命祭三皇如孔子礼”。元代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以如此大的规模祭祀黄帝等,并遍置三皇庙于全国各地,这不仅前所未有,且为后世所无。
明代对传统诸礼多有改制。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帝以天下郡邑通祀三皇为渎”而罢祀。六年“帝以五帝……于京师立庙致祭”。嘉靖时,“建三皇庙于太医院北,名景惠殿。中奉三皇及四配。”将黄帝一体而三位,各以帝王、圣师及先医的名义与伏羲、神农等合祭于诸庙,但只限于京师之地。清代为满人统治,几乎全盘汉化,悉遵旧制。康熙年问,于文华殿东建传心殿,奉祀伏羲、神农、黄帝等如旧。康熙等帝亦亲祭,行三跪六拜礼。元代各州县所置三皇庙,至明清有存者,主要为民间祭祀。
对炎帝的尊崇、祭祀,在历史上虽没有对黄帝的尊崇、祭祀那么重视,但是也有一些记载。对炎帝的祭祀,主要表现在“藉田”上。正如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所说,神农最先懂得使用地力,种植五谷蔬菜,因而成为农业始祖,被尊奉为“地皇”。夏商以来,就开始有了祭奠农神、祈求五谷丰登的典礼。如《令鼎铭》曰:“王大藉农于(淇)田。”周人将后稷(弃)、烈山氏之子“柱”,与炎帝一样祀为“农神”(神农)加以祭祀。战国时,秦灵公有“祭炎帝”之举,首开官方祭炎活动。至汉,仍时有祭祀。汉高祖刘邦开祭“五帝”之先,汉武帝多次“行幸雍,祠五峙”。汉文帝首开“藉田”礼仪,以祭“先农”,即“炎帝神农”。以后汉帝大都效仿之。三国时的魏国帝王,为显示其正统地位,均有藉田之举。晋武帝泰始四年诏曰:“夫国之大事,在祀与农”,并“以太牢祀先农”。晋孝明帝以“神农配火”。
隋唐以后由于对农业的重视,而更重视藉田礼仪。隋设藉田在京城长安南郊,以中侍奉耒耜,“载于象辂”。唐代皇帝亲自参加藉田。唐太宗贞观三年在长安城通化门外东郊十里设先农坛祭祀炎帝神农氏,于坛南十步躬耕藉田;唐高宗和武则天常驻跸东都洛阳,便于祭祀和举行藉田大礼,又在洛阳上东门外七里道北设置先农坛和藉田;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敕建三皇五帝庙祀神农。
北宋刚一建立,宋太祖便让其官员寻访“炎帝陵”,在酃县(现炎陵县)御祭,“三岁一举,率以为常”。不仅如此,北宋王朝还于都城汴京朝阳门外七里筑造先农坛,藉田祭神农。宋仁宗明道二年亲自藉田,公侯效仿,规模之大,而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南宋虽偏安江东,但仍继承了北宋传统,于临安嘉会门外以南四里的玉津园附近祀先农藉田。
元明清祭祀、藉田礼仪更为完善。元代虽皇帝未亲藉田,但此事照常进行。“先农之祀……如祭祀之仪”。明太祖定都南京,于洪武二年建先农坛于南郊,亲祭先农;迁都北京,在宫城之南建起了先农坛,每年仲春二月,由北京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顺天府尹致祭。以后每代皇帝登基初年,都要亲祭先农,行耕藉礼。崇祯十五年还对祭祀乐作了修订。清朝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礼制。三十五年正月,康熙还派大臣到酃县的炎帝陵去祭祀,雍正二年赏赐藉田农夫布,颁赐各省嘉禾图;乾隆还亲自到中南海丰泽园指导农耕演习。清朝的祭祀先农一直延续至光绪年间,并规定各省、府、州、县,都要设立先农坛藉田。
在历史上对炎黄二帝的“认祖”,不仅表现在华夏汉民族中,而一些非华夏汉民族亦予以认同。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地处长江上、中、下游的蜀、巴、楚和吴、越被中原称为蛮越,而此时纷纷认同华夏,甚至自称黄帝、炎帝苗裔之正宗。魏晋南北朝,夏国赫连勃勃自称“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鲜卑慕容氏“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日东胡”。氐秦苻氏,称“其先盖有扈之苗裔”。鲜卑拓跋氏认为是“轩辕之苗裔”。鲜卑宇文氏又称“其先出自炎帝,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刘渊是匈奴贵族,石勒是羯人,都认为他们是匈奴别部。而据《史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日淳维。”契丹族先自认是炎帝之后,继而又认为是出于黄帝苗裔。又如前面提到的元、清两代对炎、黄二帝的祭祀,仅清朝于炎帝陵御祭就达38次之多。这些族源认同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认同反映了非华夏汉民族与华夏汉民族的一种强烈的认同心理,即情感。据有关专家考证,时至今日中华民族中,除汉族之外,有苗、羌、藏等33个少数民族与炎黄二帝有“共祖”关系。
总之,从春秋战国的“炎黄唐虞苗裔”、司马迁的华夷诸族共祖,至今日的“炎黄子孙”;从秦汉的“四畴”、“五畴”及“藉田”到今日全国多处修陵建祠的寻根祭祖热,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炎黄二帝在中华民族中的“共祖”地位不但未曾动摇过,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愈加巩固,越来越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其原因之一亦是最根本的,就是由于炎黄二帝“共祖”象征作用的结果。
二、炎黄二帝具有文化纽带的象征作用,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