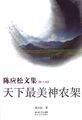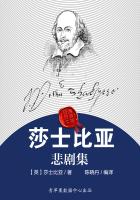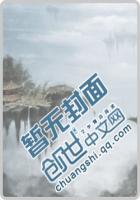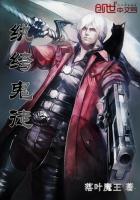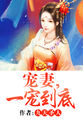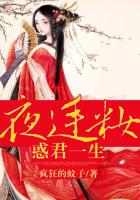炎帝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意见分歧亦大。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未将“历史的炎帝”与“文化的炎帝”加以区别,从而造成对炎帝与神农氏、炎帝的时代、炎帝的始祖地位、炎帝的生葬地诸问题见仁见智,各有说法。本人依据古文献记载,并结合今日有关学人的研究成果,谈点个人不成熟的想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从“历史的炎帝”到“文化的炎帝”
所谓“历史的炎帝”是指从历史的视角来认识炎帝,认为炎帝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即真有其人;所谓“文化的炎帝”是从文化的视角来认识炎帝,认为炎帝既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又是一个文化的符号、时代的象征、始祖的象征。由于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考察炎帝,所以,也就产生了炎帝是人还是神,炎帝与神农氏是一人还是两人,炎帝与烈山氏是否一人,炎帝生葬地以及炎帝时代的界定诸分歧。我认为,此类问题的产生,关键是将“历史的炎帝”与“文化的炎帝”混合一起而造成的。而这二者的混合,其核心是炎帝与神农氏的合户。
从“历史的炎帝”到“文化的炎帝”大致经过了三个演变时期:
(一)“历史的炎帝”——春秋及其以前。记载炎帝的历史文献,我们现在能看到且比较早的是春秋时期的,有三种四条:
1.《逸周书·尝麦》:
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案:“赤帝”即“炎帝”。
2.《左传·昭公十七年》:
郯子曰:“……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炎师而火名。”
3.《左传·哀公九年》:
史墨曰:“……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
4.《国语·晋语四》:
司空季子曰:“……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为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若将上面的几段文字连缀起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炎帝大略的生平事迹:其父族少典氏,母族有氏,诞生、成长于姜水,与黄帝为“兄弟”。因其与黄帝的居住地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习俗,故而姓姜。他在部落中的职务为“卿”,工作为“火师”,并因“火纪”而得名“火(炎)”。将炎帝的事迹加以归纳,可以看出,炎帝的功绩主要有三项:一是“火师”,即保管火种者。由此知道,炎帝可能将火应用于农业,发明了“刀耕火种”;二是从后世人们添加的“帝(禘)”号来看,是祭祀活动的主持者。因古代祭祀要用到火,“燔柴以祭天”,故而称“炎帝”;三是辅佐黄帝“执蚩尤杀于中冀”,炎、黄、蚩三部落联盟,建立了华夏集团。炎帝为华夏族始祖之一。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均未提到神农氏、烈山氏等。可见炎帝与神农氏、烈山氏并非一回事。依此还可以看出,春秋及其以前人们传说的炎帝完全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无有一点儿神性的味道。
(二)“历史的炎帝”向“文化的炎帝”的过渡——战国、秦汉时期。使“历史的炎帝”而转入“文化的炎帝”,始于战国,完成于西晋。战国时期魏国史官编录的《竹书纪年·前编》,首次将炎帝与神农氏相连,称为“炎帝神农氏”。随后由战国时人撰,成于战国末年的《世本·氏姓》再一次写道:“姜姓,炎帝神农氏后。”到了西汉末年,由于王莽篡权的需要,刘歆便在《世经》里说:“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种,故天下日神农氏。”将炎帝与神农氏放在一起连说。之后的班固《汉书》、王符的《潜夫论》亦出现了将炎帝与神农氏相连的文字。《潜夫论》载:“有神龙首出常[羊],感妊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王符很清楚地将二者视为一人,并将炎帝视为神农时代的一个古帝的名号。炎帝与神农氏的合户,标志着炎帝的事迹放大了,将“战国、秦汉间陆续出现的神农事迹全给炎帝收受了”。炎帝的时代就不是与黄帝“同时”了,而是先于黄帝。且加长了。这样一来,炎帝“再不是《国语》中的炎帝”,即前边所说的“历史的炎帝”,而具有了文化的意义,进入了“文化的炎帝”的范畴。
其实,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的古籍中,未将炎帝与神农氏合户的还占绝大多数。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如《山海经》、《礼记》、《商君书》、《尸子》、《孟子》、《管子》、《庄子》、《文子》、《列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尚书大传》、《新书》、《淮南子》、《尚书序》、《史记》、《春秋繁露》、《新序》、《说苑》、《列仙传》、《纬书集成》、《新论》、《白虎通义》、《论衡》、《吴越春秋》、《越绝书》、《说文解字》、《风俗通义》、《独断》、《古史考》等古籍中,均未将二者连在一起,即使在同一部书里,炎帝、神农氏亦是分开的。在写到二者的事迹时,亦是分开的,说到发明农耕、医药、交换、音乐等均为神农氏,说到火、战争则是炎帝。这里我们仅举司马迁《史记》为例。
司马迁虽未在《史记》中对炎帝和神农氏作以专门论述,这可能与他看到有人将炎帝与神农氏相连不无关系,但在《五帝本纪》、《秦本纪》、《封禅书》、《历书》等卷中都提到了炎帝和神农氏,但均是分开来说:“神农氏世衰。而神农氏弗能征。炎帝欲侵陵诸侯。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尊黄帝为天子,代神农氏”,“神农之前,吾不知矣”,“神农以前,尚矣”,“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等。可见,在司马迁的心目中,炎帝与神农氏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此期间尽管已有人将炎帝、神农氏合户,“但是这种偷天换日的手段固然可以欺骗一般庸众,终于骗不了一二思考精密的学者。三国时,谯周作《古史考》,就以为炎帝与神农氏各是一人”。虽有人反对这种合户,但在西晋以后,炎帝与神农氏则完全成为一人了。
在此还要提到的,在东汉初,郑玄在注《礼记·祭法》“厉山氏有天下也,其子日农,能殖百谷”时说:“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日烈山氏。”开始将烈山氏与炎帝挂钩。另外,汉代高诱在注《吕氏春秋·古乐》“昔古代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一语时说:“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别号。”将炎帝与朱襄氏相连。《左传·昭公十八年》注:“先儒旧说,皆云炎帝号神农氏,一日大庭氏。”又将炎帝与大庭氏相连。另外,还有将炎帝与连山氏、魁隗氏视为一个氏族部落或一人的。炎帝成了多个古帝的化身。
(三)“文化的炎帝”——西晋及其至今。西晋学者皇甫谧,在其所撰的《帝王世纪》里,他对上起远古帝王,下至汉、魏的历史进行了一次大整合。在说到炎帝时,他将神农氏的事迹置于炎帝的身上,将二者完全视为一个人,为炎帝编写了一份较为详细的“履历”。将其降生、生地、妻子、儿女、世系、事迹、葬地、迁徙等都涉及到了,并赋予了炎帝较为浓厚的神话色彩,如“游华山之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等。至此,可以说完成了战国、西汉以来从“炎帝一炎帝·神农氏一炎帝神农氏”的过程,即从“历史的炎帝一历史的、文化的炎帝一文化的炎帝”的过程。
不仅如此,皇甫谧在其笔下,在继承郑玄“烈山氏炎帝说”的基础上,更为明确地说:“炎帝神农氏……继无怀氏之后,本起烈山,或称烈山氏”,“神农氏起列山,谓列山氏,今随厉乡,是也”。此外,晋的另一位学者杜预,在其《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注中亦说:“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厉山在湖北随州北四十里。”除了引郑注外,还确指了厉山的位置。这样一来,使炎帝的事迹变得更为复杂起来,炎帝的生地由“姜水”一地而变为两地,随州厉山亦成了炎帝的出生地。同时皇甫谧又说炎帝“葬茶陵”,今日之炎陵县,亦出现了较为密集的炎帝传说。
在《帝王世纪》的影响下,以后出现的古籍中,则基本上是将炎帝与神农氏视为一人,凡提到炎帝或神农氏都属于“文化的炎帝”的范畴,而“历史的炎帝”则完全隐藏于“文化的炎帝”的背后。其中唐司马贞的《三皇本纪》、南宋罗泌的《路史》在引述皇作的基础上,对炎帝的事迹作了更为系统的记载,其影响也较大。尤其是《路史》,对前人来了个集大成,以七八千字的篇幅对炎帝事迹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描述,并赋予了炎帝更多的“神性”。不仅如此,《路史》等有些古籍中,还把炎帝与祝融、蚩尤(阪泉氏)等相连,使炎帝的生平中又有了祝融和蚩尤的事迹。
当然,也有认为炎帝与神农氏不是一人的,如清代中叶的崔述。他在《补上古考信录》里,则明确地说:“神农氏之非炎帝也。”其理由:
《史记·五帝本纪》曰:“轩辕氏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又曰:“炎帝欲侵陵诸侯;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夫神农氏既不能征诸侯矣,又安能侵陵诸侯?既云世衰矣,又何待三战然后得志乎?且前文言衰弱,凡两称神农氏,皆不言炎帝。后文言征战,凡两称炎帝,皆不言神农氏。然则与黄帝战者自炎帝,与神农氏无涉也。其后又云:“诸侯成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又不言炎帝。然则帝于黄帝之前者自神农氏,与炎帝无涉也。
《封禅书》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夫十有二家之中既有神农,复有炎帝,其为二人明甚,乌得以炎帝为神农民也哉!
要之,自司马迁以前未有言炎帝之为神农者,而自刘歆以后始有之。
崔述说“自刘歆以后始有之”不确,实际上从战国起就有人开始将炎帝与神农氏合户了。
在此期间,除了古籍中的记载之外,民间关于炎帝大量的传说故事(其中许多可以说是神话故事)都讲的是“合户”了的炎帝,即“文化的炎帝”。如在宝鸡地区民间流传的“炎帝降世”。说炎帝降生后,头上长角,身上生疮,炎帝母安登便抱上他到九龙泉“洗三”(洗澡)。刚把炎帝放进泉水,便从泉底游出九条龙,向他身上喷水,顿时,炎帝头上的角没有了,身上的疥疮没有了,变成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炎帝见风而长,三天能说话,五天能走路,七天能下田干活。在这则民间传说里,却更多地赋予了他神话色彩。在湖南炎陵、山西高平、长治等地区也有类似的炎帝降世的民间传说。有关炎帝发明创造方面的民间传说就更多了,如“炎帝抱太阳”、“神农寻谷”、“神农种五谷”、“炎帝祈雨”、“神农鞭药”、“炎帝择婿”、“降牛耕田”、“炎黄联姻”等等;而且,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版本。这些民间传说,虽则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有些甚至荒诞不经,但是,它作为一种文化,却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炎帝”的形象,使炎帝更具有了文化的意蕴。
随着二千多年来文人、民间的相互传说、演绎,即顾颉刚先生说的“层累地造”,使“历史的炎帝”完全走向“文化的炎帝”。“炎帝”之名已不在是《左传》中以“火师而火名”的那个具体人物的名字了,而成了内含“人物”、“氏族(或部落)”、“时代”等的多种文化的集合称谓,正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所说:“在氏族史上着名的某人即成为该氏族以之命名的祖先。”其身上负载着神农氏等多个古帝的事迹,甚至其身上的“神性”,要多于“人性”,即演变为纯粹的“文化的炎帝”了。我们今天所认识,所研究的,就是“文化的炎帝”。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为什么有人说炎帝是人,有人说是神,产生炎帝生葬地异说的根本原因,即有人从历史的视角研究炎帝,有人从文化的视角研究炎帝所造成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能使“历史的炎帝”走向“文化的炎帝”。且被历史所认可,一直延续于今天,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阴阳五行学说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炎帝与神农氏的合户虽说在战国时的《竹书纪年》、《世本》中已经出现,但二者真正的实现,且被人们接受是在西汉末年以后,即受此时流行的五德终始说的影响。西汉末年,刘歆作的《世经》,根据邹衍原始的五德终始说又创造了一种新的五德终始说,从伏羲的木德为始,以五德相生说为次,木生火,故炎帝以火德继;火生土,故黄帝以土德继……木又生火,故帝尧以火德继;火又生土,故帝舜以土德继,这样一直编排到汉。王莽为了给自己篡权寻找理论根据,便依据刘歆的五德终始说又编排了一个系统,自认为自己为黄帝的后裔为土德,而土生于火,火是炎帝,但炎帝与黄帝为同父昆弟,同时代人,不能由炎帝(火)禅让(生)于黄帝(土),于是便又依据《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等记载:黄帝之前尚有神农氏。但神农氏不是火德,怎么办?于是便想到炎帝,便将表示前一代的神农氏与表示火德的炎帝“生生地合起来了,‘炎帝神农氏’一名就出现了,战国、秦、汉间陆续出现的神农事迹全给炎帝收了!”如此,将刘、王两家的世系变为:炎帝神农氏禅让(生)黄帝轩辕氏,帝尧陶唐氏禅让(生)帝舜有虞氏,汉禅让(生)新,即“(火)炎帝神农氏一帝尧陶唐氏一汉”相对应于“(土)黄帝轩辕氏一帝舜有虞氏一新”。王莽编排的世系及其五德之运,似乎顺理成章,没有什么理由可反对的。到了东汉时王符,他在《潜夫论》里,依据五德终始说,将同德的帝王一起说为祖孙,即从华胥生太吴伏羲氏到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青阳氏、颛项高阳氏,组成了一个后者代替前者、更加紧密的关系网,使“炎帝神农氏”的称谓完全固定下来。
二是适应了秦汉以来“大一统”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需要。在战国以前则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诗经·商颂》:“天欲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大雅》:“厥初生民,时维姜螈。”其他如任、宿、须句出于太昊,郑出于少吴,陈出于颛顼,楚、夔出于祝融、鬻熊等等,他们是各有各的始祖。但春秋以来,由于“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本来为横的,现在变为纵的,有了君臣、祖孙的关系。到了秦汉统一国家的出现,这种“大一统”的观念更为加强。在《尧典》、《五帝德》、《世本》等书所编排的古帝系统的基础上,经《史记》、《汉书》、《潜夫论》推演,一个完整的华夏族的世袭系统即“三皇五帝”图便基本上固定下来,“炎黄”成了华夏族之始祖,即国家、民族“大一统”的象征。炎帝与神农氏的合户也就很自然地被人们接受了。
三是反映了真实历史的缩影。罗琨先生曾谈到炎帝与神农氏的合户时说,人类的童年时代以采集兼捕捉小动物为生,后来发明了火猎,狩猎便成了独立的经济部门。这就是“取牺牲以供庖厨”的伏羲氏时代。距今一万年左右,中华大地出现了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这是始教天下耕种的神农氏时代的开端。以后,制陶、琢玉、制骨、牙雕、纺织、铸铜等各种手工业部门先后出现,逐步推向史前发展的高峰。与此同时亦产生了分工、交换、私有制和阶级分化,进入了文明的初曙的英雄时代,即以战争取胜而王天下的黄帝为代表的时代。“所以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实是夏朝以前历史进步的长河中的三大重要里程碑。”经考古印证,文献记载的种种发明,确在历史上出现和存在过,并凝结在很多民俗中,“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形成有赖于那个时代奠定的基础,所以,‘炎帝神农氏’一语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一代代地流传下去”。
“历史的炎帝”到“文化的炎帝”,其意义,今天看来,简言之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为炎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依据,使“历史的炎帝”的形象更为高大、内涵更为丰富,使炎帝更为平民化、宗神化,易于为老百姓接受,有利于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文化认同,有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以及有利于炎帝寻根祭祖旅游文化的开展。
二、炎帝与黄帝为同一时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