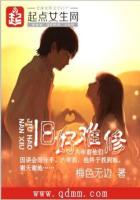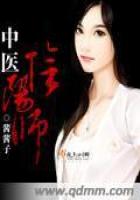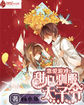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王震中博士在其《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中,通过对“世界各地最早的文明社会皆立足于农耕系统而形成的事实”的研究,认为农耕的起源,“改变了人类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是“文明的起点和基础”。并指出:“只有进入定居的农业,人口才会逐渐获得较为明显的增长,较大的地域集团才开始形成,社会生产的分工、财富的积蓄、所有意识的萌发才得以实现,战争和贸易才能发展起来;也只有进入定居农业,社会性、政治性组织才变得愈来愈复杂,社会的不平等、阶层和阶级才得以产生,强制性的权力机构才会产生,农耕礼仪、宗教祭祀等观念形态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如果我们以此为参照对北首岭遗址的内涵加以考察,就会不难发现:宝鸡北首岭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
北首岭遗址是1958-1960年及1977-1978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它是一处保存比较完整的仰韶文化村落遗址,有着丰富的居住遗迹、遗物以及年代比半坡类型更早的北首岭类型堆积。根据碳14年代测定,北首领早期距今6970±145-7100±140年;中期距今6120±140-6790±145年;晚期距今5745±110年-6035±140年。
从遗址发掘的情况来看,北首岭仰韶先民已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北首岭遗址的仰韶文化堆积厚处达四米以上,有些地方数层居住遗址叠压在一起,村落形制具有相当规模,而上、中、下三层文化遗存又具有明显的连续性。说明仰韶先民在此定居周期性比较稳定。居址中出土的生产工具共951件,其中石斧、石铲、石刀、骨铲、角铲、角锄、陶刀等农业生产工具共248件,占26%;骨镞、角矛等狩猎工具共81件,占8.6%;石网坠等渔猎工具仅6件,占0.6%;敲砸器、石凿、研磨盘、研磨棒、研磨器、磨石、角凿、陶锉、陶内模等日常生产用具和制陶工具共617件,占64.9%。说明在所有的生产经济中,农业居于主要地位。此外,居址中还发现较多的加工谷物的石碾盘、石棒及家猪骨骼,77T1-4所出动物骨胳均以家猪为主,在早期灰坑里还发现了一叠四件的石铲。这些情况进一步证明,即便在早期,农业也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历史传说和古今专家、学者研究表明:宝鸡是炎帝故里。炎帝的生活年代在仰韶文化晚期之前,与北首岭考古文化年代基本相当。所以有学者推断北首岭遗存便是炎帝及其族人的遗迹。
古籍记载,炎帝号神农氏,是农耕工具“耒耜”和粟谷的发明者,“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教民农作”,“乃始知谷食”。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亦为北首岭先民较为发达的农业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明。
定居的农业,使北首岭先民的村落具有相当的规模,且布局又有一定的规律。村落的中心有一块南北长100米、东西宽60米的场地,经过钻探和发掘都没有发现房址和墓葬,只发现有两层路土,“当是公共活动场所”。场地的周围有许多房址。场地之北,有22座,其中有16座门道朝南;场地之西,有10座,其中有8座门道朝东;场地之东南,有17座,其中有10座门道朝北和西北。“很显然,房屋是有意围绕着广场建造的”,从而“形成场地以北和以西的房屋与场地以南和以东的房屋遥相对望的情况”。以此说明两点:一是北首岭先民已完全过上了定居的生活,二是北首岭当时是一个有众多人群居住的村落。若以每户5口人计,其村落人口有250之多(这仅以发掘遗址计算)。从宝鸡渭河流域的考古发现来看,以北首岭下层、高家村等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居住遗址有近20处(属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遗存的居住遗址500余处,龙山文化遗址200余处。所以,有学者指出:“从遗址分布图上看,几乎与现代的村庄分布重合。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凡是现在的村庄,基本上都有新石器时代古遗址存在;凡是现在人类生活的地方,几乎都有新石器时代先民活动的遗物遗迹”。可见,宝鸡地区已形成了较大的地域集团。从“炎帝以姜水成”,“黄帝以姬水成”的文献记载来看,这个“地域集团”可能就是姬、姜二族的联盟集团。
有学者认为:“北首岭遗址不是一般的原始部落,而是一个前国家的权力中心。”北首岭虽无类似国家宫殿式基址,但发现了“大房子”。77F3房屋基址面积为88.36㎡,是其中发现房屋基址最大的一座。它朝东面对一个南北长100米、东西宽60米的广场。从发掘看,这座“大房子”只有灶坑,没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不像是居室,当是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而在其活动中必有某个权力人物的存在”。从77M11墓葬中发现的用花斑石磨制得很精致的石钺看,它与石斧不同,“已丧失了武器和工具的功能,成了一种象征,即权力的象征”。再联系炎帝“初都陈”和黄帝“都陈”(陈为“陈仓”,陈在北首岭东面约3公里处),亦从一个侧面说明,仰韶文化中期的北首岭已具有了“前国家”的性质也是有可能的。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的概括。”北首岭“前国家”的出现,标志着北首岭社会已开始进入原始文明社会。
北首岭遗址墓葬出土的许多材料表明,当时社会已有了一定的分工。在第Ⅳ区的墓葬里,有的墓随葬有很精美的石斧,但它们并未有使用过的痕迹,可能标志着墓主人生前是农业生产活动的领导者;有的墓葬有较多的骨铲原料,并有意识地放在一块大砺石上面,可能反映了墓主人生前是专司骨器制造的;有的墓随葬有成盂颜料或大块红色彩绽;有的墓随葬的陶器特别精美,可能标志着墓主人生前是专职造陶器的;有的墓随葬有整柬骨镞,有的墓随葬有数十枚獐牙,可能标志着墓主人生前是狩猎能手。
随着分工的出现已有了贫富差别,这在北首岭遗址中期以后有所反映。在一些能够反映墓主人生前有若干专长的墓葬里,往往随葬品比较多。而在第Ⅵ的墓地里,无论中期或晚期的墓葬里,有相当部分无随葬品,即使有也只有一二件陶器,与出土十余件或七八件陶器的墓相比,显然存在一定的差别。“在原始社会,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具有专门生产技能的人不但受到社会的尊敬,而且在物质生活方面也将分享到较多较好的一份”。从墓葬出土随葬品的多少就反映了当时这一社会现实。
社会分工的出现,贫富差别的产生,社会有了剩余产品,随之也有了交换。文献记载:炎帝神农氏发明了“日中为市”,开始了物物交换。而这种传说,从北首岭遗址墓葬中发现的数十枚榧螺,得到了印证。此种软体动物只产于南海或东海,而在相距数千里外的北方或西方发现,“很可能是经过辗转交换得来的”。
北首岭仰韶文化中期以后,原始的文化艺术也有了较快发展。首先,反映在绘画方面,当时的彩陶除了常见的“人面鱼纹”以及图案化的几何形纹外,还出现了一些精彩的写真画面。M52的一件陶壶肩上,绘画了一幅水鸟衔鱼的图画。画的是一只形体不大的水鸟,叼住一条大鱼尾巴,鱼负痛回首挣扎,水鸟紧衔不放。笔法简洁而粗放,画面紧张而生动,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这幅“水鸟衔鱼图”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此外,还发现了几种颜色的颜料,而且数鼍颇多。这反映了当时绘画不仅有较高的艺术水平,而且已相当普遍。颜料的发现,为研究原始绘画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其次,在雕塑方面,中期的一件半身人象雕塑,头部已经残缺,但人像的双手手指仍用刻痕加以表示,手法极为原始。可以说它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时代最早的人像雕塑作品”。另一件是半浮雕式的男性人面陶塑,眉目须发十分逼真,为复原当时先民面型,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再次,开始出现了原始文字。在77M17发现的一件尖底陶器上,有黑彩写画的“、W、、山”等多种符号组合一起。此外,77M:15(7)的1式壶上,黑色彩绘写的两个符号,已明显地表示出数量和对称的概念,也反映出北首岭先民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审美意识;77T3:2彩陶片上绘写的,与姜寨遗址中出土的刻画符号相同。对这类刻画符号,研究者大都认为是汉字的起源。郭沫若说:“刻画符号的意义至今尚未明确,但无疑是文字的起源,或者是中国原始文字孑遗。”于省吾、李孝定、徐锡台等先生也都持相同意见。彭曦先生说,北首岭尖底器上四个黑彩绘写符号,“应当是文字史上的一种质的变化,即文字开始有了记载复杂事物的功能”。并认为,这种陶器刻划、绘写符号即最早文字的发明者,是居于仰韶文化区系中心地区的少典氏族。及其后裔炎帝、黄帝族,因为当“文字具备记载复杂事物功能时,才可能称得上有册有典的起源”。何光岳先生亦认为:少典氏之“典”与“典册”有关,“可能是最早发明文字的人”。
北首岭仰韶文化延续了近1500年,经历了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亦是新石器时代的繁荣期。在这长达千余年的历史中,北首岭先民创造出了先进的原始文化,尤其是先进的原始农耕文化,为中国原始文明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北首岭遗址发掘者研究认为:“北首岭下层类型是半坡类型的前身”,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文怀沙先生认为,北首岭先民为“炎帝的祖先”,中华民族的根与本亦在此。如果此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认为: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族继承和发扬了其“祖先”创造的先进的农耕文化,而又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本氏族部落的文化,即以农耕为主要内涵的姜炎文化。后来的周人在宝鸡周原发迹,创造了先周文化,而先周文化又是“姜炎文化与姬周文化的融合形成”的。那么,换句话说北首岭仰韶文化的遗传因子又为先周、西周文化所吸取,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由此可见,把北首岭仰韶文化看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原功于《宝鸡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后收入《姜炎文化论》,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题目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