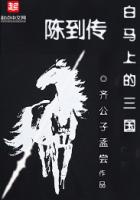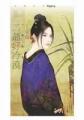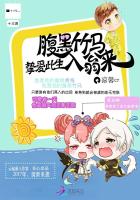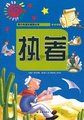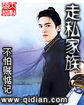一、究天人之际——对天命的怀疑
先秦时,众多思想家、哲学家对于人生及其命运都做出深刻的思考,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孔子一派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孔子认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进一步强调富贵无法用人力去追求。就连“道”,在孔子的心目中也是“道之将行也,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可见孔门是完全信奉天命的,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富贵贫贱,完全与高悬于天的命运有关,绝非尘世芸芸众生的力量所能改变,故孔子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孟子承袭了孔子的天命观,对于“天命”也是唯命是从。他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意即没有人叫他这样做,而做了,这就是天意;教条令司马迁产生莫大的怀疑,逐渐认识到“天”无法把握“人”的命脉,真正主宰人类命运的,无论是灭亡抑或贵达,都是人为所致。因而历史是人类自身的活动过程,人才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司马迁针对当时的谶纬神学给予针锋相对的批驳,表现出清醒、冷静、理智的历史哲学精神,在实践中他着力向人们展示了人的内在价值的实现过程,强调人事的决定作用以及各种人才对历史发展的作用。
二、“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
——对人才的重视
纵观《史记》,司马迁对于“天命”的认识似乎常常模棱两可,比如在《天官书》里记载说:
“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
在《夏本纪》中记载: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
这两则材料,前者是说星象能预示人事的吉凶,后者则表明了人君失德,天降灾异以示警告,表面上看似乎承袭的是“天命”论的思想,但与此相矛盾的是,司马迁在记述这些历史现象的同时,又讥讽这类星气占验为“凌杂米盐”(《天官书》),根本不可信。在《太史公自序》里,他又说:“星气之书,多杂祯祥,不经”,即讲述星象气数的书,掺杂着许多有关祈福、预测吉凶的内容,荒诞不经,否定了星气之书的可信性。实际上司马迁涉猎天文学知识,是认为自然界有其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诸如天体运行是有规律可循的,但它的规律是由人类推算出来的,因而天象运行并不是神秘莫测的。而人事的变化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一旦掌握此规律,即可避凶趋吉,国家祯祥。
在历史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司马迁将其睿智的目光聚焦于人事,努力探寻其发展的规律,在他笔下,历史成了一幅由一个个有血有肉、多姿多彩的人物构成的画卷。司马迁曾说:“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刘敬叔孙通列传》),司马迁没有将人事的作用局限于君主,更没有推诿于神。传统思想中的“神授君权”在此变得苍白无力。司马迁实事求是地通过对人力因素的揭示,拨开“君权神授”的迷雾,用事实阐明了历史不是一个人或某个神创造出来的,它需要许多人的才智参与创造。通观《史记》,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平民、商人、妇人、游侠、医生、卜者、方士、倡优,旁及少数民族首领、农民起义领袖等,凡是活动在从黄帝到汉武帝这三千年的历史大舞台上的各种各类、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都在司马迁的视野之内和评价之列。这显然已不同于对君主作用过分夸大的那种历史观念,它强调了众人的作用。
《魏公子列传》记载魏公子名冠诸侯,声震天下,其才德远远超过齐之孟尝、赵之平原、楚之春申。原因在于魏公子“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太史公自序》)。他屈尊求贤,不耻下交,驾车虚左亲迎门役侯嬴于大庭广众之中,多次卑身拜访屠夫朱亥以及秘密结交赌徒毛公、卖浆者薛公等。而他正是在这些“岩穴隐者”的鼎力相助下,完成“窃符救赵”和“却秦存魏”的历史大业。这也反映了司马迁重视人民群众力量的进步的历史观。《高祖本纪》刘邦在称帝后曾总结他成功的经验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也,此吾之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所擒也。”由此看来,项羽最终的失败并非“此天亡我”,而刘邦最终的胜利也并非“听天由命”,而在于是否善用人,能驾驭人。
与“究天人之际”的思想相联系,司马迁已经不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肯定人事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是以具体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去丰富和证实他的这一认识。更为可贵的是,司马迁在肯定人在历史进程中所起作用的同时,强调了各种人才在历史上的作用。
也没有人去招致,而来了,这就是命运。弦外之音即天下万事万物的发生,实际上都是由天命主宰的,所以“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孟子·尽心下》)。即君子依法行事,静静地等待命运的安排罢了。
庄子才华恣肆,目空一切,但即使这样一个孤傲狂放的天才,竟然也不能冲破“天命”的樊篱,而是无可奈何地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到也。”(《庄子·人间世》)“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庄子·德充符》)“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庄子·德充符》)显然庄子认为,对于命运的降临及其安排,人力是无法抗拒、无力招架的,只能安然地承受;或者是逆来顺受,这就是“有德者”采取的一种态度。
以上由儒道两家信奉天命派的思想,足见“天命”论的巨大影响。司马迁距离先秦300多年,而且先秦孔孟以下,汉代的一批学者如董仲舒、扬雄、王充、王符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天命”论的信奉者及宣扬者。可见至司马迁时“天命”论仍经久不衰。但司马迁并未拜倒在“天命”之下,他对于自古流传的“天命”说表现出极大的疑惑和不解。司马迁的疑问在于:既然天命存在,那么古往今来的“善人”和“操行不轨”的人最终遭遇却为何总是差强人意?善人屡屡遭殃,恶人为所欲为,这样看来,“天命”岂有什么公正性及正义性,既然如此,由上天所赋予的命运又何尝不令人怀疑呢?
司马迁对于天命的怀疑是在解释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和自身遭遇中产生的。他在《史记·伯夷列传》中论及伯夷的遭遇时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肚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
这段话司马迁有意识地动摇并否定了“天”对个人命运乃至国家兴亡等人事的决定作用,表现出清醒的历史理性,这种怀疑精神在其许多篇章中都有所反映,如《蒙恬列传》中蒙恬被赵高所害,临死时说:“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恬之罪也。”乃吞药而死。蒙恬是秦国的功臣,对秦国没有任何过错,他纯粹是死于国君的昏庸,而非绝地脉之罪。司马迁在论赞中写得很清楚,“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廖,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与此相似的还有《李将军列传》,李广自结发与匈奴数十战,部下偏裨得侯者多人,而李广不得侯,他问望气者王朔:“岂吾相不得侯耶?且固命耶?”王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王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之所以不得侯者也。”而《李将军列传》的本旨是谴责汉代的几朝皇帝及其宠幸们迫害李广,最后造成李广悲惨结局的罪行。李广何以不得封侯,这在列传中写得很清楚。文帝空口赞赏而不用;景帝因嫉恨其胞弟梁孝王而迁怒李广,李广在破吴楚时有大功,由于接受了梁孝王的将军印,还朝后而赏不行;至于汉武帝更是与卫青合起来故意地作弄他,以致闹得道远失期,最后自杀身死。所以王朔之所谓:“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之所以不得为侯也”,与《白起王翦列传》中,白起临死时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坑之,是足以死”一样,都是历史人物对造成自己悲惨遭遇的罪魁祸首不好直说,而故意做出的像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解释。
司马迁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根据大量历史事实的分析和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洞察,似乎意识到历史人们的人生轨迹中所上演的生死祸福、起伏跌宕的历程,推诿于所谓的“天命”不过是一个自我解嘲、自我解脱的托辞而已。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善恶祸福、因果报应的道德就是说,司马迁已经注意到,历史不是一个人可以创造出来的,它需要许多人的才智参与创造。“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的认识,使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历史哲学思想更为丰富、更为具体,是人在历史进程中作用的一种更为深刻的认识。
三、“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探寻治乱兴衰之故
司马迁“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太史公自序》),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寻求着历史发展的规律,试图揭示出历史发展的真理。通过对具体历史事实的考察,对人事活动的探索,司马迁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诸多方面总结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成败兴坏之理”。
司马迁的民本思想是很明确的,他在《史记》中指出,三代之王都是因祖上积德累善而赢得了百姓的拥戴。“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秦楚之际月表》);武王伐纣,“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周本纪》);秦之亡,是因为“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张耳陈余列传》。楚汉相争,民心向背的作用更为显明。刘邦多次战败,以至父母、妻子都成了项羽的俘虏,为什么最后终于走向了成功?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说,“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项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淮阴侯列传》)。而刘邦则是“承敝易变”,即对过去的弊病加以革除,顺民之俗,将政治得失与人心向背紧密联系在一起。楚亡汉兴,民心向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顺应民心,以民为本这一治理天下的国策的提倡,势必要求统治者采取“德治”的方针。司马迁以具体的历史事实说明修德与行德对于一个朝代兴亡成败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他在《五帝本纪》中说:“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王气,艺王种,抚万民,度四方……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在《夏本纪》中,他记载了“桀不务德”而亡,“汤修德”乃“践天子位”的事;在《殷本纪》中,记载了太戊“修德”、武丁“行德”而去灾异,“殷道复兴”的事。司马迁认识到一个最高统治者实行“德治”,不但可以保当世的统治无患,而且还能远荫子孙,使他们的统治地位长久不衰,昌盛繁荣。
司马迁除了对统治者的基本国策提出“德治”的评论外,还对贤相良将治平天下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
“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乱臣贵……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
三代的兴亡如此,春秋列国的争战如此,楚亡汉兴尤其如此。他十分感慨地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用贤相良将以治平天下的思想贯穿《史记》全书。司马迁指出,春秋时,齐桓公因得管仲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晏列传》)。战国时,因乐毅、田单施奇计,“遂存齐社稷”(《太史公自序》)。秦能卒并天下,是因为秦孝公用商鞅,民富国强;秦惠王用张仪,连横告成;秦昭王用白起,破赵长平;范睢建远交近攻之策,击破东方六国;秦始皇则在李斯、王翦、蒙恬等人的辅佐下,终于一统天下。楚亡汉兴的历史,更可以说是一部贤相良将辅佐刘邦打天下、治天下的历史。然而齐桓公因为晚年不听管仲的劝告,而信用奸佞小人,结果病中发生了诸子争夺继承权的内乱,以致死后无人理丧,“尸虫出于户外。”一度称雄于东南的吴王夫差,骄傲自大,不听子胥的忠言,一意信用小人,最后战败而被迫自杀。而昏庸的楚怀王,听信挑唆,疏远流放忠心耿耿、才干卓荦的屈原,而亲近奸佞小人,最终落个客死他乡、国破家亡的境地。司马迁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深刻地揭示出用人得失直接关系到国家之兴亡。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讲到了撰述《本纪》的原则是,对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司马迁通过对政治形势、经济变化、世风趋势等历史现象的概括,提炼出“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平准书》)这一带有理性辩证色彩的历史认识。
司马迁在《平准书》中以秦喻汉,希望汉武帝能从历史的教训中获得启示,他提出秦统一天下之后,不注意发展经济,随意变革币制搜刮民财,集天下之财,用于“外攘夷狄,内兴功业”,以至于“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而统治者“犹自以为不足”。由于统治者对于资财的贪求和积聚,造成贫富分化、社会生活失调,从而改变了当初古朴的社会秩序。结果,统一的秦王朝由强变弱,直至迅速灭亡。社会历史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其原因就在于“物盛则衰,时极而转”。司马迁看到了“盛”与“衰”是作为事物的两个对立面而存在,彼此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关系。基于这一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司马迁在撰述《史记》的字里行间中始终渗透着“通古今之变”的宗旨。
具体说来,他首先采用十二本纪的方式,通过以历代帝王为中心的“王迹”盛衰史的描写来察其变。接着,采用世家、列传与本纪纵横相连的方法记述历史人物,将古往今来的历史贯通起来,来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另外,他还采用“表”、“书”等形式反映古今历史之变。十表,按世系、年代记述五帝、夏、商、周、汉各朝代及诸侯国分合盛衰的过程;八书则分别记述了古今各项制度的变化。而众多的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并促成整个社会乃至历史的变化。诸如司马迁在《平准书》后论中,谈及“农工商交易之路通”本是社会发展中的积极因素,但由于统治者对资财的贪求和积累,反而成为导致经济衰退、社会生活失调的诱因。司马迁不仅看到了经济变化带来的社会变化,而且清醒地意识到对战争性质的变化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对历史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司马迁在一开始肯定汉武帝反击匈奴,但是当汉武帝将反击演变为黩武时,司马迁便极力赞美汉文帝偃武修文而不论汉武帝之用兵,以此讥讽汉武帝的穷兵黩武。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切近世,极人变”的辩证思想。在司马迁的眼中,社会历史发展只有通过“变”,才能不穷而久,从历史观念的发展来看,这显然已经具备了唯物、辩证的因素;从唯物辩证史观来看,司马迁的这一认识,已经达到他那个时代认识的高峰。
综上所述,司马迁通过对具体历史事实的考察,从以上三个方面总结了历代治乱兴衰之故,不仅揭示出历史发展的真理,而且为历代统治者探索出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一史创目的,使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司马迁是在真正地履行着一位史学家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
董运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