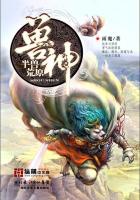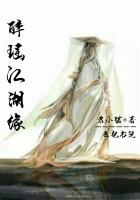程言峰
有这样一则故事:英国一所小学里的校长很喜欢小动物,其中他最喜欢一只叫“拉爱科”的小狗。课余时间他经常带着“拉爱科”跟学生们一起玩耍。有一天,校长突然发觉“拉爱科”不见了——最终,他在花园边找到了被剖开了肚子的心爱的小狗,其内脏几乎全被掏了出来。“凶手”很快被找到了,是小学生麦克劳德。后来校长得知,这个孩子好奇心极强,总想看看狗的内脏是怎样的,因而导致了这一悲剧。校长爱狗但更爱学生,他最后决定惩罚麦克劳德,罚他画两幅画——一幅是人体血液循环图,一幅是人体骨骼图……长大以后,麦克劳德成了一位著名的解剖学家,那两幅画至今还收藏在英国皮亚丹博物馆里。
我惊叹于这位校长惩罚手段的高明。麦克劳德后来的成功,得益于小时候他的好奇心受到校长的保护和引导。孩子有错,应该教育,但如何教育却大有学问。有些教师认为教育就是制服,让错者不敢再犯。因此,学生一旦犯点错误,就毫不客气地大声呵斥、贬低、侮辱,使孩子们稚嫩的心灵遭受到难以承受的刺激。不客气地说,这种做法,纯粹是报复和解恨。而麦克劳德的校长呢,心爱的小狗被害,最初他一定是暴怒的。但是,最后他却容忍了,只给“凶手”一种善意的“惩罚”。这不正像一枚蚌面对猛然袭入的沙子吗?——一种无条件的接纳与包容!
从某种角度来说,一粒攻入的沙子,对蚌是一种干扰、一种破坏,甚至是一种侵害。可是,“伟大”的蚌却不仅悄然接纳了沙砾,而且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爱去浸润它,用自己的生命和光华去感化它,直至把那沙砾改化为晶亮闪光的珍珠。
师者如蚌。“蚌”是一种无私与宽宏,一种接纳与包容,一种博大与精深,一种至诚与至真,一种至韧与至爱。蚌意如斯,师当若何?
我想,小小的河蚌尚且有如此的胸襟,那作为我们以育人为天职的师者,不是更应该用那种博大的包容,让那暂有瑕疵的孩子变成一粒粒闪耀光彩的珍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