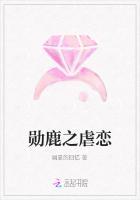李、白自然不能接受这种城下之盟,遂公开与南京决裂,复电,斥责蒋介石“墨迹未干,自毁信誉”,表示对蒋的任命“殊难遵令”。同时,李宗仁在全省下达了全民动员令,扩编成立战斗部队,一周之内就组编起21个师,准备与蒋介石战斗到底。
与此同时,李、白数度对外发表讲话,表示决不因为广东内变而停止抗日运动,而竭诚欢迎各抗日反蒋党派、团体、人士,到南宁共商救国大计。为了把主张抗日反蒋的力量团结起来,李宗仁还亲自致函主张抗日的李济深来桂主持大计,并派遣亲信赴港邀请抗日名将蔡廷锴、区寿年人桂重组19路军。
至7月底,李济深、蔡廷锴、翁照垣、胡鄂公等相继人桂。全国抗日组织救国会的杨东莼、何思敬,第三党的章伯钧以及国内各界名流邓初民、彭泽湘、刘芦隐等也应邀来桂,一时间也是豪杰汇聚。在“抗日图存”的口号下,桂省军民普遍发动起来,民团、学生大都动员起来,老百姓也纷纷订立了《抗日公约》,被激起来的民众热情持续高涨。
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号召“反蒋抗日”。李、白举旗反蒋,主张抗日,不管其当时的急迫政治意图重心是否在此,但此举却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有所契合,适应了当时普遍主张抗日的社会潮流。毛泽东在6月9日通过陕北无线电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表示:西南抗日反蒋中“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但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吾人准备在军事上及其他各方面给西南以各种可能的援助”。(29)中共的表态引起了李宗仁、白崇禧的重视,他们派人与延安建立了联系,并与中共领导人就订立《抗日救国协定》进行了探询和商讨。
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围绕对桂用兵问题,也出现了不同的态度。两广方面在事变发生后已经与派往西北剿匪的东北军、西北军接上联系,张学良、杨虎城部“已呈不稳”;四川刘湘、山东韩复榘、云南龙云等对“伐桂”态度暧昧……这些举动,使蒋介石在筹划攻桂时不得不有所顾虑。他再次调整战略,开始寻求谈判解决问题的转圜办法。处于劣势中的广西方面自然希望避免战端,这就使和解有了共同基础。最后在各方的努力下,和议方案最终达成,内容包括:蒋承认以中、日现状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广西届时保证出去参战;蒋收回调动李、白职务的命令,李、白通电服从中央的领导;蒋并答应对广西事变以来之财政开支予以补助。(30)9月16日,李宗仁在南宁宣誓就任广西绥靖主任,并发出和平通电。内称:
宗仁痛念国家危亡,激于良心职责驱使,爰有前次请缨出兵抗战救亡之发动。唯一目的,既欲以行动、热忱吁请中央领导俾能举国同仇,共御外侮,区区此心,当为国人所共鉴。无如抗敌之志未伸,而阋墙之祸将起,内战危机,如箭在弦,群情惶惑,中央威惧。所幸吾中央当局,鉴于民众之爱国情绪之不忍过拂,以及仅有国力之不可重伤,特一再派遣大员入桂观察;对桂省一切爱国运动之真相已彻底明了。同时对宗仁等救亡等项意见,全部俯予接纳。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予为一致之努力。(31)两广事变就这样结束了。
围绕抗日还是剿共所引起的一次次政坛险情,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至少在表面上也要对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出调整,也不得不把抗日作为自己维持政权的必须考虑。实际上这种政策转向,从日军增兵天津后就已开始酝酿。1935年10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在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时,暗示中国政府准备武装抗日,希望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对此,苏方很快作出反应,并在9天之后与中方进行了秘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苏联政府提出了改善两国关系,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等设想。
作为准备抗日的一部分,国民党也开始与中共接触,并先后开辟了4条渠道与中共联系。第一条渠道是,派遣邓文仪到莫斯科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第二条渠道是,指派陈立夫负责打通国共关系的工作,在南京同中国共产党接触。第三条渠道是,由宋庆龄传递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国共两党中央直接建立联系。第四条渠道是,通过中共上海地区党组织沟通国共联系。到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中共中央谈判代表与国民党谈判代表进行直接谈判,国共两党的沟通渠道正式建立起来。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日的态度也开始趋向强硬。在1936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于在五全大会上讲的外交政策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损害我国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说明白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他还说:“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度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种侵害,就是要损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32)蒋介石这些言论,与半年前的讲话相比,已发生了颇大变化。他不仅明确宣布决不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而且表示了一旦中国领土和主权再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害,即下“最后牺牲”的决心。
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还加紧了为抗战预作物质准备的行动。在1935年国防计划中,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区域,以消耗战略的长期抗战,“制止敌之蚕食野心,确保我之领土完整”。在1936年的国防计划中,又将全国分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确定“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
为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还决定对原有庞大而杂乱的军队进行整编,计划至少要整编出60个师,半年一期,每期编练6至10个师,目标是加强和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为抗击日军建立一支国防陆军的基干。蒋最为信任的干将陈诚随之受委,为陆军整理处处长,全国所有的炮兵、骑兵、工兵统由其负责督导整理。
张治中也是蒋介石信赖的不多的几个嫡系将领之一,蒋同样委以他重任,责成张治中负责南京和上海地区的战备工作。蒋介石还把张从中央军校调到苏州,在狮子林和留园,以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名义,秘密进行作战研究,实际上承担了预设将来作战指挥部的使命。
蒋介石还下令加强江防、海防,以防御日军海军袭击,并同时下令整顿南京、镇江、江阴、镇海、福州、厦门、汕头、虎门等要塞,充实其武备。在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还秘密调集4个师从事构筑国防工事的任务。至抗战爆发前,共在江浙地区建立工事2264个,占全国总建工事的三分之二。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独裁实力人物的蒋介石在对日态度缓慢变化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虽也有变化,但总的来说没有改变消灭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当1936年底国民党党内矛盾有所缓和之时,他的这一立场和态度便再次凸显出来。
(1)《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2)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1931年7月23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150页。
(3)《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出版1992年版,第248页。
(4)《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出版1992年版,第249页。
(5)蒋介石:《剿匪的成效如何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见《蒋中正言论集》,第5辑,第12页。
(6)《蒋中正言论集》,第1辑,第98页。
(7)蒋介石:《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09—247页。
(8)须力求著:《胡汉民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09页。
(9)天津《大公报》,1932年2月13日。
(10)《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2期,1933年2月15日。
(11)《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3期,1933年3月15日。
(12)《国闻周报》,第13卷,第9期,1936年3月9日。
(13)申晓云著:《李宗仁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220页。
(14)王维礼著:《蒋介石的文臣武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页。
(15)朱金元著:《民国十将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页。
(16)《一二·九运动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8页。
(17)《一二·九运动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
(18)《一二·九运动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357页。
(19)《全民月刊》创刊特大号,1936年3月15日。
(20)胡开明:《一场激烈的斗争和一个事实的故事》,见《12·9运动回忆录》,第1集,第248页。
(21)晨风:《郭清之死》,见《北大旬刊》,第2、3、4期合刊。
(22)参见《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83页。
(23)《全国各届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见《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24)《李济深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25)《胡汉民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54页。
(26)《申报》,1936年6月10日。
(27)《国闻周报》,第13卷,第23期。
(28)齐裴:《两广“六一”事变》,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29)《毛泽东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党史资料室编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210页。
(30)程思远:《政坛回忆》,第83页。
(31)《毛泽东书信集》,第71页。
(32)蒋介石:《御侮之限度》(1936年7月13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0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