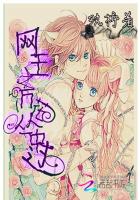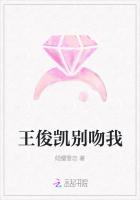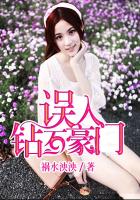金兰私情岂能置换民族大义,优柔寡断乃兵家之大忌。张学良的一丝犹豫致使绝密的兵谏筹划险些胎死腹中。严酷的现实再次教育了张、杨张、杨内紧外松,紧急点兵布阵。蒋介石睥睨一切,自感已把对手逼入“死穴”。双方的暗中角力进入最后摊牌阶段清晨6时,扣蒋战斗打响,8时蒋氏在山洞中被擒。城内仅用两个小时即结束兵谏行动。蒋介石撤张、调防东北军的命令终成一纸空文大变迫在眉睫之间,张学良处于极度矛盾之中。
他与蒋介石有着近10年的交往。父帅被日军炸死之后,是他坚持易帜,追随蒋介石,为蒋介石实现全国“统一”立下汗马功劳;中原大战之时,是他不顾东北军将领的反对,力排众议率军人关调停,在最关键的时候帮助蒋确立了中央统治地位;九一八事变之时,为坚决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他不惜舍弃自己的家乡,舍弃自己的家财,舍弃父子两代的根基,甚至替蒋氏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当然,蒋介石也给了他荣耀和地位,而他也始终对蒋有一种感恩之情。他视蒋介石为长辈,蒋介石亦把他看作是晚辈,第一一夫人宋美龄还与他的夫人于凤至结拜为干姐妹。尽管他与蒋氏说话很随便,有时不免争吵,蒋也没有像对待别的异己军事实力人物那样认真计较过。
张学良与蒋介石就是在种复杂关系中走过来的。
但是,这一次政见之争,却使他没法让步。他要先攘外而后安内,而蒋氏却要先安内而后攘外。虽然表面上看这只是先后顺序的变化,但却涉及到是爱国、救国还是卖国、亡国的民族大义。他与日本有着国仇家恨,在率领东北军打回老家之前,让他放弃抗日这是一个不可能的选择,也是他一个不可动摇的人生原则。
他也深深理解蒋介石的苦衷。蒋与共产党斗争了十几年,始终把共产党视作心腹大患,而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也确实证明只有共产党能够抗衡于蒋,使蒋“剿共”终难成功,而蒋要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地位,也就势必想方设法削弱共产党挑战他独裁统治的能力。
但是,理解并不等于可以支持。与民族的生存相比,与解救人民于水火的大义相比,个人的权力欲望和恩怨情仇都是微不足道,可以抛在一边的。如果仅仅为了个人,张学良可以什么都不要,可以什么都舍弃。几年前,张学良曾经为了保住蒋介石而主动下野,张学良也曾不止一次地向蒋介石披露心迹:“为了委员长,我张学良可以牺牲一切!”
今天的蒋介石,却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把张学良逼上了绝路。
今天的张学良,为了民族大义,也终于不得不迈上逼蒋抗日的关键一步。
金兰私情岂能置换民族大义,优柔寡断乃兵家之大忌。张学良的一丝犹豫致使绝密的兵谏筹划险些胎死腹中。严酷的现实再次教育了张、杨前面说到,张、杨于12月8日晚正式确定兵谏捉蒋。把这个日子作为张学良最终定下兵谏的时间,是相对于最后成功捉蒋而言的。从张学良后来口述解密的资料中得知,在这之前已开始了捉蒋行动,只是没有成功罢了。
那是在蒋介石第二次来到西安之前的12月1日。张学良派在外面的东北军联络人员王化一从武昌打来“华密”电报,说:何成浚秘密告知,他在洛阳为蒋介石祝寿时,在钱大钧的办公桌上看到拟好的电报稿,内容是调东北军到苏皖,然后调福建去,使之与共产党及杨虎城隔离,请副司令有所准备。
原来从武昌行营移住西安后,张学良仍将王化一以“四维学会”及东北中学校长的名义留在武昌,实际上让王负责收集南京方面的情报。那天晚上,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招待武汉的军政官员,王化一也应邀参加。散席后,他将王留下,告诉了他在洛阳看到的秘电。
何成浚是北伐战争中去北方谋求南北息争时与张学良结识的,两人常相往来,私交甚厚。对他提供的情报,张学良深信不疑,立即找来杨虎城研究并决定采取捉蒋行动,并为此拟定了三套方案:
开始他们打算设法将蒋人和车骗到西安城内,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蒋软禁起来;进而又想以请蒋再次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为名,在中途设伏,劫蒋入城。但当时时机紧迫,这两个办法都仓促难以实行,并且西安蒋系势力众多,问题也不那么简单。他们最后考虑,认为干脆把蒋介石捉起来还是以采取全面的军事行动的办法较有把握。(1)虽然设定了三个方案,但是,这只是个模糊的、粗糙的方案,对于怎样捉蒋、派谁去捉蒋、何时开始行动等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均未进一步研究。张学良最初提出由17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完成捉蒋任务,但蒋介石驻在东北军防区,由17路军的部队跨系统执行这一特殊使命,不仅后续支援存在问题,还容易引起两军间的误会,因而这一方案没被采纳。
正当张、杨为怎样比较稳妥地实现捉蒋而不断筛选各种方案时,蒋介石终于打破惯例离开华清池了。12月6日上午,他在邵力子的陪同下前往西安南郊。张、杨紧急研究后认为有机可乘,遂决定在他由南郊回临潼途中将其秘密地捉起来,押送至西安新城大楼,然后再和他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
张、杨预计,蒋返回临潼经过西安的时间约在12点左右,他们设定:在西安南关附近实施捉蒋,行动时不准开枪,不断绝交通,不挖断公路,当蒋介石乘坐的汽车路经此地时,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士兵立即冲出来迫其停车,实施逮捕。与此同时,东北军派出部队逮捕驻守临潼华清池的蒋之随行人员,解除华清池附近及临潼车站备用专车上的警卫武装。西安方面,由17路军负责逮捕蒋系军政大员,解除公安局、宪兵团、省党部等的蒋系武装。
对这个行动方案涉及17路军的任务,杨虎城亲自进行了检查,只等东北军捉拿蒋介石,他便组织城内行动。但直到下午3点还未见捉蒋动静,杨虎城怕出现意外,赶忙询问张学良。张解释说,他中午接到南京电话,说何应钦当天来西安见蒋,准备将何一起捉拿,所以临时改变了行动计划。第一次捉蒋行动就这样未及实施便流产了。
这次行动的流产,反映了张学良对捉蒋的犹豫心理。而大战来临前的犹豫是极为堪忧的。几个月前就是因为张心存犹豫、拿不定主意而坐失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那是6月初两广事变爆发以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密电张、杨,要求西安方面出兵援助。此时日本谋求“华北特殊化”已经成为事实。为求自保,张、杨曾派出使者到北平、太原、济南探询各实力派对待抗日的态度。各方的表态证实,一旦日本进攻华北,阎锡山可能投降日本,宋哲元将是虚晃一枪,向后退却,日军将不战而得华北和山西,蒋介石若继续执行“剿共”政策,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局面必难形成,到那时,西安将会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为此,张、杨曾商定寻找机会,打破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推动全国抗日局面的形成。而两广事变的爆发,为实现张、杨抗日愿望提供了可能,加之两广方面派代表进驻西安进行游说,于是,张、杨就决定:
(一)张、杨分别致电蒋介石,称:日寇进逼,国亡无日,举全国之力以挽救,尚感力竭,若内战不止,更是手中自戕,长敌气焰,要求和平解决两广事件,反对对两广用兵;要求和平统一,共商抗日大计。
(二)如蒋对两广罢兵,西安方面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和召开国会以解决国是的主张,通电全国各军事长官、各省府、各法团征询意见。
(三)如蒋对两广继续用兵,西安方面即出兵援助两广。军事部署为:东北军编为第1集团军,以王以哲为军团长,下辖两个军,向郑州、武汉推进,担任主攻。东北军第51军留在甘肃,担任警备后方的任务,对青海马步青、宁夏马鸿逵方面严密警戒。17路军编为第2集团军,以孙蔚如为军团长,辖第17师,陕西警备第1、第2旅,由雒南出南阳经襄阳向汉口挺进;17路军的第42师担任韩城、朝邑、大荔及豫西一带的河防,向山西方面实施警戒,确保西安及陕县至郑州段陇海铁路的畅通:淳化至耀县、耀县以东至韩城以北,商请红军接防。(2)如果这一方案实施得当,对蒋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不仅援助了两广,使蒋不敢举兵南犯,而且很有可能使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西北的抗日要求。
但是,张学良面对内部劝其观望的意见,面对蒋介石要其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邀请,处于两难之中,最终将执行决定的时间拖了下来。这一观望给了蒋介石用兵两广的勇气,也就给了两广致命的一击。
两次犹豫产生的消极后果,使张、杨都认识到,如此下去将断送此前的各种努力。12月7日,杨虎城对张学良说:“不能再失时机(指上次对两广事件的失机),不能再失人心(指适应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要求)”。张学良也坚定地表示:“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3)张、杨定下决心以后,分别向他们的心腹和主要高级将领打了招呼,开始秘密布置。但直到此时仍然没有确定发动的时间,以致酿成12月9日的一场虚惊,险些误了大事。
那天晚上,张学良安排了两项活动:一是去华清池见蒋,二是与杨虎城联名邀请南京的军政要员看戏。黄昏时,17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有事找东北军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但此时孙正和士兵准备乘卡车出发,仓促间只告诉宋他先去临潼,让宋改时间再来。由于12月6日两军已有布置,宋文梅误以为孙铭九此行临潼就是执行扣蒋使命。他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了17路军总部。
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得知情况后,觉得问题极为重大,发生又这样紧迫,必须让杨虎城早有准备。而此时杨虎城正在戏院招待南京蒋系大员看戏,王菊人把他接回总部报告此事后,杨虎城联想到张学良未到戏院看戏,又有上一次未通知即取消扣蒋行动一事,认为东北军开始行动也是有可能的。
作出这样的判断之后,杨虎城认为必须配合东北军行动,他按以前与张学良商定的17路军的三项任务(解除西安城内蒋系武装,占领特务机关,接收蒋系各级机关并扣押蒋系高级将领),作了部署。当夜17路军的兵力部署是:17路军陕西警备第2旅孔从洲部(共3个团)和炮兵营,由孔指挥,担任西安城内的任务;特务营宋文梅部(共4个连),作总预备队;卫士队2个连,包围易俗社戏院担任扣押蒋系高级将领的任务,并担任新城至易俗社的警戒;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驻新城担任临时指挥官。
杨虎城在下达作战命令后,为了不使蒋系要员们看出破绽,又返回易俗社继续陪同蒋系大员看戏。而17路军负责执行任务各部于晚8点均开始出动,各街口均布双岗,只等扣到蒋以后开始行动。等到10点左右,孙铭九方面仍没有消息传来,杨虎城顿生怀疑,一面请陕西几位绅士继续点戏,以拖延时间,一面赶回绥署,命王菊人查问究竟。王菊人找到孙铭九才知道,孙铭九去临潼是查路而不是扣蒋。这才迅速通知以解除夜间军事演习的名义调回已经出动的部队,限拂晓前立即归还建制,回驻原地。一场虚惊终于结束。
这一夜,杨虎城在凌晨1时才赶回绥署。他深感两军官兵人心浮动,扣蒋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再推迟下去,一旦部队失控,发生骚动,将暴露整个计划。
12月10日一大早,他就应张学良之约到张公馆研究此事。张学良与他有一样的感觉。于是,两位主帅决定:今日完成准备;11日晚上行动。
张学良能够迅速定下扣蒋决心,除了发生了12月9日扣蒋预演这样的突发情况,客观上使行动不能再拖外,西安爱国救亡的一二·九事件的爆发,也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线。
在17路军因情况不清而提前进行扣蒋预演的同一天,西安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抗日罢课游行活动。这次活动是由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通过“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组织的。张、杨在8日得知情况以后,起初并不赞成游行。他们认为,扣蒋行动已经决定,如果这次群众运动引起蒋的注意,蒋就会搬入其嫡系部队控制区中去住,那便打草惊蛇,捕蒋计划将会落空。其次,如果蒋系部队对群众开枪,而他们又阻止不了,发生了血案也不好。因而张、杨建议救国会停止游行。张、杨还决定,如果救国会非举行游行不可,就由17路军特务营沿途贴在游行队伍两边行进,把蒋系的宪兵和警察隔在外边,起到保护游行队伍的作用。
但这些建议均未被游行组织者采纳。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组织这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目的是利用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契机,揭露蒋介石反共的新阴谋,进一步推动张学良、杨虎城走联共抗日的道路。由于张、杨的扣蒋行动是在绝对机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不可能向他们有所透露;而他们此时也不了解张、杨的行动计划,因而,未能达成一致。
但是,爱国学生自己也制订了安全措施。组成了一支由2000名同学参加的纠察队,负责维护安全;组成了由百余辆自行车编成的交通队,负责来回巡逻,传递信息;还组成了2个代表团,以备谈判和宣传群众。
12月9日早晨,15000名大中小学学生由各校涌进西安城南门,当游行队伍行进至东大街时,遭到国民党军警拦截,结果,一颗示警的流弹击中了竞存小学12岁的小学生。小学生中弹身亡的消息传出,广大学生怒不可遏,坚决要求严惩肇事的西安市公安局长马志超。10时许,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隆重开幕,并通过《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言》。这份《宣言》提出:对此当前的危局,我们四亿五千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们,都应该下必死决心,为民族牺牲,为国家牺牲。我们的当局,更应该下最大决心,与全体国民一心一德,共赴国难,共同牺牲。《宣言》还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当机立断,即日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一面派遣现驻西北边疆的17路军和要打回老家的东北军,组织援绥军星夜北上驰援;一面停止‘剿共’军事,随即商讨抗日救亡大计。”
会后,游行学生委派代表入西北“剿总”、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递交请愿书。张、杨为不使蒋介石生疑,未出面接见学生代表。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虽然与学生见面,但重弹“救国不忘读书”的论调,并含蓄批评学生参加爱国运动为过,这番言论激怒了学生,游行大军遂转而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