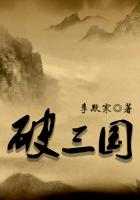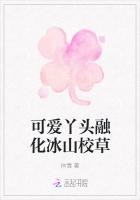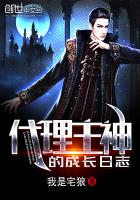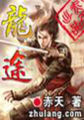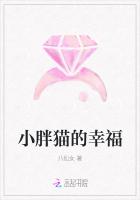张学良只得相机将学生去临潼请愿的事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闻讯勃然大怒,指责张学良放任学生运动,命令张学良立即予以制止,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同时,命令西安的特务机关、宪兵第2团、省公安处、西安军警联合督查处、省党部,对学生运动“查明拿办”。军警闻讯,倾巢出动,在灞桥附近的土坡上架起了机枪,准备屠杀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学生。幸亏张学良及时赶到,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
张学良请求学生们不要再去临潼,他请求同学们把请愿书交给他,由他转交蒋介石。他对同学们说:“你们不必去,不必去挨打、挨枪。我可以代表你们,一定替你们要求;我可代表蒋委员长,一定达到你们的目的。”
张学良讲到:“同学们!同学们!诸位爱国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我,这么冷的天气,你们挨着饿去临潼请愿,这使我个人难受了!……今天我敢肯定地答复你们,我张学良致死还是抗日的,不但你们现在要求我出兵,要求政府出兵绥远,而且我自己也在极力请示中央抗战的……诸位!我张学良若不出兵抗日,任凭诸位将我处分,我也是自甘领受的。”
学生们被张学良的真诚所感动,他们高呼:“拥护张副司令出兵抗日!”“拥护抗敌领袖!”“拥护抗日政府!”“我们愿为救国流血,愿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
许多学生失声痛哭,在场的不少东北军士兵流下眼泪,张学良也抑制不住连连手拭苦痛的泪水,他再一次向学生保证:“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更迫切。你们请回去,一星期之内,我保证用事实回答你们的要求。”
张学良为群情所激动。当晚,他把学生的要求紧急呈报给蒋介石,并且又动了劝谏之心。没想到他所得到的又是一通训斥:“你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到底是站在学生的立场呢,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张学良又被蒋介石一个闷棍打了回来。
蒋介石对张学良面对学生的表态非常不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汉卿向余报告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以代表你们,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代表,可酌另考虑你们的要求’。彼以自言甚得意,余当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的代表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4)而这一天张学良的失望亦达到顶点。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向其部属解释对蒋实行兵谏的理由时,这样说道:“‘一二·九’西安学生游行,事先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出各种方法来制止,我提出几个办法: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主席召集扩大纪念周,令学生用文字表示。实在还不行,非游行不可,由我和杨主任、邵主席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要到临潼去。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令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激愤,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竞公开说明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军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5)于是,“便断然决定”,实行“兵谏”,用武力迫使蒋转变。
张、杨内紧外松,紧急点兵布阵。蒋介石睥睨一切,自感已把对手逼入“死穴”。双方的暗中角力进入最后摊牌阶段12月10日。这一天对于蒋介石和张、杨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天。
鉴于张学良对学生运动的处理背离蒋之本意,再次引起蒋的不满。这天,蒋介石召开没有张学良参加的军事会议,作出了他解决张、杨问题的最后决定。
作为一个疑惧心颇重的靠军事机器起家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独裁人物,作为一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代枭雄,蒋介石不能不考虑这一决定的作出,即意味着张、杨及其两军要求立即发动举国抗日的希望就此归于破灭,也不能不考虑手握重兵的张、杨会不会做出绝望之中的反抗。
蒋介石考虑的是什么?
他认为,张学良一次又一次地劝谏,是对他忠诚的表现。这种忠诚从东北军“易帜”开始,近十年始终如一。张学良自己亦说过“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6)因而蒋介石对杨虎城严加防范,进驻西安时宁可选择离城25里的张学良的防区华清池,而不住杨虎城的防区西安城内。
此行,蒋介石只带了近身侍卫官和一个警备区队(排),连警卫股长黎铁汉及其所属20名警卫人员也没有带。
华清池大门由东北军卫队一营的一个加强连守卫,驻临潼的105师1旅3团派一个连驻守骊山烽火台,控制制高点,警卫华清池。
蒋介石嫡系的西安宪兵团虽然派来80名宪兵,驻守华清池内院,但看管火车站专列用去40人,华清池内真正有作战能力的蒋系人马也就只有40来人。
此种部署说明,蒋介石对张学良和东北军还是可称放心的。
蒋介石认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可保他个人安全无忧。在洛阳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已做好缜密的军事部署。大批军队已经集结于河南,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坐镇开封,指挥二线部队。前锋樊崧甫军已过洛阳,在潼洛间构筑工事。西线宁、甘至汉中一线,“中央军”已有十二三个师,万耀煌军的一个师陆续进入战略要地咸阳。樊军董钊师准备入驻临潼。装甲列车已开到陇海线上待命。马丁式飞机70架也已进驻西、兰两地,其中在西安停放45架,并又将由广东投靠南京的部分飞机调来补足100架。此外,还储存了3000吨炸弹,预备了毒气弹。面对如此重兵,张、杨若与他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他认为,东北军与17路军矛盾对立,不可能联手。在来西安之前,蒋系特务机关把关于张、杨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报了过来。这里面,有关于东北军与17路军关系紧张的,有张、杨与共产党私通的,等等。在蒋介石看来,东北军虽确有“通匪”隋事,但张学良本人不会“真心向共”。掌握蒋介石决策内幕的张镇曾说:“我们开初收到有关西安方面的情报,说张、杨意见不合,有要火拼的模样。当时委座认为情报比较准确,因为张、杨之间的矛盾必将越来越大,最后难免冲突。后来又得到情报,说张、杨两人来往密切,有联合一致反抗中央的模样。委座对这情报的判断是,可能性不大。因为张、杨两人,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联合不起来。何况中央军当时云集潼关一带,随时可向西安推进,而张、杨在西安的部队很少,又怎敢反抗中央呢?委座因而大胆飞往西安。”(7)蒋之所以“放心”是否还认为,他在张学良身边安插有自己的耳目亲信,张学良的一举一动都在自己的监视之下。原来,蒋介石在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后,同时派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任西北“剿总”参谋长,又以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的全部班底组成西北“剿总”政训处,以特务头子曾扩情为处长,担任东北军的政治训练工作,向东北军将士灌输绝对拥护蒋介石和坚决反共的思想,并负责监督和调查东北军和17路军官兵的思想与行动;在这同时,还有大批特务进入了西安,散布流言蜚语,挑拨东北军和17路军两军之间的关系。这使蒋介石自以为张、杨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以他之力应付张、杨游刃有余。
蒋介石的高级幕僚、特务系统也不只一次地考虑这类问题。但除了陈诚曾提醒蒋“西安已绝非宜于驻节之地”外,其他人都没有怀疑到张、杨会对蒋氏下兵谏重手。
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曾预感东北军基层官兵的情绪不对。他在12月8日杨虎城约见他时曾吐露自己的担忧。他说:我感到形势严重,忧虑会不会发生日本“二·二六”事变那样的事。杨虎城听后马上说:决不会有那样的事。后来,邵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我是担心东北军不稳,或有不利于张的举动,并未想到张会以兵力扣蒋,更不曾想到杨会与张合谋。”(8)特务头子曾扩情亦没有想到能会发生扣蒋事变。事变时,当他从睡梦中被惊醒后,还以为张、杨两部发生军事冲突,直到第二天早晨看了张、杨的通电后,“才恍然大悟”。
蒋介石的亲信、派往西北“剿总”的参谋长晏道刚,听到枪声后,也只是怀疑杨部兵变。谁也不曾往张学良身上去想。
张、杨正好利用了蒋介石的误判,一方面继续在高度秘密状态下加紧进行军事准备;一方面故布疑阵,照常去临潼见蒋,并进行诤谏,还大规模地宴请蒋系军政要员,造成歌舞升平、太平无事的景象。
12月10日晚,张学良自己驾车只身来到新城杨虎城公馆,与杨研究政治军事形势,安排“兵谏”行动。张、杨对此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作出了如下判断和安排:
一、军事方面:豫西地区的“中央军”不足10万,分散在郑州至潼关一线,如果蒋介石被扣留,豫西“中央军”没有立即集中向陕西进攻的可能。届时必须确保潼关这个隘口,争取时间把分散在陕西及陕甘边界的东北军与17路军集中到西潼路上,时间约需5天左右。迅速占领潼关的任务,只能使用驻在大荔一带的17路军42师冯钦哉部。同时,请红军派一部进入商雒地区,确保潼关右侧安全。估计红军到达该地约需10天左右时间,但商雒一带既无“中央军”,红军又行动迅速,并有群众工作基础,完全适宜担任商雒地区的防务。此外,令驻洛阳的东北军炮8旅暨洛阳军分校东北军军士大队占领洛阳,迟滞“中央军”西进。对已经进入咸阳的“中央军”万耀煌部(2个团),由17路军警3旅将其包围缴械。兰州方面,由于学忠51军固守,并商请红军派出一部兵力进出甘肃西兰公路,以牵制胡宗南等部“中央军”,使其不敢向陕西进逼。
如此部署,则可背靠红军,南凭秦岭,保障关中。汉中只有蒋系王耀武、李及兰两个师,只需扼守宝鸡一带即可对付,所受威胁不大。由于蒋介石被扣留在西安,南京势必有所顾忌;也由于万福麟部、宋哲元部和韩复榘部陈兵于平汉、津浦两线,威胁着陇海线,估计南京当局不敢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更不敢贸然孤军深入陕西,这样有利于东北军和17路军迅速集结做有效的防御。
二、政治方面:“兵谏”的目的在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估计会得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和四川刘湘的支持。由于路途遥远,难以取得他们军事上的直接支援,但政治上的同情、声援也可壮大“兵谏”的声势。华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已表示愿以兵力支持,这较有力。至于山西的阎锡山,至少可以保持中立,不至于以武力威胁河西与豫西。起事之后,可形成西北、华北、四川、广西联合起来与南京对峙的局面,逼使南京不敢武装进攻陕西,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召集有各方代表参加的救国会议,组织抗日联合政府。扣蒋后,蒋介石必须声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确保东北军和17路军的现有地位,然后才能考虑释放他。(9)张、杨还决定,东北军负责华清池扣蒋,17路军负责西安城内扣留蒋系军政大员和部分武装。11日夜正式发动。
张、杨作出部署以后,根据各自承担的任务,分头对两军又进行了布置。
先说执行华清池扣蒋任务的东北军。为了达成军事行动目的,张学良授权105师师长刘多荃为总指挥,由驻临潼的第105师第1旅第3团和驻西安南门的第1团担任外围警戒,129师师长周福成为外围警戒指挥官。
外围警戒的任务于11日晚,经67军105师师长刘多荃下达到该师第1团、第3团,并令所部听从周福成的指挥,其任务是:担负外线警戒,防止蒋介石突围逃跑,并适时支援内线。据此,周福成部署第1团展开于灞桥以东,届时,包围华清池西面和北面,占领临潼火车站,解除火车站宪兵武装,控制交通,特别注意灞桥至蓝田方向;第3团包围华清池的东、南面,并在骊山附近设置机动兵力,准备适时支援内线。
内线行动的任务由张学良的卫队二营担任,主要是进入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完成扣蒋任务。由105师第2旅旅长唐君尧任内线指挥。
挑选谁来担负活捉蒋介石的任务,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蒋介石是当时全国的军政领袖,扣蒋会被视为以下犯上;华清池周围警备森严,除东北军卫队一营守卫华清池大门及在周边警戒外,二道门内全是蒋系卫士,装备精良,且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如果不能顺利地达成任务,势必为蒋逃走提供机会;扣蒋的目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而必须抓住一个活的蒋介石,而不能把他打死,更不能让他跑掉。因此,在扣蒋的人选上,必须考虑:一、胆大心细,不能因见到蒋就胆战心惊,不敢行动;二、有丰富经验,能干净利索地解除蒋的卫士的武装;三、对张、杨忠心不二。既不能因与蒋有仇怨而挟公报私,也不能暗地通蒋,出卖张、杨。
开始,张学良曾经考虑由17路军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担此重任,宋为此也挑选了250名亲信士兵作好了准备,但由17路军担负这一任务的不利因素是,他们不熟悉蒋介石行辕的情况,而行辕周围的驻军概系东北军的部队,张担心两军配合会成为问题,弄不好还会引起东北军部队的误会,影响扣蒋任务的完成。
经过张、杨的反复考虑,最后确定由孙铭九、白凤翔、刘桂武3人共同执行扣蒋任务。作出这种安排,是因为东北军卫队二营是张学良的近侍部队,其营长孙铭九对张素来忠诚,还非常熟悉蒋的行辕的情况,便于应变。骑兵6师师长白凤翔是张学良一手提拔起来的,为执行这次任务,刚把他从固原电召到西安;刘桂武是绿林出身,张学良对他曾有救命之恩,他和白凤翔一样,机智勇敢,枪法极好,因在军官训练团学习时受到张的赏识,遂留在张的侍卫副官处供职。另外,还安排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配合,这是因为蒋介石行辕的外围警卫是张学良卫队一营担任的,吸纳该营长参加扣蒋便于行动指挥。
华清池扣蒋行动的3名具体实施者中,有2人对蒋住处及其周边环境不甚熟悉。为此,张学良先于10日上午安排白风翔、刘桂武到华清池面见了蒋介石;11日,又带着刘桂武去了一趟蒋介石行辕,以熟悉蒋的长相及行辕的地理环境。孙铭九营长也频繁地来往于临潼大道上,察看华清池周围的地形。考虑到西安华清池尚有25公里,为便于行动张学良还令特务2营1连连长王协一率领30名士兵赶到十里铺,与原驻扎于此的王振东排会合,到灞桥驻扎。11日上午,张又令向该地增加了1个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