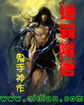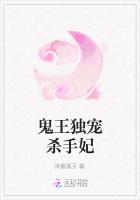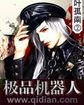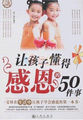法、德、意: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法国支持英美的和解主张;德国虽属意释蒋,又不愿支持主和派:意大利反对西安事变,主张中日亲善法国对于中国西安事变后事态如何发展也是极为重视的。12月15日专门召开内阁会议,听取外交部长台尔博斯的报告,研讨具体对策。鉴于在此前一天美国代理国务卿穆尔对西安事变的公开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在尽力获得西安事件之详情,美国对于远东仍继续遵循不干涉他国事务之政策”,法国内阁会议遂决定,“由外交部注意今后之情势,再定适当办法。”这一表态实际是美国的翻版。随后,在美、英联手实施和平营救蒋介石的计划时,法国的外交决策者把静观事态的政策改变为力主和平解决事变。
法国各大报刊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不表支持。他们认为,西安事变“使中国复生内战之危机,且将使历年来在艰难之工作下所收之功效,陷入停顿状态”,“张学良之出此行动,是否真正爱国尚属疑问,实际上仅为私人问题而已。张学良从前为东北军领袖,中国政治上之第二人物,而现在华仅居次等地位,于心不满,故此时乘其部下多怀二心,竞藉此暴动,以济其私”。
法国政府认为,中国不能没有蒋介石领导。他们说:“现在中国军队之力量,实较五年优胜,此种进境皆蒋委员长所赐,因蒋氏素来抱有压制各个军阀建立一支强有力之中央军之决心”,因而,希望恢复蒋氏自由,和平解决事变。
德国在西安事变发生前不久,刚与日本签订了《防共产条约》,两国在反共反苏上的共同利益,使其必须站在日本的立场上。但是,除了与日本的战略利益外,德国在华还有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
德国在华的利益首先从军事领域开始。早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就与德国西门子公司驻远东总工程师亚曼博士商洽雇用德国顾问之事。孙中山要求聘请的德国政治、经济、军事顾问的理想人选为:(一)政治顾问,由大战末期德国首相之高级助理兴芷海军大将担任;(二)经济顾问,由前任胶州之德国高级专员许拉尔担任;(三)军事顾问,由一德国高级将领担任。但是,由于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去世而未能执行此项计划。
1926年,蒋介石在成为国民党的军政实权人物后,聘到了一战时期德国的军事独裁者鲁登道夫的高级助手包尔上校。1929年包尔死后,柯利伯代理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总顾问一职。柯利伯虽然履职只有一年,但他的军事思想却对蒋介石的“中央军”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傅宝真所说:
德国之所以能在军火工业及军火运输方面,占绝对优势地位,大部由于自柯利伯开始,直迄于顾问团被召回前,德式顾问被正式参与我国各项讨逆及防御战役中。并在我陆军训练与组织之计划中,渐具颇深之影响力。因此,我军事当局,渐采德式操典、训练与组织方法为准绳。包尔抵华后,以顾问团基础未固,仅以个人(带少数随从,如王格姆等)身份,前往武汉前线,协助蒋公草拟作战计划与其执行。此即谓顾问团以整个组织而言,并未正式涉入战斗及其有关行动。但包尔死后,武汉地区仍极具重要之战略地位,且桂军有卷土重来之势。如武汉陷于敌手,桂军可与北方冯玉祥之国民军直接狼狈为奸,对我中央政府威胁甚为严重。故蒋公命柯利伯及其作战参谋数名,赴武汉地区布防。俟该局势缓和后,蒋公再命柯利伯及其参谋,筹划沿汉水流域对国民军发动之攻势,并以占领郑州为目标。不久,我中央军即占领该城。美国陆军武官亲赴郑州战场观察,在其报告中,彼曾指出,我军获有德国雍(容)克公司单翼及双翼之飞机助战,故轻举而占该城。(42)1930年夏,曾任德军参谋本部总长的魏泽,继任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总顾问,他帮助蒋介石制订作战计划,赢得中原大战胜利,此后,又参与制订了对红军的第一、二、三、四、五次“围剿”计划。应当说,魏泽对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中央系军队发展的建树作用是巨大的,但是,他的建军思想被怀疑为德国军工企业谋利,蒋、魏开始出现矛盾。
1933年,一名更有军事成就的德国将军进入蒋介石的视线。他叫色克特,与希特勒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应邀对中国军队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之后,给蒋介石草拟了一个《陆军改革意见书》,其要点是:
1.“任何建军之先决条件,首在国境之安定;此即谓数年外在之和平与内部政治情势之稳定。在此条件未达成前,有效之军事组织工作,将无从谈起,连续不断之战争,将影响最终目标之完成。”色氏这一见解,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谋而合。
2.中国建军应重质量而不重数量。他说:“中国所急需者,不在一庞大陆军之建立,而在集中全力创设一训练优良与配备完善之小型精锐部队。”色氏断言,目前中国军队,不在患寡,而在患多。为此,色氏为中国军队建设提出了三项中心思想:(一)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与防卫外来侵略之安全盾牌;(二)军队之威力,在于其素质之优良;(三)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育。
3.军队的军事指挥与行政系统的最高权力应集中于一个人身上。色氏认为,“中央政府统治权之基础,在于其军队置于单一之指挥系统,亦即直属于委员长。但其先决条件却应使军官之任命,依照统一之原则行使,而不应置于个别师长或将领手中。”
4.中国陆军的改革方向应放在军事行政方面。色氏主张,在军事体系内,明显划分组织功能,坚持层层负责,统一指挥,是国军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在军事指挥系统中,职权必须作清晰的规定。军事机器中,诸如训练、行政与指挥等单位,均应统属于总司令管辖,作为政府的一员,直接对政府负责;军政部长、军团司令及参谋总长等又须对总司令负责。
色克特所提的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令蒋介石十分佩服。
蒋氏即聘任色克特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总顾问。蒋介石不仅对于色氏军事方面的意见言听计从,而且对色氏的厚待也是前所未有的。经蒋介石批准的就色克特地位所作的规定中说:
将总顾问对于钧座及对于德籍顾问之地位,以下列名义谓之:
“委员长委托人”
“总顾问”
办事方式:一切日常公务,以及关于德籍顾问之指挥,均于总顾问办公室或鄙人私宅内处理之。代表委员长与中国各机关之谈话,在南京军官学校委员长官邸内举行之。(43)这里所谓的“委员长委托人”,实际上有“代理委员长”或“副委员长”的意思,故其地位,仅次于蒋。因而,“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须亲自到领袖官邸向色克特请教。此不但为包尔、柯利伯与魏泽所无法享受之地位与特权,即在中国历史中,亦恐无第二位外籍人士所能被国家元首如此赏识与重托。”(44)此时,德国顾问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影响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由政治和军事上的影响逐渐延伸到经济领域。色氏在推进中国陆军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也推进了中国与德国的军火及经济合作。有资料显示:
德国大公司互相倾轧,为推销本身之产品及利益,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与顾问及我国官员相勾结,以求达成其推销目的。美国一家电气公司曾抱怨称:有时该公司故意将标价降至德国公司所标者若干成以下,但中国政府仍选购德货,想其中必大有文章。我国建军财源,本已极为有限,再有此种腐化现象,对抗日战争准备影响至巨。(45)上述说明,1936年的中德关系,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关系良好,合作加深,且德在经济上也对中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而,它对西安事变的演变相当关心,担心因此而引发新的内战,危及它的既得利益,并希望早日和平解决事变。
这种双重的利益关系,使得德国对于西安事变的态度陷于两难,一方面,在战略态度上需要与日本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它不方便公开地赞成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更不便介入英、美的和平调停。故在处理西安事变的问题时,采取了以私人身份表达立场的方式。12月20日,德国国防部长柏龙白致电宋美龄:“敬祝委座充分健康,早日出险,从而益增力量,以领导广大之中国。”21日,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致电孔祥熙,对西安事变“焦虑良深”,希望“一切妥善解决,委座事业获竟全功”。
意大利是支持蒋介石反共打内战的,对于西安事变的处理,它支持日本的中日亲善政策。在德国养病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返国,得到了意的鼎力相助并促成其与日本达成谅解。
意大利为了说服张学良反共投日,还派出了秘密使者齐亚诺做说客。齐亚诺是墨索里尼的女婿,同时也是张学良的好友。12月21日是,齐亚诺代表意大利政府致电张学良,要求释放蒋介石。电报全文如下:
阁下系吾好友,兹若与共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不能缺少蒋介石将军,请即日恢复其自由。(46)对于中日关系,齐亚诺坚持认为,“此际中日两国,若能推行协调政策,实属最为明哲,且有实际利益。反之,任何企图,凡以妨碍此种政策为能事者,必系以碍此种政策为能事者破坏性质的野心为背景也”。在这同时,意大利在国内舆论上,坚持了日本的宣传基调,大肆散布西安事变是出自“莫斯科魔手”的谣言。
除了上述各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之外,各国舆论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基本上大同小异。他们从各国的在华利益出发,纷纷谴责张学良“受苏俄指使”、“与共产党同流合污”、“劫持最高统帅”,并攻击张学良有政治野心。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张学良忧虑重重,思想负担十分沉重。
(1)原电稿失散,此件系中央档案馆所存的抄收电稿。
(2)原电稿失散,此件系中央档案馆所存的抄收电稿。
(3)《张学良大传》,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页。
(4)《对中国实施的策略》(1936年8月11日,内阁有关各省决定),参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6页。
(5)王金林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3页。
(6)王金林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3页。
(7)《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
(8)《日本历史20·近代7》,东京岩波书店1981年版,第133页。
(9)秦郁彦:《日中战争史》,东京原书房1979年版,第13页。
(10)《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东京美铃书房1977年版,第682页。
(11)胡德坤:《中日战争史》(1931—1945)修订本,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12)《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211页。
(13)《现代史资料8》,第631—632页。
(14)《日本外务省档案》,S68,S1615—28,第61页。
(15)《驻日大使许世英5次电告》,参见《西安事变资料第》
(16)《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17)《休阁森爵士致艾登先生(第231号)》(1936年12月13日),参见《党史研究资料》1988年第2期。休阁森即许阁森,下同。
(18)《休阁森爵士致艾登先生(第245号)》(1936年12月18日),参见《党史研究资料》1988年第2期。
(19)《代理国务卿穆尔致驻华大使詹森电》(1936年12月18日下午7时),参见《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20)《驻华大使詹森致国务卿电》(1936年12月19日晚11时),参见《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21)《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
(22)《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
(23)《代理国务卿穆尔致驻华大使詹森电》(1936年12月14日下午2时),参见《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24)《驻华大使詹森致国务卿电》(1936年12月16日中午),参见《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25)《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26)《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27)《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28)《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9页。
(29)《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1935—1937),上海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659页。
(30)《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3页。
(31)《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5页。
(32)《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电》,参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7卷,第670页。
(33)《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9卷,第677页。
(34)《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1935—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59页。
(35)《蒋廷黻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字出版社1979年版,第197页。
(36)《挽救危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页。
(37)《挽救危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页。
(38)《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4页。
(39)《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页。
(40)《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0页。
(41)《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1页。
(42)《蒋介石详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585页。
(43)《蒋介石详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591—592页。
(44)《蒋介石详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591页。
(45)《蒋介石详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593页。
(46)《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