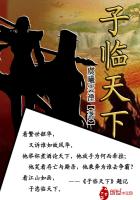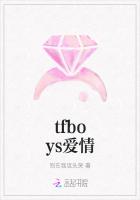七、对第三者部队(指红军撰者注),准由杨主任秉承顾主任之意,设法接济。(15)西安与南京双方的谈判于1月24日正式拉开帷幕。西安方面的代表是米春霖、谢珂、李志刚,南京方面的谈判代表是顾祝同。第一次谈判,在潼关举行。这次谈判的重要问题,西安方面由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等商定,必要时邀请周恩来共同商讨。南京方面,以顾祝同和他的参谋长赵启骤为主,重要问题请示蒋介石。
当时,顾祝同在火车上办公。西安代表去时,他正集合各路司令官作出准备打仗的姿态。谢珂见状很不满意,首先作了措辞强硬的发言。他说:“蒋委员长在西安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既有诺言在先,军队就应东开,准备抗日,为什么‘中央军’反而西进,是不是又要来打内战?东北军和17路军对此非常激愤,假若压迫太甚,一定要打仗的话,我们是有准备的。”
顾祝同说:“西安方面既表示接受国家领导,就应该服从国家的命令,国家有统一调度军队之权,现在国家要你们拆除二华防线,‘中央军’进驻西安,17路军调驻渭河以北地区,东北军调驻邠县以西一直到兰州地区。你们不听国家命令,反而在二华增兵布防,这就是不服从国家领导的表现,所以才进兵解决。”
谢珂又说:“在张学良将军未回西安以前,‘中央军’是不能西进的。”
双方各执一词,谈了3个小时毫无进展,最后商定两天之内可以继续谈判。
由于双方谈判一开始即出现僵局,顾祝同转而又与何柱国会谈。何柱国向他提出两点要求,都是关于军队布防的,一是在西兰公路上东北军驻一个军;西安附近17路军驻两个旅。顾祝同对此两点未表异议,并于其后向蒋介石发电请示两个问题:
一、红军移动时发给若干经费,总需30万(至少)至50万元。
二、西安事件中已用之费600万彼方请予核销,可否准许200万元。
此时,杨虎城对于和谈成功寄予很大期望。听完谈判代表的报告后,他说:“只要国家政策有转变,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他担心东北军以释放张学良为谈判先决条件,将把事情弄僵,于是加派曾在黄埔军校任外文秘书、与顾祝同有私交的17路军参议王宗山为谈判代表,以缓和谈判气氛,便于和顾祝同商谈。
蒋介石也急于使谈判取得成果。针对顾祝同的请示,他于1月25日上午9时,对潼关谈判提出七项要点:
一、东北军在西兰公路上可先驻4个团,待其移动完毕以后准再增2个团亦可。但成阳城内不可驻部队。
二、17路军在西安附近,于其他各部未移动完毕以前不能超过两团兵额。待各部移防完毕后,如有必要亦可酌增一、二团。惟其驻地仍须由行营指定令行。
三、第三者(红军)移动时,以30万元为度。
四、西安事件报销之费用,最多不得超过200万元。
五、17路军、东北军移动时,准发1个月伙食;待其移防完毕时,准再先发1个月。
六、张汉卿名义必待其部移防完毕后方能呈请,此时如果请求不惟无益,适增国民之反响,徒戾汉卿而已。
七、第一步,各部撤至西安、成阳以西日期,最迟不得超过本月30日;第二步,移防完毕不得超过下月10日。但东北军入甘路程较长,准予酌量展申,然亦不得过下月15日也。惟“中央军”接防陇海全线至宝鸡,必须于下月5日以前完毕。”(16)对蒋介石提出的7项要点,杨虎城和中共未提疑问,东北军表示原则同意,但要求“先发表张之名义而后移动”,这使谈判进展又缓下来。26日,顾祝同通过何应钦向蒋报告:“商谈情形不能迅速开展,杨之态度并不如何坚持,第三者亦未出而捣乱,问题全在东北军。”而东北军内,“高级将领大体均可接受命令,但对下级不能妥为运用……军官中亦有态度甚恶者,均为下级居多。”(17)蒋介石对东北军持此态度甚为恼火。当天傍晚,他指示刘峙、顾祝同向东北军发出恫吓,声明:第二天中午前为谈判最后期限,届时如果还达不成协议,东北军还不撤退,即为和平破裂,“中央军”将开始对东北军前线阵地及前方指挥部进行轰炸,而暂缓对西安新城目标的轰炸,以示区别。善于恩威并施、分化对手的蒋介石,在发出战争威胁时仍不忘制造对方内部的不和,以牵制对手。27日上午,蒋介石又致电东北军各将领,进行“劝说”,再次承诺:
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后,中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但此时万勿提出事实上不可能之问题,以延误大局也。(18)不管蒋介石的承诺能否兑现,也不管人们对他的承诺有几分相信,但有了这一承诺对于化解在谈判中因张学良出处问题而出现的僵局总是有益的。
张学良对于因他的出处问题而使谈判陷于僵持也深表不安。27日,他急电东北军前方将领,要他们千万不能把他的出处问题作为接受甲案的先决条件。电文说:
知前方仍未接受移防命令,万分焦急。此事如前次瑞风、志一两兄弟回陕时,兄等接受甲案并即实行,则良之出处此刻已不成问题。今因迁延,引起误会,委座实属为难万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即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迫切,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勿再固执误事为要。(19)对于谈判陷入僵局,中共中央亦十分关切。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如确能停止战争,可保证让步。如要“出现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毛泽东在这次电报中还告知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无论是和或战,应由杨虎城、王以哲左派打定主意,我们应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与此同时,为加强党对西北善后的领导,中共中央还派出名义上仍在“负总责”的张闻天秘密到达西安。
毛泽东、张闻天的电令,使中共代表团对解决西北善后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周恩来、叶剑英等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加入谈判。中共作为“三位一体”的一方不仅应该参与西北善后的谋划,而且中共作为一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加入善后谈判,对于推进谈判进程也是极为有益的。这一动议经过东北军的何柱国转报顾祝同后,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中共加入谈判以后,谈判很快取得突破,三方于第二天即1月28日,基本达成东北军在7天内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北岸的协议,并决定执行甲案。在这个协议中,南京方面也作了局部让步,比如,进驻西安与潼关一线的“中央军”由12个团减为3个团,同意在三中全会前呈请恢复张学良公权,给以职务,让张学良来陕训话后部队移防等。同时明确,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仅限于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留待五届三中全会解决。
蒋介石一直把中共视为宿敌,顽同坚持“剿共”,但中共为了抗日的大局,为了避免内战重启,堪称以德报怨助蒋化解了僵局。
对此,蒋氏是心存感激的。周恩来抓住这一机会,以毛、周的名义致电上海的潘汉年,请潘设法向蒋介石传递中共的下列意思:
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中共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但是,蒋必须同意:
(一)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供养。(三)暂时容许一部分红军在陕南驻扎。(四)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五)亲笔复恩来一信。(20)蒋介石表示同意中共意见,并于1月31日电告顾祝同: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月给20万至30万元的经费;同时委托宋子文答复潘汉年:同意两党联合抗日。此后又同意在西安设立红军联络处。
对于西安方面与南京即将达成的和平协议,在东北军内部却引起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打还是和。
主和的是东北军的元老派,他们是师级以上的将官,以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为代表。主战的是少壮派,他们大都是抗日同志会的领导骨干,以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为代表。
主和的元老派只有少数人,他们从和平解决事变这个大局出发,也争取释放张学良,但并不以此为先决条件。其中态度最坚决的是董英斌,他始终坚持“三位一体”的团结。王以哲忠于张学良,也尊重周恩来,倾向于接受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
张学良被扣以后,面对西安方面群龙无首的局面,面对“中央军”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对南京特务的收买瓦解,元老派中也出现了各为自己打算的倾向,沈克、檀自新与蒋介石的密使打得火热,外界甚至还传出了于学忠已投靠南京的传闻。甘肃省财政厅长陈端也于1月9日向孔祥熙密报,称“于学忠已表示服从中央并建议作调解人”,故“中央军”对51军保持友好姿态。蒋介石于15日批准陈端的建议,并电令胡宗南与于学忠切实联络,避免冲突。
主和派的这些做法,使少壮派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元老派被蒋介石收买了,腐化了,营救张学良不力。
少壮派大都是张学良在武昌行营期间和到西安后提拔起来准备用以抗日的干部。其中,孙铭久是1935年调到参谋秘书处工作,管人事档案,后兼随从参谋,参与机要。应德田本是负责陪李杜去联络苏联的,因一时难以成行,才回武昌行营任秘书。张学良认为,打起仗来,既要依靠“拿杆儿”的老将,也要依靠少壮派这些联共抗日的先锋和骨干,两者不可或缺。因而对少壮派非常赏识,委以重任。张学良亲任会长的抗日同志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培养抗日骨干的少壮派的组织。在张学良培养提拔下成长起来的少壮派,对张学良自是绝对忠诚。他们认为,不救回张学良一切无从谈起。
少壮派的成员虽然都是一些团、营职军官,但他们人数却很多。他们提出的“为释张学良不惜一战”等营救张学良的主张,在东北军内颇有市场,无人敢说“不”,也为广大的东北军官兵所赞同。
张学良从抗日准备出发,从东北军的发展出发,培养年轻一代军官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后来的发展也表明,少壮派积极拥护联共抗日主张,在西安事变起到了先锋和骨干作用。但是,培养年轻干部的依托——抗日同志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也少有具一定政治经验的军、师长加入。因而,少壮派在政治上把拥戴张学良看得高于一切,认识和处理问题就难免陷入简单化,自然也不会认同元老派的主和意向。
1月20日,蒋介石公开拒绝释放张学良后,少壮派的活动更加频繁了。他们认为,蒋介石不肯释放张学良,只有走“打”的一条路。这时,一度曾经传出的东北军有人“拥王代张”的谣言又乘间兴起,这使少壮派确信主和的将领都是为了升官发财。他们发起了营救张学良的签名运动。这个“签名运动”主张为了救出张学良不惜对南京方面作战,“战胜了可以使张学良获得自由,战败了就投靠红军”。应德田、孙铭久等带头签名,主战的少壮派随之响应。征集签名的活动延伸到渭南前线,团长以上的军官有100多人都签了名。团长们签了名,师长们也跟着签,最后有的军长也签了名。
签名的成功,使少壮派受到鼓舞,调子越唱越高,他们以此为据,宣扬对南京开战是东北军上下一致的主张。
在当时,选择甲案,乃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甲案,对东北军不利,因为甘肃是个穷乡僻壤之地;乙案对东北军有利,因为豫皖比较富庶。但是,接受甲案,意味着“三位一体”不被拆散;而选择乙案,意味着“三位一体”不复存在。而现实是,只要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靠拢在一起,对西北局势的发展就有利,营救张学良回陕也是大有希望的。正是看清了这一点,周恩来建议杨虎城:对乙案坚决拒绝,对甲案可基本接受。杨虎城及17路军的想法与周是一致的,张学良也是这个意见。
当然,选择甲案或者乙案也有风险。这就是不管是接受甲案还是乙案,都意味着“三位一体”要让出西安这一战略要地。作出这一重大牺牲和让步之后,能否保证内战从此停止,抗日从此而起?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也有这个顾虑。为此,毛泽东于1月21日电示潘汉年,要求蒋介石写一个保证书,保证和平解决后不会再有战争。
少壮派顾虑的不是这些重大战略问题上是否还起变化,他们紧盯的只是眼前救张问题能否马上实现。少壮派认为,无论接受甲案还是乙案,都不可能把张学良救回来。他们对接受哪个方案都反对,一心想要的是“开战救张”。
“开战救张”虽然从战略全局上看并不可取,但这一主张却很容易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中取得共鸣与支持。元老派虽然主和有理,并握有兵权,但都怕背上不救张学良的骂名,而不敢公开讲反战问题。
杨虎城是西北方面的最高负责人,他原本是主张接受甲案而和平的。对战的问题,此前他取的是以战促和的态度,现在和平在即,选择战势必失去和平的机会。但是,他更担心如果采纳甲案,“中央军”开进西安后会对他报复,在张学良被扣之后他的这种心理负担进一步加重。杨虎城在“战”与“和”问题上的摇摆不定,与少壮派有着共鸣,并使少壮派从中看到了希望。
这样,劝说少壮派罢战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共的肩上。1月下旬,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来西安在张学良公馆大厅举行座谈会,邀请两军主和、主战的主要人物参加,做大家的工作。彭、任先后讲话,大致意思是:
(一)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要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新瓜分殖民地。日本决心灭亡全中国。英、美虽与日本有矛盾,但尚无决心与实力制止日本的侵略。苏联虽是反对一切侵略,但重点是对西边的德国。我国面临亡国之祸,必须全民团结,争取国际援助,共同抗日。
(二)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因此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依据,也是当前的基本政策。
(三)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国际上更依赖英美,在英美与日本有矛盾的时候,他仍有抗日的可能性,释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正确的,更增大了这种可能性。蒋介石是可以抗日的,只要大家团结好,在全国抗日高潮中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张汉卿先生是可以回来的。
(四)目前形贽不宜用战争去解决问题,打仗可能引起更混乱的局面,更不利于张先生回来,高兴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21)彭、任两人谈了近两个钟头,然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但大家均无表态。这种沉默,当然不意味着与会者的思想统一,而只能是信任和沟通的桥梁发生裂缝的表现。十年后,周恩来在对美国记者李勃曼谈及西安事变时曾说:“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22)1月27日晚,周恩来邀请东北军少壮派的主要人物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等人,到金家巷张公馆继续做他们的工作。
会谈伊始,少壮派即激烈地反对和平解决的方针,主张只有张副司令回来才能撤兵,并要求红军予以支持。